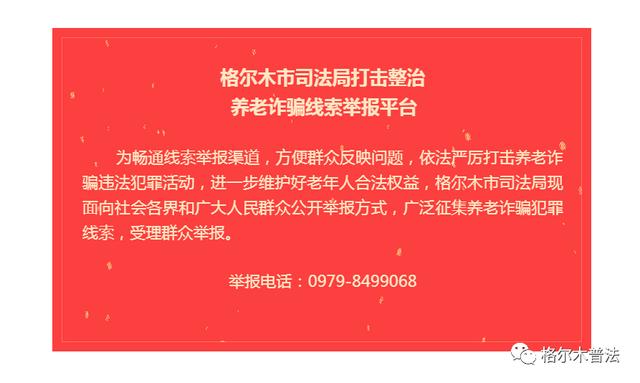冬天来了,北风一吹,天气一下子就冷了许多。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夜间,大街小巷不觉就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小贩站在烤炉前,也不大吆喝,更花不起钱请名人代言,因为烤熟红薯浓郁香味儿就是很好的广告,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
红薯,又叫红芋、红芋、甘薯、地瓜。从品种上大致可分为红瓤红薯,白瓤红薯。在中国,红薯的吃法很多,但把红薯烤着吃,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而又最简朴的吃法了。在我的家乡多用红瓤红薯,烤熟的红瓤红薯特别的香甜。但北京也有烤白薯的,吃起来有一股栗子的香味。

人对食物是有记忆的,这种记忆几乎都是从儿时开始的。记得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念他童年时代曾经“吃伤”,年逾花甲却又“因为久违,有了感情”的一种食物。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有着汪先生味觉记忆中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儿时的烤红薯。
就烤红薯而言,留给许多人最初的印象不是城市街头巷尾烤红薯的炉子,而是儿时的乡下,那时家家户户都用锅灶做饭,而燃料则以稻草、麦秸等农作物的秸秆为主。庄稼人过日子总讲究个精打细算,饭熟之后,趁着灶膛里的余火,扔几个红薯埋在火堆里煨熟。
从锅灶里扒出来的红薯远没有炉子里烤出来的品相好,红薯通体乌黑,剥开乌黑的焦皮,露出黄澄澄的瓤儿,顿时散发出阵阵香味,放嘴里咬一口,软酥酥、甜润润的,那个香,就甭提了。剥过红薯的手上粘满了黑乎乎的炭灰,稍不注意,就会弄到脸上、鼻子上。

但凡食物皆为美食,红薯也是如此。按照美食家的说法,美食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温饱之需,其次是口舌之欲,最后是慰藉心灵。我们这一代人贪吃的天性其实源自食物匮乏的童年,能求得温饱已经是那时许多家庭的梦想。然而,就是在这种刚刚就能达到的温饱之需里,一些关于食物的记忆便深深埋下了种子,历经一生都难以改变。
在对于烤红薯的记忆里,似乎都与冬天有关。而在冬天的记忆中,永远少不了走街串巷,推着由汽油桶改造的烤炉车的小商贩。炉灶边,除了待烤的红薯,还有乌黑发亮的无烟煤;那灶口是用铁盖盖着的,炉子的上面放着一层烤好的红薯,一个个软软的,热乎乎的,迎着寒风飘来一阵阵香味。

或许烤红薯确实太普通了,以至于烤制的工具都如此简便,且全国各地如出一辙。烤红薯看似简单,但要掌握好火候并不容易,俗话说“七分烤,三分捏”,也就是烤的过程只占七分,余下的三分全凭着一点点捏熟。这捏要轻重适度,捏轻了,不易熟,捏重了地瓜会变形,就不好卖了。卖烤地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论斤卖,要几块,用秤一称,那秤杆儿打得高高的,绝不缺斤短两。也有一些地方是论块儿卖,有分大小块儿的,块儿头大小不同,价钱也不同。
同任何烹饪技法一样,烤红薯也有技术含量。民国时的另一位文人徐霞村所著的《北平的巷头小吃》并将烤红薯的特点概括为“肥、透、甜”三个字。肥,是选用那种圆乎乎、皮薄、肉厚实的白薯烤制;透,说的是烤白薯的手艺,不能生心也不能烤煳、烤干了;甜,就是甘甜且不腻,越吃越香,令人爱不释手。所以烤红薯的秘笈为“七分烤三分捏”

一个人,一个炉子,一篮子红薯,这就是烤红薯“专卖店”的标准配置。过去,烤红薯的小商贩很辛苦,大清早就站在街头,迎着冬日的寒风,一整天也赚不了几个钱。民国年间文人张醉丐曾为烤白薯绘画配写过一首打油诗:“白薯经霜用火煨,沿街叫卖小车推;儿童食品平民化,一块铜钱售几枚。热腾腾的味甜香,白薯居然烤得黄;利觅蝇头夸得计,始知小贩为穷忙。”寥寥数句,可见让我们知晓烤红薯这营生有多么的艰辛与不易。
吃烤红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刚出炉的红薯拿到手后,因为太烫,红薯便在双手之间翻来覆去的跳起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它的诱惑,一边吹气,一边迫不及待地剥开那层如历经了风霜的树皮般的红薯皮,金色的肉便毫无掩藏的出现在面前,一阵阵的热气升上来,在空气中红开出一朵朵白而透明的花。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吃烤红薯同样,有性急的人还未剥完,便咬下一口,糯而面的红薯进入了口腔——这时便已顾不上烫了,一股甜味从红薯中伴随着热气不断涌出,塞满了整个口腔,咽下之后,嘴中还弥漫着温暖的气息,觉得嗓子被什么东西黏黏的,甜蜜的糊着。再然后,便如风卷残云般把一整只烤红薯扫荡干净了,有人甚至连红薯皮也不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