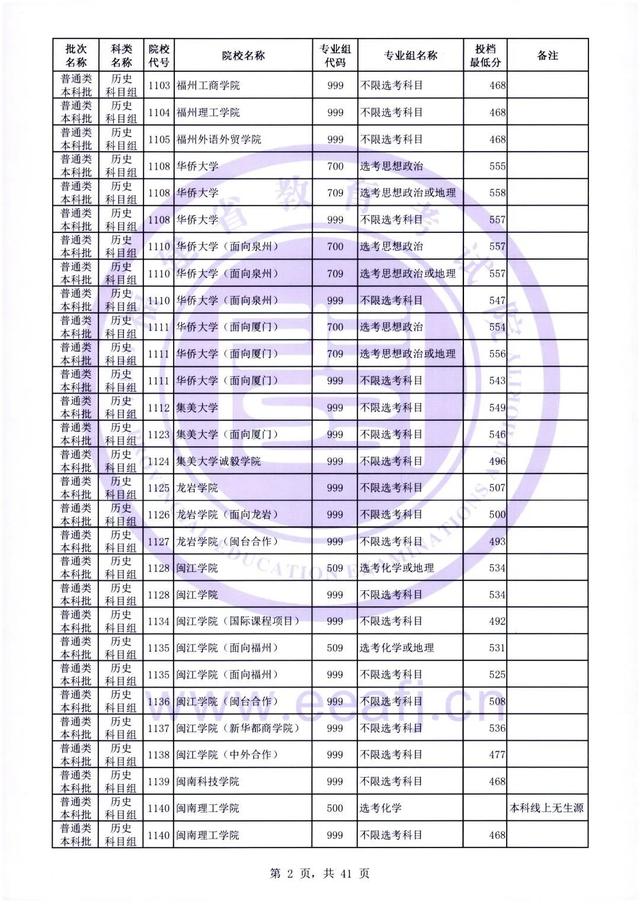同其他的乡村一般,沈阳市的满堂乡,在表面望上去是一个再平凡普通不过的村庄,资料有着农家炊烟,也有着大片的耕地。
可在这一片平凡之中,却生活着一千一百八十一名满族,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过去满清贵族的后代,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可在清朝灭亡后,他们为了躲避外界的视线,曾经集体改姓,试图隐姓埋名,以求得在乱世中的安稳。
这些满清遗贵从何而来,为何生活在沈阳,有着什么样的传承历史?他们又在清朝灭亡后遭受着怎样的经历呢?要知道这些,还得从明末清初说起。

聚居许多满清贵族的满堂乡,位于沈阳的东郊,坐落于沈阳的东陵区。沈阳的东陵,也被称为福陵,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坟墓。
这座陵墓气势宏大,占地面积广阔,几近20万平方米,牢牢地立在沈阳的天柱山上,望着山脚下的每一个村落。
而满堂乡内的清朝遗贵,与这座天柱山上的陵墓以及陵墓的主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满堂乡内的满族人群中,与东陵主人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一群被称为“黄带子”、“红带子”的人。

“红带子”、“黄带子”,是红色和杏黄色的腰带的代称。
在清朝的统治规则下,原本普普通通的两色腰带,被附加上了非凡的政治含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系,在满清皇族内被尊称为“大宗”。
由塔克世这一家族主支繁衍下来的,被皇帝特许系上杏黄色的腰带。而其他的皇族分支,则被允许系上红色腰。红黄两色腰带,实际上就是满清皇室宗亲的象征。

根据这些满清皇室宗亲的说法,满堂乡的“黄带子”,其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第六子塔拜。1639年,塔拜在沈阳死去,满清朝廷便在其父亲的陵墓附近,为塔拜修建了一座坟墓,坟墓的位置恰好落于满堂沟。
塔拜去世的时间点,正处在崇祯年间,此时的满清还未入关,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的清王朝,尚未完全建立。原本按照习俗,塔拜的后人应该留些人手看守他们祖先的坟墓。出于战争和政治的需要,塔拜遗留下来的后代便随着其他满族人一起骑着马入关,在刀光剑影中为满清拼出来一片基业,建立起绵延数百年的清王朝。

随着时光的流逝,塔拜的后人一代接着一代老去,新生的八旗子弟开始习惯起北京的悠闲生活,可塔拜的曾孙裕得瑞,却忘不了落在沈阳老家的祖坟。
于是,在经历一番辛苦的路途后,裕得瑞便从北京的胡同,来到沈阳的乡村,看守起自己祖先的墓地,时间久了,便在此落了户。
而比起“黄带子”,“红带子”与东陵的连接要更深一些。“红带子”能记忆最早的祖先,是颚穆拜。颚穆拜是努尔哈赤时期的一名贵族,他曾经伴随着努尔哈赤东征西讨,还见证过满清势力攻克明朝控制下的沈阳。
夺取沈阳这座东北重镇后,满清把沈阳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苦心经营。作为努尔哈赤心腹的颚穆拜,由此被命令留驻沈阳,其后代子孙,在满堂乡繁衍生息,渐渐形成如今的人口。

除了“黄、红带子”这两类满清的皇亲国戚,满堂乡内还有一群被称为“三户赵”的满清贵族,他们虽然不如“黄、红带子”那边有权有势,但凭借着祖先的身份,还是能从清王朝那里拿到许多俸饷,因此在清代,他们的生活也还算惬意。
“三户赵”原本是努尔哈赤的三门亲戚,分别为伊儿根觉罗氏的洼和穆,喜塔喇氏的那哈初,以及祝氏的萨哈达。

这三户姓氏都是喜塔喇氏那哈初的后裔,是努尔哈赤的舅舅家,其先祖喜塔喇氏随着努尔哈赤一同起兵,共创帝业。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定都沈阳,编制八旗后,被编入正白旗,成为满清统治者中的一员。
1629年,喜塔喇氏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奉旨看守东陵”,而后又在满堂乡的中水泉一地建立“国戚祠堂”,并渐渐由一个姓氏,演化出如今的三个姓氏分支,并在时间的长流中改为赵姓。
就这样,“黄、红带子”和“三户赵”,以及其他一些零零散散的小贵族,互相之间紧密联系,通婚频繁,构建出满堂乡内规模尚可的满清贵族势力。
在清代,这些满清贵族凭借着自己与皇族的特殊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政治身份,享受了无数清王朝给予的特殊待遇,过着极为腐化的惬意生活。

根据清朝的规定,“黄带子”作为清皇族的近支,从15岁起,每年都能领取到一笔俸饷。到了20岁成年时,这笔俸饷会再次翻倍,有36两。而且,这些饷银不单单只有男性能获取,满足一定条件的满族女性,也同样可以领得到。
除去这些每年固定不变的俸饷外,“黄带子”们娶妻生子,续弦病亡,也同样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赏银。
不过,仅仅这些经年累月都不变的俸饷,还不足以满足这些贵族的生活开支,真正让贵族过上奢侈腐化生活的,还是他们从清朝那里得到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在清代,“黄带子”作为身份高贵的满清贵族,在违法法律时并不归地方官府审理,而是转由专门负责皇家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进行处理。
因此,这些贵族就相当于可以减免相当程度的法律处罚,在法律上高人一等。
而在满堂乡当地,“黄带子”贵族还依据自己的权势,占据了大量的山林耕地,在满清贵族还未腐化的后金时期,“黄带子”的祖先塔拜就占有6000多亩的土地。
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满清贵族势力在当地的不断增长,其占有的土地和其他各类经济权益,也越来越多。

与“黄带子”类似,“红带子”作为皇族的远支,他们也在政治和经济上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唯一不同的,只是“红带子”得到的特权数量,和“黄带子”相比起来要稍微少一些。
但即使特权数量相对较少,这些“黄、红带子”,以及其他的满清贵族群体,都能依仗着权势,过着赌钱打猎,骑马游逛的快乐生活,无需去作别的劳作,成了骑在人民头顶上的“寄生虫阶层”。
而在这些有权有势,并仗着权势获取金钱的贵族之下,更多的还是被束缚于制度之中的普通旗人。以及日子更为悲惨,仅仅有着个奴才身份的汉人。

从古至今,任何国度内的贵族群体,从其衣食住行,到各种奢侈享乐活动,都离开不了数量繁多的底层百姓,满堂乡的清代贵族们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满堂乡内,就存在着许多为“黄、红带子”、“三户赵”等贵族提供服务的百姓,这些辛苦劳作的百姓中间,既有自祖先起就紧密依附于贵族的满族旗人,也有先前也是“三户赵”贵族,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破落人家。
更有本为自由身,却不幸为满清掳掠,沦落为满清奴才的汉人。

在这些不幸却平凡的人群中,普通旗人数量最多。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无需遭受如汉人悲惨的命运,却也需要为兵或为农,为清王朝的统治出力或出钱。
依照满清朝廷的规定,满堂乡内的满族旗人,大多数从事着农业生产。和关内的汉人相同,他们也常常需要顶着烈日,到田地弯腰劳作,把自己的汗水融入东北的大地中,在秋天收获金色的果实。
实际上,在漫长的耕作中,这些每日劳作的旗人,不论之前祖先是身为“三户赵”的贵族老爷,还是世世代代就是普通平民的满族旗人,他们已经渐渐在每日的农事中融为一体,变成一个新的农耕阶层,成了一个个本本分分的农民,用自己的勤劳收获明天,而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也似乎就此被牢牢固定在这片黑土地上。

但这些满族农民的命运,有时有能窥见一丝转机。为了能从旗人中获取到稳定的兵源,清王朝规定,从满堂乡内的这些旗人中,选二三十名男性为兵员,充当马甲。
被选为马甲的满族人,不但能得到一笔兵饷,还领有一定数量的“随缺地”。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有战事发生,这些满清兵员就有机会从战争中夺取军功,建功立业,实现阶层的迁越。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种“制度”、“条件”的保障,这群普普通通的旗人,虽然也时常遭受贵族的欺凌,为其剥削,却也能见到一丝光明,找到对未来的一点盼头。
日子虽然苦,但也勉勉强强能过得下去,年景好一点时,也能经历和老婆孩子一起在热炕头上喝酒聚餐的好时光。
但和这些旗人百姓比起来,满堂乡内汉人百姓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在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满堂乡内的汉人社会地位极低,大多数汉人都是人身自由被贵族把控的奴才。
他们平常遇见“黄、红带子”、“三户赵”这些贵族时,必须极为尊敬地口称“老爷”,而在为自己的主人做事干活时,更需要尽心尽力。
否则,一旦稍有不如意,便会被自己的主人殴打责骂,有甚者,直接被主人处死。

满堂乡这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奴才被打死的悲剧。有一次,一名陈姓的汉人奴才,因为未能及时向自己的主人请安,遭到主人的痛骂。
陈姓汉人不愿自己平白受到冤枉,便稍微多加解释,结果竟引起主人的愤怒。这位贵族当即招来了几个族人,活活地将这名陈姓汉人和他的儿子打死。
满清贵族的残酷统治,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可怖的事情,不单单存在于满堂乡这片小小的土地上,它遍布于满清王朝控制下的所有地方。在这水深火热的统治之下,普通旗人,以及汉人百姓的愤怒正在一点一滴积攒着,等待着怒火喷发的时机。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清王朝紧紧封闭的国门,打碎了清朝皇帝世世代代统治华夏大地的美梦,而在这轰轰作响的炮声中,满堂乡贵族们的安稳日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高高在上的满族贵族老爷们,迎来了时代的剧变。
在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里,满清朝廷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西方列强的资本开始渐渐进入华夏大地,中国的经济也慢慢与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市场深度融合。在这种局势之下,华夏大地境内原来较为充裕的白银,开始逆转明清以来的白银内流趋势,转而向海外,特别是向西方流动。

白银的大量外流,不但削弱了满清政府的经济实力,还造成“白银”与“制钱”的兑换差额越来越大,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伴随白银价格上涨而来的,是物价的一路升高,在1890年到1910年这短短的二十年间里,粮价就翻了几倍,一斗高粱的价格,在1890年时,仅仅是半吊钱,而二十年过后,花上2吊多钱,才能买到一斗高粱。
“银贵钱贱”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形之下,满堂乡贵族能拿到手的银钱数量大大减少,而且消费能力也明显下降。
此外,因为满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本该足额发放的“饷银”,朝廷减半发放,而且中间还得经过宗族族长的克扣,最后贵族们领到手上的饷银,自然是少得可怜。
在这种困境下,“黄、红带子”、“三户赵”等皇亲国戚们,开始慢慢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日子也开始像其他普通旗人一样,变得紧巴巴起来。

穷则思变,面对经济上的窘迫处境,一部分满清贵族开始转向农业,经营自己依靠政治特权强占来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满族大地主。
但能成为地主阶层的,只有少数的几名幸运儿。更多的贵族,则不得不成为农民,弯下身子,干起他们从前极为鄙视的农活。
时代的巨浪就这样把以前骄横至极的满清贵族打了个翻身,原先联系紧密的满堂乡贵族,在这时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幸运者成了地主,维系着往日奢侈又腐化的生活,不幸者则被打落云霄,与其他平民一起从地里刨食。
时代的剧变不但影响着满清贵族,也改变着此前麻木的平民百姓。在各类新颖的经济形态推动下,在各类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此前为满清贵族欺压,为满清朝廷残酷统治而积攒几百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出来。
在1911年,酿成了一座革命的火山,把这个封建的清王朝毁灭掉。

虽然远在东北,但此时南方革命的浪潮也能波及到此。在辛亥革命期间,因为满汉间旧有的民族仇恨,出现过许多汉族意图报复满族的传闻。而曾经骑在人民脑袋上作威作福的满清贵族,更是人民要打击的首要对象。
在这类传闻的包裹下,因为自身与旧王朝的紧密联系,满堂乡贵族们惶惶不可终日,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任何问题,只要努力思考,总会有个解决的思路。这群满清贵族们思来想去,在革命浪潮越发高涨面前,他们终于横下了一条心——决定集体改变姓氏,从原来满族特征明显的满姓,改成平凡大众的汉姓。

于是,在清朝覆灭后,原先的“黄、红带子”、“三户赵”等贵族,开始改姓为赵,或为白、祝、徐、谦等等各类不同姓氏,以意图隐姓埋名,掩盖自己过去与清朝的关系,在革命中守住安稳,留得一丝生机。
而满堂乡中一大贵族势力——“三户赵”,其“赵”的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在改名之后,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满堂乡贵族们,失去了少数能代表往日荣光的姓氏,变得与身边其他普通人一般平凡。
在时光的浪潮中,他们渐渐融入庞大的社会底层中,与其他汉人百姓一起喝酒、劳作、打牌、通婚,真正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

回望过去,距离满清统治已经过去一百多个年头了,对于那些满清遗贵而言,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生活,已经如旧梦一般永远地飘散去,曾经把他们整个宗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血缘牵连,也在城市化大潮面前被冲垮得稀散。
如今的满清遗贵后代们,虽有些仍然以宗族的形态聚居着。但更多的,已化为原子般的家庭,和其他普通的百姓,共同生活在沈阳,生活在东北,生活在华夏大地上。
如今的他们,已经放下过往历史的重担,与其他族群的人民一起劳动,一起欢歌,一同悲伤,对于这些人群而言,依靠血缘和姓氏维持种群认同的时代已经淡去,剩下的,唯有基于意识而形成的一种身份认同——中国人,牢牢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1]本书编写组.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2]刘玺鸿.群体认同的历史与想象——兼读刘正爱《孰言吾非满族: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6(03):70-74.
[3]袁正. 消失的城市满族——以沈阳满族群体变迁为例的城市满族人的民族性[J]. 理论界,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