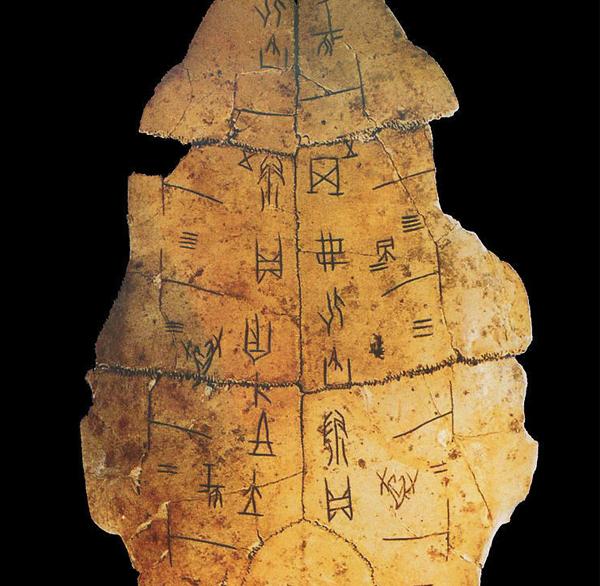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农历是戊辰年,属龙,寓上升之势明制,凡辰、戌、丑、未年,都是举行会试的年份各省举人上春官(礼部)赴试,称为“大比”今岁戊辰科,又恰值十三省官员,三年一度的来京朝觐述职,庸者汰,优者奖,俗谓“大计”,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明朝太监刘瑾罪行?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太监刘瑾罪行
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农历是戊辰年,属龙,寓上升之势。明制,凡辰、戌、丑、未年,都是举行会试的年份。各省举人上春官(礼部)赴试,称为“大比”。今岁戊辰科,又恰值十三省官员,三年一度的来京朝觐述职,庸者汰,优者奖,俗谓“大计”。
“大比”、“大计”不期而遇,均事关士人前程,所以早在去年尾梢上,各地官员举子们,就已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齐奔龙门而来。除了准备考察、考试,他们还满京师四城地投帖拜客,钻窬打洞—京人口毒,谓之“扫街”。
这时,有一个头条新闻不胫而走:“司礼监太监刘瑾刘公公,欲为其女择一佳婿。”据传,刘太监还强调:“吾女必得名士大夫。”
不乏好事者来帮闲凑趣,献议说:今天下才俊名士,齐聚场屋,刘老太监必是想在今科举子中择一东床。众人无不称是,都道:皇帝取门生(过去的进士都被称为皇帝门生),太监招女婿,如果太监女婿再兼而为皇帝门生,岂不倍增荣光?
这个冰人,还是做得!许多人开始忙活,各去物色说合,必欲荐一贤能。
一 刘太监的家世
要说一户人家,有女初长成,娇羞如花,待字闺中,总会惹来少年青目。如果这户人家,又够发达,有势力,则尤能歆动四方。而若论大明正德年间,谁家最有势力?——辄非刘老太监莫属。
婚姻属家事,先须扯扯刘瑾的家世。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兴平在明代是西安府的属县,别名槐里,据说著名的陇西李氏即发源于此。兴平知名,还与两个人物有关:一位是杨贵妃,另一位便是刘瑾。然而不幸,女宠与宦寺,恰恰是正史中被数为误国最深的两类人,合称“妇寺”,皆为不祥之身;尤可巧的是,刘瑾家的老宅距离贵妃上吊的马嵬坡,不过百步。这就让善于联想的文人攥住了话柄,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郑岳有诗道:
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敢,阉竖复生兹。
大意是马嵬坡非善地,昔日妖姬魄散于此,冤魂百世不散,至大明乃生一逆阉。这当然是刘瑾坏事后的话头了,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正当“炙手可热势绝伦”,谁敢说他一字的“逆”?
《明武宗实录》述刘瑾身世:“本姓淡,幼自宫投中官刘姓者得进,因冒其姓。”短短十八字,就有两处错误:
其一,刘瑾并非“自宫”入宫。刘瑾死于正德五年(1510年),得年60岁,以此推算,当生于1451年,即景泰二年。谢蕡《前鉴录・刘瑾》所收刑部状词记载: “(刘瑾)自幼净身,景泰年间选入皇城乾清宫答应。”景泰一共六年,刘瑾就是景泰六年(1455年)入宫,也不过五龄,焉有自己下手“割势”的能力?称其自宫,不过为了贬斥其为人。
其二,刘瑾本姓为“谈”,而非“淡”。《实录》说刘瑾投中官刘姓者,因冒其姓。明宫故事:阉童初入宫,都会拜一前辈中官为“本官”,认己为“名下”,但改姓与否,并无一定之规。“谈瑾”改名为刘瑾,并无可怪,奇怪的是,刘瑾一家老少都弃祖姓而投刘宗。如他的父亲叫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赠从一品的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母刘氏赠一品夫人。明代宦官最高官职不过“太监”,正四品,是没资格荣其父母的。刘荣夫妇蒙此格外之恩,自然是叨了他们的幼子刘瑾的光。可老子随儿子改姓,却匪夷所思。《武宗实录》在 “刘荣赠官”条记事下有云:“瑾本姓淡(谈),冒刘姓,自称赐姓云。”这便有解了,原来有“刘”为赐姓一说,如此则全家荷光,弃祖改宗,亦无不当。而依实录言,刘瑾左右皆不离一个“冒”字,或冒本官之姓,或冒赐姓,到底真相如何,恐怕只好问九泉呢。
刘瑾有一兄,叫刘景祥,正德二年(1507年)之前才是个寄籍锦衣卫的舍人,在刘瑾入掌司礼监后,官阶迅速飞腾,不数月即实授锦衣卫百户,世袭管事;不久又“冒功”升作锦衣卫指挥,管南镇抚司事。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病笃,刘瑾忙赶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替他乞恩,进官为都督同知,并赐本身、妻及三代诰命。这样入土时,就可以换身一品的袍子了。
刘瑾有位妹婿,叫孙聪。其父名孙逢吉,成化年间在陕西任佥事、副使,直做到按察使、布政使,后以“老懦不为”罢官致仕。孙逢吉一直在陕西做官,也算刘瑾乡梓的“父母官”,大约以此与刘家联姻。孙聪一说娶了刘瑾堂妹,一说娶了刘瑾同父异母之妹。可能孙聪没有功名,所以只做到“礼部司务”这样的小官;当刘瑾得势时,已经致仕。刘瑾与这位连襟的关系,亦存两说:一说“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则是刘瑾幕中之人,相当亲昵;而另一说,则称孙聪甚不为瑾所喜,有朝臣要抬举这位妹婿,还遭到他的无情讥责。
刘瑾还有一从孙(《后鉴录》作“侄男”),名二汉,却偏有术士妄言“二汉当大贵”,后来成为刘瑾蓄意谋反的口实与动机。
以上是刘氏男性亲属,此外还有二女。这两个女孩,其实是侄女,一说“兄女”,一说“弟之女”(更有一说为“从孙女”,当误)。刘瑾称为“吾女”,想必是极宝爱的。
二 太监府的两位美婿
刘府待嫁的,是二女中的姐姐。这时,有两人进入刘瑾的备选名单,一位是福建莆田人戴大宾,一位是陕西解元邵晋夫,他们都是“弱冠登第”的少年才子,上京来参加会试的—“谀者争以二人姓名进”。
刘瑾先相中的,是戴大宾。大宾,字寅仲,年方十九,才情优沛,尤长于“作对儿”,现存的佳对仍有不少。不知是否出于刘太监的关照,他一下就中了今科第三名探花,正当青春,就做了翰林院的编修。假若再赘入刘府,“穷状元”迎娶相府千金的旧套就要重演了。
只可惜一件事,使这桩婚事窒碍难行:大宾在家中早已聘下一位高氏女子为妻。
刘瑾何时知道这个情况的,不得而知,但有史说他立刻起了恶心,要“夺其(大宾)旧聘,以弟女妻之”。正好有位叫张嵿的官员出知兴化府(莆田县属该府),刘瑾便主动“有所馈”,以此棒打鸳鸯事相托,却遭到张嵿的拒绝。为此触怒了刘瑾,遂摭拾他的旧事,将其削职为民。《明史》里有张嵿的传记,可他的传文里并没有这件光彩的“抗阉”记事,因而其真实性待考。
还有一种说法,说刘瑾看中戴大宾后,为其建邸舍,赠其车马仆从,极致殷勤。可是戴大宾却将与刘结婚视为畏途,为了拒婚,每日纵酒佯狂,并不时鞭笞刘瑾所赠之仆。仆从便跑到刘瑾面前哭诉,说大宾为人轻薄,不是致远的大器,渐渐地刘瑾就不提这件婚事了。正好大宾闻母丧,急忙出京归乡,不料卒于途中。
戴大宾纵酒是真,评语却另有一种,说他知道中了刘府的雀选,“意气殊洋洋,纵酒不检”。士人参加科举,都需要在试卷中填写姓名、年龄、籍贯、三代等信息,中举后刻印梓行的《同年录》,也要详细登载,而戴大宾的《齿录》(即同年录)里,关于婚姻,明白写道:“聘高氏、刘氏。”戴大宾不离高氏(或许还未及离),又纳刘氏,并恬然书于同年录里,为天下士人所笑。
戴大宾终究没有做成刘府的女婿,除了他为人轻浮,还因有人对刘瑾说:“莆田山川风气不佳,本朝福建中大魁者已有九人,然仅一人至少詹事,一人至祭酒,四品而已;余者止修撰,皆夭,少显贵者。”说的是戴大宾非寿永之人。于是刘瑾始有悔意,对人说:“我不可做牛丞相。”牛丞相的典故出自戏剧《琵琶记》,讲的是秀才入赘相府的故事,刘瑾这么说,含有对这桩婚事不再强求的意思。这话传到大宾耳朵里,遂请假归乡(一说奔母丧),不幸半路病死。正应了“福建大魁”非夭则不令终的魔咒。
此事不谐,刘瑾转而属意于陕西解元邵晋夫。邵晋夫,名昇,人称其“才调超逸,能诗”。他是凤翔人,与刘瑾算是大同乡,年仅十六岁,就中了丁卯(正德二年)陕西乡试的魁首(称“会元”),但此番会试却落了第。
戴大宾被排除后,他才进入刘瑾的视野。刘瑾说:“(邵晋夫)吾关中人,(吾女)归邵生,其可!”但邵晋夫对与刘氏缔婚,并不引为荣幸,反而“踯躅呼天,百计求免”。这不难理解,虽然刘瑾权势熏灼,但毕竟是阉宦,士人对与之联姻,难免有些心理障碍。
但不管邵晋夫如何抗拒,事终“弗得”,还是做了刘府女婿。但他婚后,并不依仗刘瑾的势力,胡作非为,而是“乃克自树立,略不与一人通,终日闭户,拊膺读书而已”。所谓种因得果,他的这种高蹈行为决定了其后的命运。
刘瑾还有一婿,名叫曹谧,娶了二女中的幼者。曹谧也是陕西人,其父曹雄,任延绥总兵官。《明史・曹雄传》说他“以瑾同乡,自附于瑾”,而瑾亦“欲广树党,日相亲重”。当时总督三边的兵部尚书才宽御寇被杀,曹雄拥兵不救,事后“佯引罪,乞解兵柄,令子(曹)谧赍奏诣京师。瑾异谧貌,妻以从女,而优诏褒雄,令居职如故,纠者反被责”。曹谧不知相貌何异,他的身份是纳粟监生,大约在将门之子的英伟中又透着几分儒雅吧。其兄曹谦,就“读书能文,有机略,好施予”。
才宽兵败被杀在正德四年(1509年)十一月,故曹、刘结亲当在五年之初。刘瑾以曹谧为婿,数为之坏法。正德五年平定宁夏藩王朱寘鐇之乱后,刘瑾又以私爱,将平贼功归于其父,进曹雄左都督,而改曹谧官为千户。
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刘瑾令侄婿弃文从武,想必是打算找机会让他冒功,在官阶上速进吧。
三 翁婿俱败
刘瑾为侄女择婿,又为之操办婚礼,其时举朝“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许多大臣,为了赶着给刘家送礼,竟然连天子的早朝都耽误了。
可是,正当刘瑾势如骄阳时,突然坏了事。
先是宁夏的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为帜,起兵造反。太监张永受命监军出征,很快平息叛乱。但就在大军班师还未到京的当口,京城里忽然传出流言,说刘瑾欲趁八月十五日为其兄出殡之机,尽捕送葬百官谋反。这样的流言太可怕了,应该出于政敌的诬害,而非实情。这位政敌,很可能就是同为太监的张永。两人皆有宠于上,在正德初年同入所谓“八党”(朝臣拟出的八名奸佞宦官,以其为一党),但他们素来不合。此前张永出征宁夏,在那里与著名大臣杨一清设计,要诛除刘瑾。所以张永未回之先,流言就出来了;而他到京的当晚(就在十五日,因刘瑾之兄尚停柩在室,防范稍疏),就在皇帝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上密奏刘瑾不法十七事。正德皇帝初时还在疑信,但很快就查有实据(如术士言刘二汉“当大贵”,家藏伪玺、兵器、过宫牌等物;特别让正德惊惧的是,刘瑾经常手执的大扇内藏有两柄利刃),又抄出刘瑾家财达数百万之巨,令皇帝大怒,而张永等趁皇帝之怒,不容其缓颊,即于二十五日用极残酷之刑将刘瑾处决了。
刘瑾是谋反重罪,按律人口家财也应“抄提”。此时刘景祥穿着新得的一品武职冠带,端端正正躺在棺材里。抄家者将其拖出,毁裂衣裳,弃置于路,旋即“追削其官,焚其尸”。刘氏满门被逮,不单“亲属同居人等”,就连远在兴平老家的族人,也械解到京。
其时,因“变起暴猝,人人持意行法”,判决多不当罪。如刘瑾实无谋反之事,他自己起初也以为至多贬谪到南方,“犹不失为富太监”。可是他当权时得罪人太多,至此众人皆来推墙—“公议大逆无道”,必死无疑了。谋反是灭族大罪,但依律,未成丁者犹可免死。治狱者对刘二汉如何处置,拿不定主意:“瑾从子二汉者尚幼,众疑其诛,且宽之。”最后刑部主事张文麟一语定谳,他坚决不同意宽贷二汉,质问说:“瑾为谁反邪?”他的道理是:刘瑾造反,皆为此儿(术士言二汉“当大贵”),此儿为祸由,岂能逃死。这虽是强词之理,而“二汉竟坐诛”。
刘二汉临行之前,呼出一段“口号”,被《明史・焦芳传》活灵活现记录下来:
二汉当死,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
大学士焦芳与吏部尚书张彩都入《明史・阉党传》,是刘瑾之党。张彩死于狱中,仍戮尸,焦芳则幸运,还乡安老而已。但我很怀疑此条记载的真实性,二汉尚在稚龄,怎能说出“吾死固当”之类的话;况且他被判处死刑,本出法外,怎是“固当”呢?这不过是时人欲借二汉之口追论焦芳,做的一篇小说罢了!
张文麟虽为二汉之罪人,却又为刘瑾众多族属的恩人。因刘案被逮的,除了近亲,还有“他族属”约30人,都是“既经别籍”,即已分户自立者,包括从老家兴平逮来的疏族,据时人目睹,“皆农人”。这些乡下种田人哪里讨过刘瑾什么好?但“深祸者穷治”,欲一概从坐,惟张文麟“独多所裁正,虽尚书亦自谓不如”,使许多人免于死亡。—这当中,或许就有刘瑾的两对侄女及其婿。
长婿邵晋夫,有一种“传奇”,说他“携妻遁去,后辗转襄汉间(今湖北襄阳一带)为娼”。正德十二年进士、诗人王廷陈曾作《闻筝诗》,写一“楚馆名娃”,善弹秦筝,繁弦每寓哀怨—“曲终仍自叙,家世本西秦”。据解,王诗“正咏其(刘瑾女侄)事”。
这故事虽然催泪,却属野语,晋夫之妻并无入楚之辱。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9《济风救难》载:“瑾败,有司逮(邵)昇。”他急忙跑到好友刘佐家里躲起来,藏了几个月:
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佐)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与瑾事,我知之。夫不权其是非之原而轻背其友,岂仁者乎?”卒脱昇于难。
刘佐有救难之德,在他的义护下,邵晋夫逃过一劫。但他得以“免诛”的根本原因,实因他“不与瑾事”,没有倚势播虐的恶行。尽管如此,仍不免“斥为民”,失去了功名。
朱国桢的记述得到著名文人康海为邵晋夫亲撰的墓志铭的印证。据《有明诗人邵晋夫墓志铭》载,刘瑾诛后,“天子以晋夫无所预事,赦为编民”。邵晋夫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十七日,在他44岁上病死于凤翔家中。康海在墓志中写道:“(晋夫被除名后)关中缙绅士夫莫不重以为冤,而晋夫洋洋粹粹,曾无少动于中,险夷不改,宠辱不形,厥觌渊矣。”确乎一位有涵之士,难怪明朝人都叹息他的早夭,称之为“犯忌才之阨”。这篇墓志还提到:“所配谈氏,无子。沈宜人(邵母)为置二妾,亦无子,乃以党氏妹之子延正为后。”这位谈氏,即应是刘瑾之女姪,邵晋夫之原配。但文字甚简,只可知谈氏已先其夫而卒,余则不可晓矣。
至于刘瑾的另外一位侄婿曹谧,改千户未数月,他妻翁就事发了。其父曹雄被言官交劾,降官下狱,遂“以党逆论死,籍其家”。他的哥哥曹谦在狱中为仇家捶死。但不久曹雄得到宽宥,诏“与家属永戍海南,遇赦不原”。曹谧的结局,于史无征,大约携其妻子刘氏(或复姓为谈氏)远戍天方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