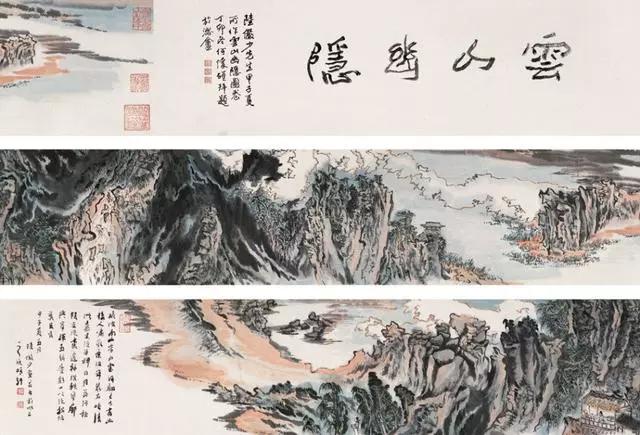今年过年回家,只好投奔了哥哥。父母不在人世了,总觉得无家可归了。住了一宿儿,就准备返程了。临走前我突然决定去看看小叔小婶。父母病重时,小叔来看望过,小婶也来看望过。但是,他俩从来都是各来各的,从不一起前来。“他俩还那样?”我问过母亲。“打一辈子!”母亲感慨地说。

小叔与小婶儿是包办婚姻,自打相亲见面,看了第一眼,小叔就根本没看上小婶。“驴脸瓜搭,呲牙咧嘴,整个一大马猴子!”其实,小婶儿虽说不算俊,但也不算难看,就是脸有点儿长,牙有点儿大。小叔长得也一般,不是啥帅小伙。就是爱打扮爱臭美,整天自己打扮得人模狗样的。七十年代大队有文艺宣传队,小叔儿是文艺演出队的骨干。演出队里有漂亮俊俏姑娘,小叔儿一心想找个俊媳妇。可是他惧怕爷爷,婚姻由爷爷作主。结果爷爷一句话,婚姻就定了下来。想娶个俊媳妇,哪成想,偏偏娶了个“大马猴”。心中一百个不愿意,但只好凑合着过。
爷爷在世时,有爷爷镇乎着,小叔不敢炸毛。小叔与小婶还过几天消停日子,并且生了两个儿子。可是自打爷爷去世,两口子就不断地发生战争。大打小打,动嘴打动手打,白天打晚上打,屋里打屋外也打,总之打了一辈子。但是就是谁不提离婚,而且谁劝离婚都不好使,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夫妻间打架次数多了,没人觉得稀奇,也没人去劝架拉架。儿子懂事了,俩人一打架,儿子就拉来奶奶镇乎一下。我们两家村东西头住着,我很少去小叔家,倒没怎么亲眼见过他俩打架。
只记得我七岁那年,到奶奶家玩耍路过小叔家,远远就听到小婶杀猪一样的哭嚎声。我刚要离开,突然小婶蹿了出来,一手捂着头,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臂流了下来,我吓了一跳。出生以来,就怕见流血,看小婶流了那么多血。我吓得折身往回奶奶跑,到了奶奶家,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小叔,小叔——”“这瘟死的,一点也不让我省心!”奶奶一边叨咕着,一边奔小叔家蹒跚而去。听说这他俩打得厉害,小婶动了笤帚疙瘩,小叔也动了板凳脚子。之后小婶儿跑回了娘家,娘家人都劝她不要跟小叔儿过了。可是不久小婶又回来了,小叔儿说“打不散,那才是滚刀肉呢!”
其实,小婶儿很能干,真心实意地过日子,一天到晚在地里忙,除了吃饭很少进屋休息。一到秋收,别人收完了庄稼,小婶儿就开始更忙了,每天逐个地找别人收剩不要的粮食。今天背回袋子玉米,明天拎回半筐麦穗。今天挖回一袋子土豆,明天捡回半筺蒜头……。小婶儿就是不喜欢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每天她家的饭都比别人家晚。家里来客,一般都是小叔儿做饭做菜。家里的衣服都是小叔儿洗,洗完衣服就收拾屋子。小婶儿每次看到小叔做这些活儿,不是说“穷干净”,就是说“瞎得瑟”,两个人的战火常因这些小事儿而点燃。
现在小叔儿小婶儿都过了古稀之年了,七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时不常地还打上一仗。不过,这回胜负颠倒了。小叔得了脑血栓,不能自理,经常尿裤子拉裤子。小婶虽然还伺候他,但也没好声没好气。一打起架,小叔哆嗦着嘴,直冒沫子,也没冒出一句话,小婶倒是直着嗓子妈了个痛快,急眼了,好给个巴掌撇子。小叔见了我,哆嗦着没说出什么,只掉了几滴眼泪。从小叔家出来,我十分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