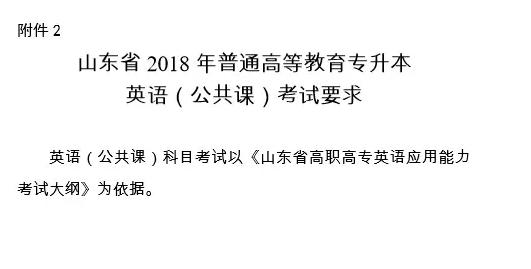摘要:“土豪”源于微博段子,现已成为当下走红的网络流行文化—“土豪文化”。此种文化现象有着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本文从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度阐释。对“土豪”这一当下人气极高的网络文化词语进行“全景式浏览”,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土豪;身份“反转”;文化隐喻;社会土壤;自嘲心理

“土豪”一词源起于2013年8月初流传的一则青年和禅师的问答笑话[1]。随后田东宝在微博上发起“与土豪做朋友”以及“为土豪写诗”活动,催生了“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句极具敏感性的网络流行语。而后借助于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迅速形成“蝴蝶效应”,再次加剧了“土豪”的走红。9月21日,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正式在中国市场推出新一代“土豪金”手机iPhone5S。9月22日,“土豪盛宴”和“豪莱坞”庆典在山东青岛举行。10月3日,“土豪丈母娘”在安徽马鞍山诞生。11月15日,武汉市拟出台“土豪政策”[2]。与此同时,“土豪”走出国门,成为BBC探讨的话题,并有可能获牛津英语词典的认可。一时之间,“土豪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行业壁垒和国界,将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土豪了”。从文化逻辑的视角看,“土豪文化”既意味着“土豪”在政治身份上的“反转”;又隐喻着粗俗文化和精致文化的混搭;它是社会阶层固化后普通大众寻求上升通道的变相反映;又是国民性自嘲心理在“后高富帅时代”的再次浮现。对“土豪”这一当下家喻户晓且影响广泛的文化词语进行“全景式浏览”,深入探求“土豪”的文化隐喻、内在机理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理论思考,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土豪”的身份“反转”:从政治打压对象到时代宠儿“土豪”一词,早在南朝即有记载[3],在宋朝文天祥[4]、清代顾炎武[5]和郝懿行[6]的著述中亦有所涉及。直到民国时期,“土豪”才作为一个政治身份并作为政治上被打压的对象登上历史舞台。但在当下,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标志着“土豪”在政治身份上“华丽转身”,成为消费时代的宠儿。1.近代革命史中的“土豪”:政治打压的对象土豪被打倒在地,再被众人踩踏,与近代的政治局势有关。民国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巨变阶段,土豪劣绅乘隙以团练武装为权力基础,以农村为“据点”,欺骗中央,勒索百姓,建立“隐蔽”的潜在地方政权。1924年,国民革命将土豪劣绅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后,在积极镇压共产党人和农民运动的同时,仍坚持以反帝反封建为口号,在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和党部对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剥夺士绅阶层的传统权威,从而将国家政权的权威渗透进基层乡村社会[7]。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土豪劣绅的称谓加之于那些大肆进行高利贷剥削的农民暴发户”,即以剥削为生存法则的基层乡村社会精英。但在实际运动中,土豪劣绅的定义演“土豪”一词的文化逻辑审视变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即将土豪劣绅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传统乡村社会精英。国共两党之所以发起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主要是大革命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地方,由于传统精英势力凭借其崇高的威望仍然在基层社会占据着权力的舞台,新政权并不稳固。对国民党来讲,建设新秩序与铲除旧势力应该是同步的,但是国民党的妥协性使其最终并未完成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整合[8]。也就是说,国民党并没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它只是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城市型上层执政党”。因而,中国革命的担子就自然地落到走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2.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土豪”:时代追捧的宠儿改革开放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被否定,到20世纪80年代初,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一系列政治“帽子”全部被废除,“土豪劣绅”这种政治标签就此终结。而与此同时,随着所有制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以及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开始重新分
层,财富和金钱成为社会分层和衡量人们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央施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富裕群体。这个群体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开发商,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100人中,有近半数的人涉足房
地产。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9]的前20位巨富中,有6人从事房地产行业;前100位富豪中,有31位富豪来自房地产行业。这些房地产富豪以较低的价格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土地批租权,再用银行贷款建设房屋出售,在高房价的形势下成为巨富,成为货真价实的“土豪”。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调民主;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的普通大众不再谈论沉重的历史和未来,也不再信奉虚假的道德说教,更不愿意进行毫无实用价值的沉思默想,他们推崇财富,关注当下轻松、自在的快乐生活,因而对“土豪”背后的革命话语“既往不咎”。基于此,前工业社会中的“土豪”在后工业社会摇身一变,成了时代的新宠。与此同时,“土豪”这个词击败“高富帅”和“白富美”,强势登场,成为娱乐圈、财经界和互联网的谈论对象。加之国人对金钱的崇拜和对权力的向往—黄色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掌控生杀予夺的封建皇权,于是“土豪金”广受追捧。
二、“土豪”的文化隐喻:粗俗炫耀与精致诉求的混搭文化即人化,是人用来弥补先天本能不足的一种“后天的”、“人为的”行为规范体系。流行文化作为20世纪以来新兴的大众化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它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流行趣味为引导,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原先丑陋的、令人憎恶的“土豪”,现在则成为流行文化消费的主题,并且人们不再感到震惊,而是争相追捧。为此,时下正流行的“土豪文化”,是刻意炮制出来的以博欢心的“文化产业”,它和消费本身已经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借助于全球化的互联网技术,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与无意识领域。土豪文化作为当前的流行文化,就其精神属性而言是“土”的,而在其物质形态上又表现为“豪”。
1.“土豪”的精神文化层面: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炫耀性消费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土豪”表达自我,建构身份的重要手段。土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炫耀性消费,既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又刺痛了社会中下层的神经。与普通大众的消费不同,土豪的消费不再是“物的消费”,而是一种“符号消费”。土豪作为一种追求“文化和符号”的动物,他们更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即附着于商品的地位、身份以及权力等价值。“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10]。土豪的符号消费注重新奇性、话题性和意义性等符号媒介,借助于这些符号媒介,土豪希望促成自我实现、寻求文化认同并将一定的社会关系意义赋予自身。对于土豪而言,“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11]。土豪消费的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而是寻求差异性,对这种差异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建构社会地位
消费主义在当下的盛行,迫使人们以金钱为最通用的价值符号,以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来标识人生意义。现代社会和当前的流行文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规训”人们的价值追求,刺激了人们对差异消费的需要,使得“财富和产品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经济系统(这是需求和生存的生理层次)被符号社会学系统(消费的本来层次)取代⋯⋯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12]。这一转变导致了消费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层意义:一个人属于哪个阶层,取决于他消费了哪个阶层的东西。“消费文化中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其中的核心便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会以不同方式去消费商品”[13]。人们通过消费“确证”自己的社会等级,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身在消费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土豪使用和消费商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通过高调炫富,展现其个性、品位、生活风格,希望赢得“高富帅”和“白富美”的认同;另一方面,借助于展示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将自己与“屌丝”阶层区别开来,以构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2)爱面子
“面子”指的是通过成功和炫耀获得的一种尊敬、自豪和尊严,是运用一系列复杂的社交技巧以维护个人的颜面的结果。面子是一个依赖性自我概念,强调社会角色和公众感知,并将其作为个人身份的核心。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往往家庭、亲戚和职业也用于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土豪为了提升社会声誉,常常为了“顾面子”、“增加面子”,通过消费有形的、具有象征价值的奢侈品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并获得社会的赞赏。另外,在人际交往中,礼物作为人情和面子的载体,被广泛运用于向他人表达尊敬和尊重,建立和维持着社会关系。土豪通过赠送奢侈品,既表达了对礼物接受者的尊敬,又带给自身一种自尊。
(3)寻求身份认同
身份标识着个体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它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来划分。在中国,身份制作为意识形态是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部分和重要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它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凝成一种情结。在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消费在加强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导致了“身份焦虑”。人们从消费商品转化为消费符号,“通过融入符号的意义体系以寻求身份认同”[14],使得符号消费成为标识个人身份的外在手段:一个人的消费内容、消费方式和消费态度,表征了其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人格类型。“在工业社会中,身份与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身份源于职业或专业。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大量增加,经济与政治机构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有了脱节。结果,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15]。土豪的炫耀性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需求,而是为了夸示财富,是符号消费强化身份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凡勃伦认为,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必须将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或权力展示出来。由于土豪渴望“被认为是富人”,希望自己成为“高富帅”和“白富美”中的一员。为了缓解这种“身份焦虑”,土豪模仿富人“我买故我在”的消费模式,在“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驱使下,土豪期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与富人群体建立联系,实现身份伦理上的认同,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
2.“土豪”的物质文化层面:豪
“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16]。在消费社会,人们开始赋予金钱一种新的道德含义,使得“占有”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品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他们就是比别人优秀。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着土豪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他们购买商品的目的在于通过夸富式炫耀,博得社会艳羡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为了显示身份、挣面子,土豪之间互相攀比的炫耀性消费愈演愈烈。和民国时期的土豪不同,如今的土豪足够新潮足够炫,养宠物不再养小猫小狗,而是养老虎以彰显身份[17];买钻戒首饰,网购土豪更是一掷千万金[18];男女定亲,土豪送上888万现金[19];买车代步,土豪大妈背金条支付[20];为向女神求婚,扬州“土豪”特意订制万元人民币的花束[21];结婚送彩礼,东阳土豪1080万礼金[22]亮瞎“屌丝”的眼;炫富摆酷,DanBilzerian晒出一挺挺枪支[23],浙江土豪更是开着坦克霸气现身[24];穿礼服拍电影,土豪中意的是23万的皮草[25]。为了向土豪致敬,商家相继推出土豪金酒店[26]、土豪金厕纸[27]、土豪金宝马[28]、土豪金大道[29]、“土豪金”铜钱大厦[30]和土豪金自行车[31]。与此同时,中国最富裕的村庄华西村因其拥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和重达1吨的金牛而被戏称为“土豪村”。

“土豪”,已经借助于大众传媒而建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在精神形态上,它与“高富帅”和“白富美”形成了粗鄙与精致的对照;在物质层面,它与“屌丝”构成富裕与穷困的对立。土豪,就这样作为粗俗和精致的混搭,在国人的“羡慕嫉妒恨”中粉墨登场。三、“土豪”的社会土壤:阶层固化在社会学意义上,当下的“土豪”多是依托房地产而崛起的新富裕阶层。他们手中的iPhone5S类似改革开放时期暴发户的镶金牙,成为非公平状态下贫富两极分化的显著标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后,教育制度已经无法承载社会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功能,先赋性因素逐渐成为获取阶层地位的关键[32],后天的个人努力越来越微不足道,青年阶层出现固化现象。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已经难以在当下日益断裂的社会里再现。继“干爹”、“干妈”和“土豪丈母娘”之后,攀附“土豪”成为出身底层的“无爹可拼”青年“曲线救国”的新路径。
1.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33],白屋不见公卿社会阶层是根据人们的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状况等社会特征,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人进行划分而形成的社会地位阶梯。一般而言,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自由流动,这种流动可分为代内阶层流动与代际阶层流动。阶层固化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或非正常状态,是一种复制式流动。它涵括两重意蕴:其一是指代内阶层固化,即社会个体一生中的阶层等次没有发生变化,处于僵化与封闭状态;其二是指代际固化,即代际间呈现出阶层世袭化现象。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中坚和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阶层固化的主要体现者。青年阶层固化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上流阶层的“世袭化”。精英阶层中的多数将他们的社会资源或职业传递给下一代;(2)中间阶层的“下流化”。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无论采用陆学艺、杨继绳还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整个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的比重都偏低,并且他们向下流动的风险正在日益加大;(3)下等阶层的“边缘化”。处于十大阶层最后两位的是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青年;(4)夹心层的出现。由于公共政策不到位,出现住房“夹心层”、就业“夹心层”和心理认同上的“夹心层”。2.阶层固化后底层人员的出路—“土豪,我们做朋友吧”(1)拜“干爹”、认“干妈”和找“土豪丈母娘”在中国传统社会,非亲生父母而拜认为父或拜认为母,叫作“干爹”或“干妈”,亦称“义父”或“义母”。面对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对于不能“拼爹”的普通大众要想突破阶层壁垒,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必须寻找“靠山”—这些靠山,要么是握有军政大权的高官,要么是家财万贯、左右逢源的阔佬。而最便捷和有效的“依靠”途径,则是拜“干爹”、认“干妈”,这使得原本单纯的拟制血亲关系被涂上一层暧昧色彩。从早年港澳娱乐圈的潜规则,到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干爹干妈文化”迅速自官场、娱乐界向社会蔓延。很多“头脑灵活”的女人迫于现实的需要,拜认不止一个“干爹”;很多务实的男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拜认多个“干妈”。拜“干爹”、认“干妈”作为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已经成为混社会的“必修课”,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科学研究”。在拜干亲者看来,能认“干爹”,会找“干妈”,懂得“十钻千拜”,是一种本事,更是一门技术活。这种拟制血亲关系虽然是“干”的,没有“湿”的“血缘关系”,但多少是“靠”上了。当然,这种“靠”是“互相依靠”,是一种互利互惠、各取所需的好买卖:对于“干儿”“干女”而言,有“贵人”撑腰,自然也就有了“来头”,不用再见了谁都“跪着舔”了,而且身价立马倍增;对于“干爹”和“干妈”而言,做事也多了一个“帮手”,何乐而不为?这样,通过拜干亲“认祖归宗”之后,“干爹”“干妈”与“干儿”“干女”就成了“自家人”,根据“传统伦理”,人是自家的亲,自家人多多少少会“照拂”自家人,要“提携”也总会先“提携”自家人。封建的那套人身依附关系又甚嚣尘上。当然,除了走“干爹”“干妈”路线之外,还可以找个“土豪丈母娘”。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婚姻已成为明码标价的交易,使得隐藏在婚姻幕布之下的丈母娘可以刺激房地产,从而拉动GDP的增长。2012年5月国家统计局全国商品房的成交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首次置业购房者都是出于婚姻需要。但是,如果遇到“土豪丈母娘”,不但房子不是问题,豪车也不是问题,但必须“相貌英俊”[34]。(2)“与土豪做朋友”对于庞大的底层人员而言,“资质俊秀”、“相貌英俊”、“头脑灵活”并且“务实”,从而能够有缘拜“爹”、认“干妈”或找“土豪丈母娘”的终究是少数,更多“忠厚老实憨”的普通大众,只得另寻他途。而“钱多人傻”的土豪,无疑是最佳攀附对象。一方面,资质平庸的普通大众,已经难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35],而他们的社会资本又极其有限,缺乏广泛的人脉,够不着“干爹”、攀不上“干妈”,也无缘“土豪丈母娘”的青睐;另一方面,和“高富帅”、“白富美”不同,“土豪”之所以“土”,是因为他们本身深深地植根于底层人士之中。这样,在普通大众和“土豪”之间,最有可能建立“可及关系”。基于这一点,才在无数不甘被孤立,渴望成为“土豪”的“小伙伴”的普通大众之间流行起“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四、“土豪”的受众心理:“羡慕嫉妒恨”的自嘲在“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背后,表现出的是一种公众自嘲的生活态度。普通民众对于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阶层固化的残酷社会现实,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服从,只能以这句俗语表达个人的“羡慕嫉妒恨”—“羡慕”“土豪”有钱,“嫉妒”“土豪”机遇好,“恨”自己无能。
1.自嘲心理的历史根基
《说文新附》有云:“嘲,谑也。从口,朝声。《汉书》通用啁。”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自嘲作为一种言语策略,表面在嘲弄自己,实际上另有所指。就国人而言,自嘲者往往借助于表层结构贬低丑化自己、深层结构上美化抬高自己,在心理上实现一种自我肯定,从而实现“情感郁积的巧妙释放”。在中国古代,专制权力导致了文人的人性扭曲,文人为了抒发心中的郁结,纷纷自嘲。到了现代,人性虽然突破了权力政治的牢笼,但却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遭到了更深层次的压抑,因为一切关系都演变成为利益关系,爱情、亲情、信任、忠诚等传统道德都被物化。“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6]。

2.“土豪文化”中的自嘲—“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在土豪文化中,普通大众的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正是理想被挤压后对自身“无根性”的确认,同时也在吹捧土豪的同时,利用崇高与鄙俗、庄严与油滑的有趣混搭和互代,实现对自身和现代社会的解构,揭示了扭曲的人背后扭曲的社会。自嘲能制造一种娱乐,一种娱乐自身的娱乐。“为土豪写诗”、“如何与土豪做朋友”和“一起来做土豪吧”,都是“土豪文化”制造的一种娱乐。这种后现代式的娱乐拒绝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嘲讽自身实现一种直观上可以感受到的轻盈松弛、酣畅欢快。与嘲讽他人相比,解构自身,让自身成为娱乐对象来得更为“欢乐”。
普通大众在“土豪文化”中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真诚”—对“真诚”的自嘲。这种真诚并不标榜自身“高大上”,而是将自身世俗的一面暴露于世,实现对自身的解构,以求自我安慰。因为这种解构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故这种解构并不影响自身的重新建构,并不影响对自我的肯定。但是,“土豪文化”中最受自嘲的是“上进心”。“上进心”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是对理想的执着,对上层社会的向往。但在消费文化之下,金钱、利益对人性的异化更为极端,怀抱理想、拥有“上进心”的人,往往被断裂社会扼住喉咙。普通大众在逼仄的空间体验基础上,生发出了以丑角身份进行的自嘲,这种自嘲在“土豪文化”中表现为寻求“与土豪做朋友”,放弃自身的人格主体性,成为“土豪”的小伙伴,通过依附“土豪”来创造共同体,以证明自己和他人“共在”,从而确认自我的“此在”—与他人在这个时空中的共在。意识到自己只是社会阶层固化面前的小丑,这是“忠厚老实憨”的追梦人从愚蠢走向智慧的征兆。而阶层固化也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土豪”晒出来的一沓沓钞票以及隐藏在钞票背后的权力。

总的来看,“土豪”一词的流行不是简单由于网络助推使然,而是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并真实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土豪”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其一掷千金但品位较差,其虽能以金钱垒砌心理优势,使“屌丝”们在财富拥有上可望而不可即,却难免“土”字的调侃奚落。就消极方面而言,“土豪”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强化了新的“符号”等级观念;更加刺激了浮躁的消费社会,导致了社会上博取“好名声”的炫耀性消费的流行,诱发了攀比、挥霍、浪费之风,给“光盘行动”的实施带来了阻力。而通过符号消费来寻求虚幻的身份认同,是人格异化的表现。同时,围绕“土豪”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与土豪做朋友”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与“土豪”为伍成为另一种“附属身份”的炫耀。就积极方面而言,普通大众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内心却是为自己的“无能”而悔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励志,激励自己向“土豪”学习善于抓住机遇。基于此,普通大众与“土豪”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以调侃式的态度解构了传统的“仇富心理”,此不失为一种积极健康的对待财富的心理态度。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土豪”这一文化现象,切忌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1]土豪.360百科.http://baike.so/doc/299254.html.
[2]http://news.ifeng/mainland/detail_2013_11/16/31304822_0.shtml.
[3]南朝《宋书·殷琰传》:“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另有《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
边幅,而内行不轨。”
[4]《己未上皇帝书》:“至如诸州之义甲,各有土豪;诸峒之壮丁,各有隅长。彼其人望,为一州之长雄。”
[5]《与人书》:“马角无期,貂裘久敝,惟长者垂悯孤根不至为土豪鱼肉,即石田十顷徐图转售,尚得为首丘之计。”
[6]《晋宋书故·土豪》:“然则古之土豪,乡贵之隆号;今之土豪,里庶之丑称。”
[7]李巨澜.略论南京政府初期对土豪劣绅的打击—以江苏北部为例[J].学海,2008(5):170-176.
[8]陈明胜.革命话语的分歧:从1927年“清党”前后打倒土豪劣绅谈起[J].党史文苑(下),2011(2):8-10.
[9]http://baike.so/doc/7222495.html.
[10][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0-71.
[11]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56.
[12][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
[13][英]迈尔·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
[14]方珏.论西方文化理论的困境及出路[J].哲学研究,2011(3):80.
[15][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8.
[16]GuyDebord.TheSocietyoftheSpectacle[M].ZoneBooks,NewYork,TranslatedbyDonaldNicholsonSmith,1994,p16.
[17]http://s1979/caijing/guoji/201309/26102125226.shtml.
[18]http://news.hbtv/finance/2013/1113/601006.shtml.
[19]http://hbtv/2013/1113/600845.shtml.
[20]http://sxdaily/n/2013/1118/c73-5271680-1.html.
[21]http://hb.xinhuanet/2013-11/25/c_118273330.htm.
[22]http://news.yesky/hot/73/35442573all.shtml.
[23]http://qiyue/news/hot/20131204/8206.html.
[24]http://hb.xinhuanet/2013-12/06/c_118451202.htm.
[25]http://fashion.ifeng/luxury/detail_2013_12/14/32124905_0.shtml.
[26]http://hebei.hebnews/2013-10/21/content_3553155.htm.
[27]http://hebei.hebnews/2013-10/24/content_3561357.htm.
[28]http://culture.gmw/2013-11/12/content_9464203.htm.
[29]http://news.jxgdw/gnxw/2276594.html.
[30]http://news.yesky/hot/343/35498843.shtml.
[31]http://news.yesky/hot/489/35515489.shtml.
[32]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4(4):76-90;张翼.阶级阶层形成的
家庭背景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9(2):78-87;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J].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4):82-92;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1(6):121-135;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中国社会科学,
2013(3):4-21.
[33]http://360doc/content/13/0830/10/9736798_310908714.shtml.
[34]http://ccdy/xinwen/shehui/xinwen/201310/t20131005_770575_1.htm.
[35]费翔.规模扩张的背后—分层的高等教育和断裂的社会[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9):1-5;刘宏伟,刘元芳.高
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社会资本分析[J].高教探索,2013(4):124-127.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7期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