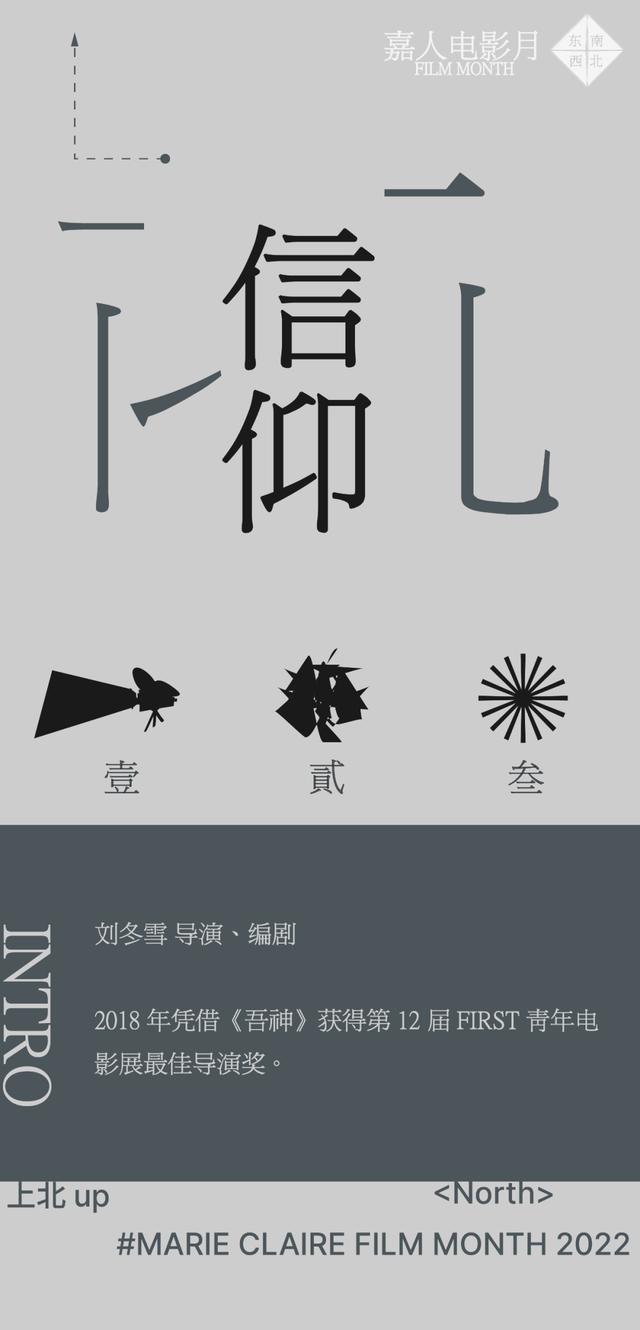
青年导演刘冬雪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吾神》,从一场葬礼、一次中邪,铺展开一幅北方乡村图景,探讨了令人困惑不已的东北民间信仰。再度回望这部作品,她直面当时的青涩和局限,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刘冬雪的家在吉林省公主岭,位于长春市和四平市之间。幼年的记忆中,家里的物质条件是很充沛的。爷爷在电机厂,奶奶是药厂的科长,姑姑、爸爸都在工厂工作。奶奶经常出差,有一次从南方带回几个杨桃,刘冬雪拿到学校让同学们猜,没有人认识。她得意地说:“这是一种水果,五角星的水果。”
那时的东北十分繁荣,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唱歌跳舞的,滚轴溜冰的。娱乐项目很丰富,各个年龄层都有。爷爷奶奶爱去戏院看二人转,扮相讲究、穿戴齐整,唱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演的是传统骨子老戏。而年轻人听流行歌曲,喜欢在广场唱卡拉OK,几毛钱就能点一首歌。
皮草大衣 GIORGIO ARMANI
刘冬雪的妈妈是裁缝,一直喜欢服装设计,订阅了当时中国仅有的时尚杂志。按照国外秀场服装的样式,自己画图纸、裁衣服。家里重视对刘冬雪的文艺培养,她在学前就上了各种课外班,跳舞、弹琴、画画、书法,都有。小学三年级后,大人让她挑一个最喜欢的,她画画的天赋最突出,就一直学了下来。
读到初中,老师建议刘冬雪学艺术,她第一次离开故乡,考上了吴作人美术中学。整个高中时期,她的成绩都非常好。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有美术基础是很大的优势。这一路似乎走得很顺,但刘冬雪不这样认为。“观察别人的生活轨迹时,会觉得他好顺利,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中间有多曲折坎坷。”
黑色拼接连衣裙 CURIEL
黑色耳饰 GIORGIO ARMANI
考大学时刘冬雪报考的是美院的造型学院,出于对成绩的自信,她甚至没填第二志愿。一个同学出于好心,帮她勾选了其他几项。那一年分数并列的人很多,拿到录取通知书,看到导演系几个字,她难以接受。整个暑假刘冬雪都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军训时看到考入造型学院的高中同学集合,她心中感到巨大的崩溃,这种情绪弥漫了整个大一期间。
大二开始上专业课,有一天电影社组织放电影,她被同寝室的女孩拉去看。当时放的是娄烨的《颐和园》,进去时已经开场 20 分钟,看完电影刘冬雪像被激活了,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想做的事。“那种你特别向往的创作状态,在那天晚上,电影全部给你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漆黑的教室里,她窥到了电影艺术的光。第二天早上醒来,所有阴霾都散去了。
大学毕业后刘冬雪进入广告公司,从商业短片拍起,再拍微电影,不断磨炼技艺。跟着孙周导演做了两年编剧后,刘冬雪萌生了拍长片的想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写了很多剧本,但还是决定先拍《吾神》,一个反映东北民间信仰的剧本。“所有人的行为、语言、习惯,都是我从小到大非常熟悉的,很有把握。”
故事发生在东北农村,农家汉张全的母亲去世,举办葬礼时,一只黄鼠狼经过,棺材里发出响动,人说这是黄鼠狼“串气儿”了。想到母亲常年卧病,家中难以支撑,大全决定继续下葬,此后儿子却患上了难以解释的怪病。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张全开始向各路求助,萨满教、基督教、佛教,轮番上阵。
印花连衣裙 TOMMY ZHONG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刘冬雪回到老家公主岭的一个农村,那里是爷爷奶奶出生的地方,也有她童年的很多快乐。“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每年放假都回去,和乡下的哥哥姐姐到处跑,玩很多城市里没有的游戏。一到冬天,到处覆盖着积雪,冻成一条结实的滑道。我们就玩儿爬犁,能从一个村滑到另一个村。”
创作团队都是刘冬雪的同学,大家都工作了七八年,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急切地想要做一个像样的东西出来。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义无反顾地跟她来到东北。拍摄时几乎全家总动员,一个远房亲戚的姑妈专门来给大伙做饭。整个村子都沾亲带故,所以他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拍完戏回去自己烧炕,晚上睡觉还冻脑门儿。“没有人抱怨,所有人热火朝天的,带着全部的热情。”
印花连衣裙 TOMMY ZHONG
片中出现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多来自于当地二人转剧团。刘冬雪认为,演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熟悉故事里的一切,多年的舞台经验又赋予了他们极强的表现力。“我把我们市二人转剧团的演员全部拉来加入这部戏,开拍前在剧团一起读剧本、排练,在现场我会尽量帮他们适应镜头。”演瞎子大仙的演员不识字,背不下台词,但是会“跳大神”的人只有他了。“我站在镜头后,我说一句,他学一句,很辛苦地拍下来。”
后来村里有一个见多识广的大伯,在一间破烂的小酒馆里跟她说,“你做的这事儿特别有意义,当年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叫《中国》。而你的意义就在于,无论拍了什么,都是在记录东北农村人的生活。”
在刘冬雪的观察中,民间信仰渗透在东北的生活日常中。“一个城市,一个区片,会有这么一间‘医院’,里边有一个能给人看病、看事的人,人都说他身上有‘仙’,什么都知道。大家有什么事基本都去问,比如说孩子升学、考试,大事小情都能问。他看病时会果断地告诉你,你胃有毛病,你肾有毛病,去了医院就查这个,别的都不用查。”
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当时的刘冬雪只想通过电影探讨这种信仰和现象,四年后回看这部处女作时,她看到了自己那时的局限性。“人物线都是被动的,很机械,所有人和故事走向都成为我急切表达的工具。”儿子张大全是苦楚的,与他相似的挣扎在困顿中的人们,都是这片大地上的悲歌。
《吾神》中故事的最后,张大全到母亲坟前给她烧纸,实现了内心的和解。电影划开了一道对底层民众观察的口子,在东北农村贫瘠的土地上,生存无所依,精神也无所依,人们需要一种信仰或者神明来解决问题,也寻求内心的安慰。“原本可以从这个角度挖掘得更深,也有很多人给我提意见,我不是不听取,而是当时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黑色拼接连衣裙 CURIEL
黑色高跟鞋 SERGIO ROSSI
黑色耳饰 GIORGIO ARMANI
很多年后,她理解了那些困苦无助、找不到出口的人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人们总需要一点支撑,不管它是什么。”这几年因为疫情,她也一度慌乱过,有巨大的虚无感。“当你义无反顾全神贯注地拍电影,全世界却停摆了,电影院一个个关停,人们似乎不需要它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刘冬雪发现电影原来才是她的初衷,也是她的终极信仰和力量源泉。“很快我就坚定了,相信希望还会来的,一切都会过去,人们还是会看电影的。”
定下心来的刘冬雪,开始了下一部长片《郝悬没失常》的剧本创作。“这是一个都市白领出现精神失常,最终被治愈的故事。直指当下的生存焦虑,也探讨了内卷等话题。”这是和《吾神》截然不同的走向,但刘冬雪说,她想先卖个关子,“这依然是东北故事的延续,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它会是我永远的创作源泉。”
M.C.
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里的“东北气质”?
L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MV是在厂房里的一个下雨天,小朋友在爸爸所在工厂的院子里面奔跑,爸爸拉着小朋友在雨中互相拥抱。那首歌让我感觉夏天好像总是在下雨,只要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很多零碎的记忆。比如你在学校门口的小卖店买东西,经常看到中年男人买一瓶啤酒,泡一碗三鲜伊面,在那儿沉默着喝酒。我作品里的东北气质,就像那个MV里的雨,一种弥漫的、渗透的感觉。
M.C.
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几代东北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伤痛也时常在一些与东北有关的作品中出现,它对于你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L它的作用力是非常迟缓的,像一种慢速飘过来的毒气,等味道弥漫上来时其实已经持续很久了。我是在过了很久之后才发现大家都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方式,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分崩离析。我埋怨爸爸为什么不能给我买一双 200 块钱的轮滑鞋,我不懂为什么家里每个亲戚都在做着注定失败的、稀奇古怪的生意。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对于一直生活、工作在厂区里的人来说,下岗是难以想象、难以预料的一件事,以至于所有人都没有准备。
M.C.
你小时候是否见过或听说过一些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东北故事?
L我爸爸去满洲里中苏边境买了一条三万多块钱的狗,说是很名贵的品种,等狗又生了狗就能卖钱——他把养狗作为一种投资。有一天清早我打开房门,客厅里弥漫着低气压,低到让人窒息,他们说狗在生宝宝的时候死了。听起来很荒谬,是吗?在那种环境之下,很多人做的求生的尝试你都会觉得很魔幻,但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坚信那是有可能成功的。
M.C.
这几年“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特别流行,你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复兴”?
L这件事其实特别有趣,我们每年过年,上一辈很少提起下岗潮,反而是我和我表姐、表弟最常聊起那段时光。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当地各自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了什么样的挫败和煎熬,大家说着说着就在一起哭,而长辈们也不哭,也不提。可能很多80后都这样,我们一样的敏感、压抑,对环境无可奈何。青少年时又搞不清楚状况,这个东西长久积压在心里,有一天成为表达的动力,于是有了小说、有了电影,形成了这种“复兴”。
编辑/ 陈柏言ChicoChan
摄影/ 李银银
撰文/ 陈晶
造型 / 王乔
化妆/ RUI
发型/ ANDY
造型协助/ 杨小天
造型助理/ 李婧雯
编辑助理/ 吕胜、牟芝栢
设计/ enkit
排版/ 丽丽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