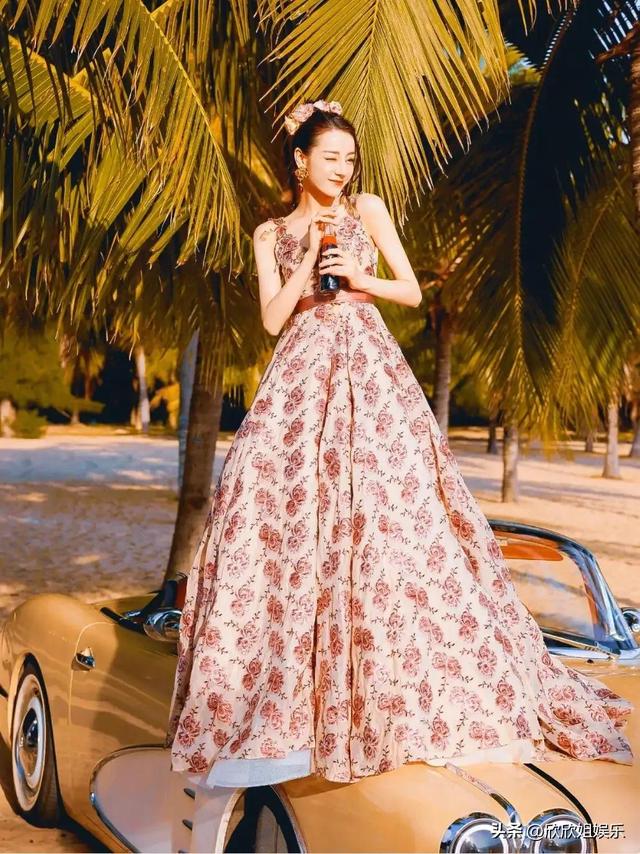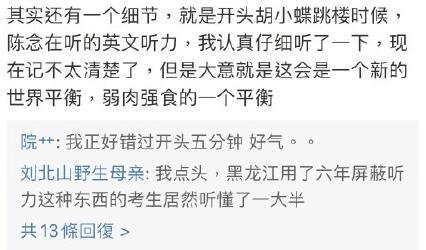文/陈路
日本的剑客文化非常盛行,并且从几十年前就通过日本影视、动漫产品的强大影响力向全世界推广,金庸对此也了然于胸,然而其作品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日本角色,比古龙、梁羽生的作品更加彻底,这可能是因为中日的侠客文化非常不同的缘故。

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者,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并称新武侠小说的三剑客。不过与另外二位相比,金庸的小说却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那便是在其中没有一个日本角色登场。而在古龙小说中日本高手众多,比如《楚留香传奇》里的天枫十四郎和无花,“迎风一刀斩”的日本刀法也让读者印象深刻。梁羽生小说里同样有扶桑高手:《龙凤宝钗缘》和《慧剑心魔》里的牟世杰。

楚留香系列里的天枫十四郎
要知道,在当时的香港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影响可是压倒性的。比如邵氏公司的武侠电影的形成与发展,便与日本剑戟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香港武侠电影中,往往少不了日本高手的身影。比如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便险些被塑造成一位东瀛高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龙、梁羽生笔下,自然也不会少了武功高超的扶桑高手的身影。
而尽管在日后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中,添加了大量的日本元素,甚至加入了倭寇这一历史背景。但是在金庸小说中,却完全看不到任何与日本相关的要素。这可以说是在当时新武侠小说家中,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
要知道金庸的小说格局很大,其笔下外籍人士不少,亚洲的有蒙古、朝鲜(高丽)、波斯、文莱,欧洲的有英国、俄罗斯、葡萄牙,但惟独没有一个日本人,甚至,日本这个词都没出现过。更奇特的是,在金庸以密宗为材料,塑造了不少武力高强的反派,如鸠摩智,金轮国师,血刀僧,灵智上人,桑结喇嘛,却独独漏掉了密宗的重镇日本。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反常的事情。
当然,金庸本人对此有过一些比较暧昧的回应,比如说认为日本剑豪小说没多少价值,日本文化不大值得重视等等。但是除了这些解答外,可能还有一个金庸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便是日本的侠客,与金庸笔下的大侠实在是极其不同的存在。
金庸小说中的大侠与政治关系紧密
1
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笔下的大侠总有着很深的家国情节。如郭靖先是为蒙古大汗征战四方,后又为南宋朝廷死守襄阳。再如萧峰,以死谏君王,为天下苍生免却刀兵之灾。
有人曾说过,自明清以来的侠义小说,总是调和为国尽忠(官府)与为民请命这两个极其对立的面相。
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和官府其实对立的。作为主要以非官方力量主持正义,“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困厄”的一群人,侠客天生接近乱世,疏远治世。只有乱世的失序和苦难,才能为侠客提供活动的空间。而乱世,又往往是和官府的恶政联系在一起的。
而侠客一旦投入这类政权的怀抱,当然让人不是滋味。在传统的侠义小说中,通常会以奸臣与侠义的对立,来转移侠客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所谓反奸臣不反皇帝,所以五鼠才会接受招安,投靠公正廉明的包大人,去对付为非作歹的襄阳王。由此,侠客们一方面能够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触及官府的权威。

金庸小说仍受到《七侠五义》之类小说的深刻影响
而到了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家们,依旧面临着如何调和官府与侠客矛盾的老问题。只不过在这里,侠客与奸臣的矛盾为民族大义所取代。《射雕》《神雕》里的郭靖就是金庸借助民族大义调和侠客和官府关系的典型。郭靖为南宋效力,主要原因不过是他是宋人。面对异族入侵,郭靖毅然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与早已腐败的行政系统合作抵御外敌。很明显,他是把民族大义置于铲除奸恶之上的。
更有意思的在于,到了其晚期作品如《鹿鼎记》中,民族大义似乎被天下苍生所取代。君不见,天地会的韦堂主最终不是反清复明与大清朝之间选择了效忠康熙爷么。他的理由无外乎康熙爷是位好皇帝,有他做皇帝,天下苍生的幸福才有保障。在这里相较于民族大义,天下苍生的幸福显得更为重要。而最能够保障天下苍生幸福的,则莫过于一个好皇帝。
由此,金庸通过由民族大义转向圣君贤相,实现了向传统侠义小说的回归。而由始至终,金庸都回避了对官府与侠客对立这一问题进行正面的回应。
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家国大义与民族大义而纠结不已。然而正是这些为国为民的大侠,却总是无一例外的回避了与政治体制的正面冲突。面对现实的政治体制,或者是如萧峰一样以死明志,或是如同韦小宝一样加入其中,最不济则是如张无忌一般,与政治划清界限规避山林。

金庸描写的侠客,大部分与政治有摆不脱的联系
或许因为金庸乃文化家族出身,其笔下的大侠们,颇有几分儒士风范。故而,其笔下的大侠们对现实政治体制的态度,与传统儒士颇有相似之处。
日本的侠义文化与政治决裂
2
在金庸笔下侠客那种家国情怀,以及对现实政治体制的纠结,在日本的侠客文化中绝难看到。或者说在日本的侠客文化中,绝难看到中国侠义小说或武侠小说中那种调和官府与侠客矛盾的纠结。因此,日本人一开始便很明确的将侠义之士定义为一切反体制者的总称。
这些反体制者未必如萧峰那样有着过人的武功,也未必如陈家洛一样有着神秘的身世与巨大的名望。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农民、町人、下级武士甚至浪人。但是却都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直接向现行政治体制发起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忠臣藏中的赤穗义士。
关于忠臣藏的原型赤穗事件,其本身比较复杂,故这里不做讨论。关键在于以该事件为原型所塑造的忠臣藏这一故事中,在主君蒙受不白之冤,而现行政治体制又无法为其主持公道,甚至政治体制本身便是加害者一方之时,赤穗藩的武士便选择以暴力诛杀主君的仇人。
这在维系了家臣对主君的忠义之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直接挑战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因此武士们最终唯有以切腹这一悲剧性结局收场。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直接挑战幕藩体制这一事实。
日本的侠客文化,不仅体现在忠臣藏等各种由町人创作的艺术作品中,也对明治维新之后的浪人有着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头山满这样的大陆浪人,还是藤井齐、安藤辉三这样的青年将校身上,都多少可以看到侠客文化的影子。无论对于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都难以否认他们身上那股为信义不惜身命,并且屡屡向体制叫板的侠义之风。
在战后的剑戟片、时代剧、时代小说中,依旧有着这种侠客文化的残余。
与同时期的香港新武侠小说不同的是,日本战后文艺作品中的侠客,通常都是普通的市井小民。如被国内某些自媒体称为日本“金庸”的藤泽周平,他笔下的武士,便都是一些最普通的下级武士,着一份极平常的工作,小心翼翼的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即便身藏绝技,也决不轻易示人。
再如热门时代剧《必杀仕事人》中的杀手们,日常都是普通的片警、裱糊匠、裁缝,日常生活不过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经营下自己的小生意罢了。
这些人如果放到金庸的小说中,大概就是星爷曾经扮演过的宋兵甲之类的角色。、

日本侠客的身份多与此人相似
而正是这样一些普通人,一旦当他人遭遇冤屈又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公正之时。他们便会站出来,施展自己的绝艺为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可怜人主持公道,甚至因此直接挑战公权力也在所不惜。
如《隐剑鬼爪》中的片桐宗藏便因为家老背信奸污友人的妻子,施展师傅所传授的绝技隐剑鬼爪将其暗杀。《必杀仕事人》中杀手们,则是拿人钱财为人消灾,那些遭受不公之人无论是拿出数两黄金还是几文钱,他们都为其洗刷冤屈,从恶德商人到贪官污吏,甚至一路杀到执掌国政的幕府老中。在完成这些壮举之后,这些日本侠客便深藏功与名,继续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日本的侠客不惮于杀家老、杀将军
尽管在这些日本侠客身上,我们看不到家国情节、民族大义,也看不到什么江湖恩怨,扬名立万。甚至连武功,也朴实无华。
相较于始终寄希望一位好皇帝,来为天下苍生谋求幸福主持公道的萧峰、陈家洛、韦小宝而言,日本侠客似乎自一开始就对当权者不保任何希望。故而复仇这种最古老的自力救济手段,便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故而日本的侠客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浓列的反体制色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世经常将家臣对主君的忠义,描述为一种单方面的,绝对的关系。从而将日本武士的忠义解读为捍卫现行体制的愚忠。但这种解释,完全忽视了日本所流行的下克上现象。实际上,家臣对主君的忠诚,从来都有着明确的前提条件。
战国大儒清原宣贤便宣称,尽管家臣对主君有着明确的责任,要对主君忠诚,但是相对的,主君也必须善待家臣,公正的给予家臣功勋相应的报偿。如果主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被家臣背叛也是理所当然。
这种御恩与奉公的关系,到了江户时代不仅构成了武士伦理的重要基础,也随着大量武士沦为市井浪人,而流入町人社会。转化为知恩图报,锄强扶弱,为信义不惜身命,甚至直接向体制叫板的侠义精神。
也即是说,日本的侠义精神与武士精神皆出自中世武士的伦理实践。故而后世也多将任侠与武士道共同视为武士伦理的继承者,甚至有人主张武士有武士道,町人有侠客道,两者共同构成了作为日本人精神的大和魂。
无独有偶,古代中国的侠客文化,也源于士的伦理实践。
先秦侠客在中国的没落
3
近代学人关于侠的议论颇多,大体而言,皆认为侠是由古代的士的转化而来。如顾颉刚便认为,侠与儒皆由士而来,尚文者谓之儒,尚武者谓之侠。而余英时则更进一步指出,侠乃武士的专名,但并非一切武士都能能被称为侠。只有其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到极致之人,才能被称为侠。
而何为侠的道德?在《游侠列传》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论述: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在太史公眼那些为信义不惜身命,急公好义,救人困厄之士才能称之为侠。
这些道德准则,无疑与日本的侠客文化中对侠所提出的要求颇为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孤狼一样的日本侠客相比,先秦任侠更像一个土豪或者是武士集团的首领。
如《游侠列传》中所列举的侠士,无论是出身高贵的战国四公子,还是朱家剧孟郭解,无论出身贵贱,大体都蓄养了不少武士。故而钱穆认为古代的”侠“还不是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存亡死生的个别武士,而是指这些个别武士的领袖,也就是赡养着这些武士的人。

先秦的侠及其在汉初的残余,才是独立之侠
但在秦制之下终于绝迹
而余英时也强调,任侠是一种团体,是与政治权威处于对抗性地位的地方势力。
不难看出,先秦的任侠,尽管在组织形态与内容上,与日本侠客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但大体奉行着相同的行为准则,并且始终处于与政治权威相对抗的地位。
只是不知由何时开始,在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与当代武侠小说,先秦任侠所否定的行为准则已经极为淡化,而反体制色彩更是消失无踪。所剩下的不是金庸笔下那些充满家国情怀的儒侠,便是古龙,梁羽生笔下超然脱俗的世外高人。反而在日本的武士小说与时代剧中,却尚能依稀看到一些先秦任侠的身影。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