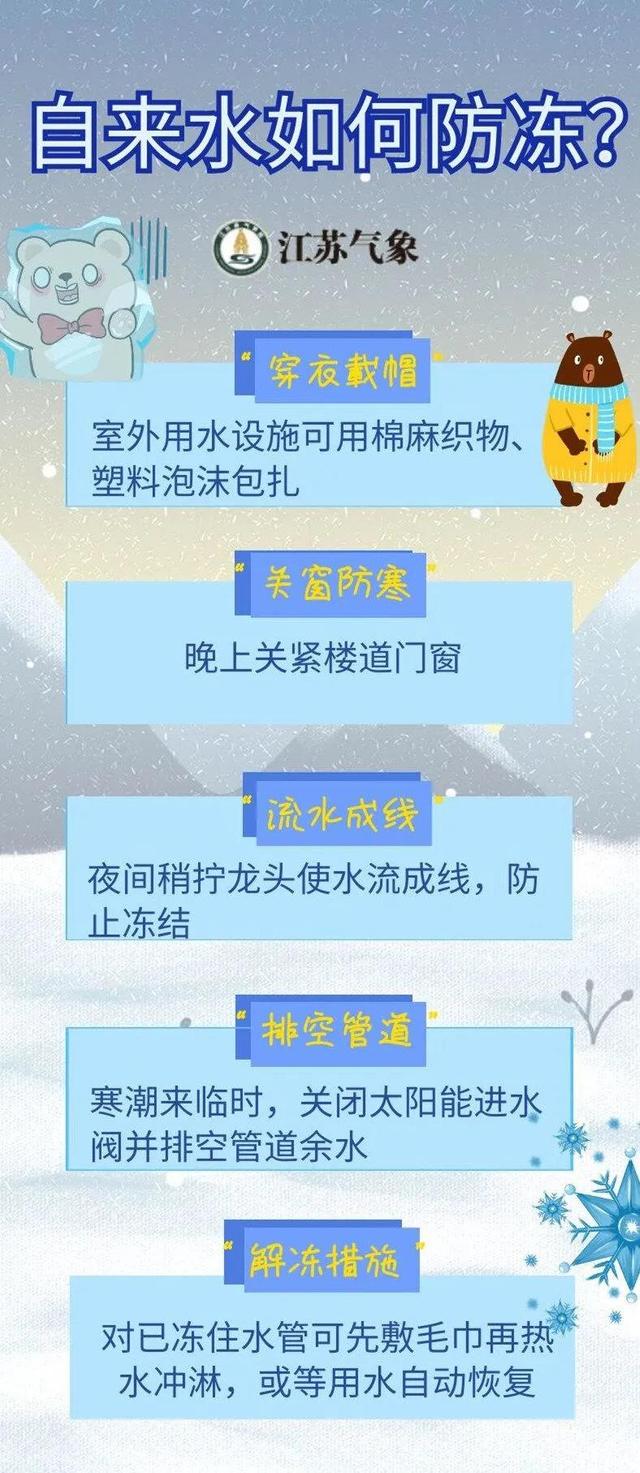我有个名叫“302 宿舍冷笑话”的群。本来叫做“302 宿舍五兄弟”,但老大一激动打成了五小弟,老三还建议改成“浪漫满屋 302”。这自然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抨击:“名字瓜兮兮滴,明显是韩剧看多咯。”
最终,在一个春风沉醉我也有点喝醉的夜晚,我把名称偷偷地改成了“302 宿舍冷笑话”。所有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大概是当时脑袋给喝秀逗了。
小群最大的好处是热闹。我们“2002 级国贸系”的群成员有 207 人,1 个月可能会说 30 句话,29 句半都是转发的消息,剩下的半句是“请为我的宝宝投上一票,谢谢同学们”。“302 宿舍冷笑话”一共 5 个人,1 天就可能会说 30 句话,29 句半都是互捧或是互掐,剩下的半句是“谁不说话谁就是傻 X”。
老二经常扮演那个“傻 X”。3 月初复工的时候,我发了条《生化危机3 重制版》上市的消息,顺手转了最新的预告片,群里瞬间就沸腾起来,除了默不作声的老二。不过,当初《生化危机3》的光盘却是老二买的,而那台被烟灰烫了一个伤疤的 PS 主机,也是老二的。

风水女孩
“老大”到“老五”并不是按年龄排序,而是按进入宿舍的顺序,我们原来不在一个宿舍,后来才搬到了一起。大一下半学期学校起了新宿舍楼,墙体白花花的,又偏偏铺了淡粉色的马赛克打底,像个刚洗完澡的胖子,皮肤下泛出腻腻的微光。
当时老大恨恨地说:“都是拿咱们的钱盖的,咱们才进来半年,学校的楼就盖得蹭蹭的。”老五回应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管他啷个多,住起!”
于是我们夹着被子、拎着箱子、提着盆子,往新宿舍跑。那天中雨,一路上刷牙缸子叮当作响,我们像群躲避炮火的难民。老二的东西最扎眼,一个包装甚好的箱子,还铺了一件蓝底白花的雨衣,露出的一角显现出一行英文 —— Sony PlayStation。
老三说:“呦呵,还是索尼的碟机,以后看碟方便了。”
老五赶忙附和:“啥子碟机嘛,明明是游戏机,玩实况足球巴适的很,是不是?”
老二没有说话,他用抹布抹了一把箱子上的几滴的雨水。老五感觉自己吃了个瘪,只能拿起一本《微观经济学》当笤帚扫去床上的灰。还是老大打了个圆场,叹了口气,幽幽的点了根精白沙:“唉,新环境儿的风水不咋地啊……”

新宿舍的风水其实很好,正对着女生宿舍楼,而我们这层又正对着艺术系女生宿舍。到了晚上熄灯前,总有悠扬的钢琴声从对面传来,而到了早上则换成了“咿咿呀呀”的吊嗓子,由此我们宿舍的全体同仁们,养成了晚睡早起的习惯。
不仅如此,我们宿舍还可以直接俯视“英语角”,其实就是卖二手书的地方。而卖书的同学当中,又以艺术系和法语系的女生最多,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概念太片面,应该说“卖书也有颜如玉”。
艺术系的女生卖书最优雅,她们的双脚会有微微的外八字,双手插在极短的卫衣兜里静静地站着,细腻的腰身就显得更加细腻。法语系的女生卖书最别致,她们边卖书边温习课文,唇齿间发出法语暧昧的小舌音。
我们都有买书的经历,都有一两本《艺术与审美》或者法语版的《悲惨世界》,书里会出现细密而娟秀的字体,或者手绘的小图案,致使我们阅读时常常走神,总是试着回忆起书的原主人长相如何,当时心情怎样,现在在干什么。
老二也买书,过程没有我们这么浪漫。他总是买游戏杂志,打交道的都是大老爷们。游戏杂志那时是最下等的存在,经常作为添头出现。比如买《围城》和《洗澡》就赠你一本游戏杂志,买套盗版的《张爱玲作品选》可以赠你 3 本外加配套光碟。
什么?不喜欢游戏杂志?那就送你个“热得快”吧。
都是限定版
但老二通过买书认识了不少人,这些人之后经常出现在我们宿舍讨论游戏。我们当时对于游戏的认识还停留在《红色警戒》《三角洲特种部队》和《反恐精英》上,因此老二和那些人的讨论,便成了大家有关游戏的“启蒙运动”。
说归说,做归做。
即便老二有着一套套有关游戏的理论,最后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上。拿《实况足球》举例,老二的水平极臭,经常被我用中国队虐到 3 比 0 以上,那年韩日世界杯国足的表现不好,我们便把虐老二的过程叫做“为国争光”。
虐的久了,老二当然不愿意,在以 7-2 还是 9-2 输给老大之后,他脸憋通红:“实况有啥好玩的,《生化危机》知道不?那才是顶级的游戏!”

我不知道《生化危机》是不是顶级的游戏,但我知道老二是顶级的“生化迷”。
有一年他准备出国,临行前请我们本地的同学喝酒。当时行李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家也快搬空了,两室一厅的房子突然有点儿荒凉。酒过三巡我们开始打麻将,老二那次手气特别好,连续好几把都是“对对胡”,以至于赢得太快自动麻将机都来不及洗牌,看着麻将牌庄严的慢慢升起,大家都有些漠然。
后来老二把我叫进了卧室,指着收纳柜里的东西开始科普:”看看!都是限定版的,全都是《生化危机》!”
我认真的看着,从《生化危机》主题的 PS、PS2、DC、显示器,一直数到《生化危机0》《生化危机1》……《生化危机6》。而《生化危机3》则被一个仿实木的架子抬高,刻意凸显出优越和庄重的感觉。

我问这些主机和游戏你打算咋办?他说先让他媳妇收藏着。我说你媳妇不跟你出去吗?老二说等站稳脚跟再接媳妇去。
气氛陷入尴尬,我打了个饱满的酒嗝,老二则笑着拍了我的后背一把。
“不对啊?这些都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我指着 DC 上的安布雷拉 Logo 说。老二又拍了我一把,很认真的回答:“对啊,我自己买的机器、我自己设计的 Logo,又自己印出来自己贴上去,当然得算是限定版啊!”

下一页:更多内容
《生化危机3》毫无胜算
限定版的概念为何暂不讨论,最起码毕业后的老二有时间折腾,不像上学时没有精力。
大四之前,我们的晚自习都要被点名,呆在宿舍里的时间极其有限,除了一日三餐的间隙。而在这宝贵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的给我们安利过《生化危机3》。
初次运行时他让我们不要进行任何操作,只为展现游戏的片头动画,于是我第一次看见吉尔苍白的脸和追击者那副畸形的牙齿,见证了特种部队有些愚蠢到惨烈的行动,以及整个浣熊市的破败和混乱。
“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去哪儿了?”当时老三这样问道。不怪他没看懂,要怪就怪《生化危机3》自己插了一段《恐龙危机》的宣传片。但最初的观感并不好,画面太小,用的电视是康佳小画仙。

解放办法是搬到自习室去,用自习室的大电视玩。但那里常年被“追剧党”和”看碟党“占据,稀少的电源插头则被“CS 党”默认为各自笔记本的私产。毕竟,自习室是晚上 9 点之后唯一的娱乐场所,唯一有电的地方。
当时的潜规则,是上完晚自习就聚到自习室看《夏娃的诱惑》或者《泡沫爱情》,实在不行就看重播的《刘老根》或者《西游戏后传》。我们对剧情毫无兴趣,也没想着要感兴趣,我们只对金素妍的嘴唇和金喜善的锁骨发呆,至于本山大叔的演技和《西游记后传》的鬼畜,也能让人兴奋到午夜时分。
跟它们相比,当时的《生化危机3》毫无胜算。老二和我们试过在自习室玩,没过 10 分钟就被赶下台,《生化危机3》的魅力甚至还不如《第 10 放映室》和《动物世界》,后俩个节目是“熬夜党”的 B 计划,周末的时候,他们就着两包恰恰和半打啤酒,能看到《夕阳红》播放主题曲。
所以,还得靠自己 —— 我们决定自己接电,官方说法是偷电。
夜间活动
这个任务依然由老二完成,开关、电线、螺丝刀、绝缘胶布的费用,老大则豪爽的表示由他报销,我记得是 13 元还是 15 元来着。
于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神情严肃地拉下的开关,宿舍顿时一篇光明,不幸的是自习室却瞬间陷入黑暗。于是金素妍、金喜善和赵本山的粉丝们齐声破口大骂:“哪个狗日的又偷电了!”
为了预防暴躁老哥找上门来,大家赶紧把空开合上,宿舍重新陷入黑暗,但是走廊灯和厕所灯又都不亮了。老二急得一头汗,脑门在黑暗里闪闪发光,老大重新钻回床铺点了根儿烟:“你当时是咋给奔波儿灞整的?”
奔波儿灞是老二的女友,眼睛长而细,若是做条延长线,感觉可以深入到眉梢,她不算惊艳但很有女人味道。至于奔波儿灞的外号,大概因为鼻梁稍微塌了一点点,又或是因为莫名原因被扣上的恶毒外号。恶毒的东西总是传播很快,辩解起来又太费工夫,所以奔波儿灞的叫法就流传开来,我们后来都叫她奔奔,她倒是一个劲儿的笑。
奔波儿灞宿舍里的电就是老二接的。求爱的过程没费太多精力,就是花费体力。那时老二每天要给奔波儿灞打水,一天 2 次,加上自己的 2 个暖瓶,像个练功的少林寺和尚。
我有时帮老二打水,打着打着奔波儿灞同宿舍的小姐妹也蹭着让我帮打。不过也算不白打,那个小姐妹经常会给我一袋锅巴,或者几个泡椒风爪,每次说吃嘛吃嘛,然后硬塞到裤兜里,我后来在背后叫她“灞波儿奔”,因为这样比较好记(名字的排列换了一下,其实是个梗)。
那时老大和老三、老五经常帮着老二打饭,每次看到老二打完水坐在宿舍的桌子上吞咽午饭时,大家都笑着调侃:“哟,降妖回来了?”
宿舍后来终于有了电,即使有嗡嗡的电流声,但听上去是种很踏实的存在。来电后的夜里奔奔经常来,和那个小姐妹一起。
夜里的主要活动自然是打游戏,通常以《最终幻想8》作为开场,因为奔奔喜欢。面对一堆暧昧的日文和暧昧的一对人,我们常常表示无奈,只能吃着小姐妹带来的锅巴和泡椒风抓,黑暗里一片卡茨卡茨的声,伴随着饱满而油腻的酸辣味。
保留节目自然是《生化危机3》,老二每次都虔诚的将碟放进,并且每次都要把开场动画看完,更为无奈的是奔奔也不厌其烦的每次都看。几次之后老大终于失去了耐心:“别整这没用的玩意儿了,赶紧滴吧!”他抢过手柄,飞快的按下开始键。
老二不仅不生气,还主动让出手柄让我们的玩,他和奔奔并肩坐在床上静静的看我们攻克难关。大家玩《生化危机3》时还定了规矩:谁死了就换人。解谜题的时候则是群策群力,那个小姐妹还用手机记录谜面和排列组合的顺序,帮着我们出主意。
只有老三不玩,他总是窝在老大的床上看,追追一出来就要嗷一嗓子,还总是去上卫生间。借口通常是泡椒凤爪吃多了,肚子有点不舒服。
即使这样《生化危机3》还是进展得很艰难,谜题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经常迷路。每到这时老二就出场了,几乎每次摆弄几下都能解开谜题,迅速推进流程。

这当然让奔奔更加佩服他,一笑起来眼睛就更具神采,老二则把手柄塞回我们手里,并一个劲的表示:“很简单啊,特别简单啊,这还用想?”
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有两个存档,进度不同一快一慢,也就是说老二早就玩过了一遍。这让无比愤慨的老大说到:“你这人儿咋出老千呢,在古代是要被浸猪笼的。”
下一页:更多内容
游戏不玩了?
老二后来再也没有显摆的机会,他刚到国外的那段时间特别爱在朋友圈里发食物,卖相不怎么样,一看就是自己做的。开始我们还认认真真点赞,发的多了就学会了视而不见,最后还是老大留言吐槽:“游戏不玩了,要当厨子吗?”
那时也难得和老二聊天,只有游戏相关的内容出现时才说上几句,我们说:“老二,你那里买游戏、玩游戏都特别方便吧。”老二答:“草!我都忘了注意这些。”
后来老二回国过春节,我才知道他在真的在一家中餐馆当副厨,发的食物都是新开发的,当然都是失败的产品,老板让他自己处理掉。至于游戏,老二真的没有时间玩,他白天要上学,晚上在餐厅工作到 11 点,回来还得做作业预习功课,周而复始持续了 3 年。
有一次回国时他明显瘦了很多,羽绒服显得特别大,尤其是胳膊那里空空荡荡,残疾人似的。我们聚餐吃的竹园火锅,老二一个人加了 3 回猪蹄,服务员流露出吃惊的眼神有点不知所措,他倒是神情自若的催促道:“加点汤,再来两根扯面,谢谢。”
这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回忆。上学时老二第一次请我们吃饭就是在竹园火锅,为的是“出老千”赔罪。按每人 50 块钱的标准,老大直接点了 6 箱啤酒,外加几个海鲜拼盘。当时老二脸色一下就变了,奔奔笑着握住他的手:“没事儿,没事儿,我来请,我来请。”
6 箱啤酒没喝完,老大摇摇晃晃的说是去退啤酒,结果偷偷结了帐。本来的计划,是吃完饭去“吸引力”滑真冰,但酒喝得太多时间也太晚,于是决定还是回宿舍玩游戏,《生化危机3》也到了关键时刻 —— 吉尔中毒,卡洛斯要负责去医院找解药。
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喝酒误事”的道理,操作时总是无法完美的避开或是击杀猎杀者,卡洛斯被堵在墙角,频繁遭受切肤的伤害。气的老二总是重新读档,其他人则大把大把的吞食锅巴,泡椒凤爪开了一袋又一袋。
奔奔的小姐妹突然让我陪她取点钱,我只能无奈放弃了接班《生化危机3》的机会。但她没有去银行,而是上了宿舍楼的天台。
记得天台晾满了各色的床单和被罩,一阵风吹来 ,一切都鼓鼓的,饱满而虚幻。近处有人不断的咳嗽,所有卫生间的声控灯便一闪一闪,天际线的尽头是一座阴沉的小山,顶峰竖着个“树”的红色大字,本来是“植树造林”的,掉了三个。
“以后不许背后叫我灞波儿奔!以后也不许叫我小卖部!”
然后她的刘海差点刺进我的眼睛,我在那一刻终于发现,她个子要比我平时见到的高,当然也怪我矮。第一次拥抱显然太过慌乱,除了她的出其不意,还因为我手里拿着锅巴,她手里则攥着泡脚凤爪,于是我们都不想弄脏对方的肩头和发梢,匆匆的依偎着彼此,又匆匆的分开。
我在天台怀着兴奋吃完了所有的锅巴,然后小心翼翼的打开 302 宿舍的大门。那时老二正熟练操作康复的吉尔,击败了追击者;老三吆喝“把门关上!把门关上!”老五趴在上铺,手里拿着茶杯,眼神在黑暗处闪光;老大则在抽烟,烟灰掉在了主机上,烫出花儿一样的疤。
怀旧之旅
2015 年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她,在毕业 10 周年的聚会里。她基本没变,甚至没胖,只是更加开朗。一个男同学喝多了擎住她的手来回抚摸:“你不知道吧,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你,真,真的。”她把手抽开:“那你追啊,现在也不晚嘛,哈哈哈。”
奔奔倒是和老二毕业不到两年就结了婚,正常得让所有人感到异常。那次奔奔是代表老二来的,老二人在瑞典公司不放假,托奔奔给我们宿舍每个人送了一盒巧克力,不知道为什么,出国的人总爱给国内的人送巧克力。
聚会很快变得无聊,座位开始打乱,大家基本上是按照收入和社会关系慢慢锁定彼此的目标,然后心照不宣的相互敬酒递烟,一种小心翼翼的市侩。至于上学时的回忆,只能作为添头出现,就像当年买书时送的“热得快”,没人会真的在意“热得快”。
老大则有些另类,一个劲儿和老五拼酒,嘴里嘟囔着“你记得不,咱宿舍那时整天玩《生化危机3》,还偷电玩,自习室的电视都差点儿给整报销!”老五答:“哪里是自习室的电视哟,是走廊灯走廊灯,罚酒罚酒!”老三那次聚会没来,媳妇刚生娃,但还是给用微信转了 500 块钱,留言是:“302 的弟兄们好。”
这笔钱是“怀旧之旅”的一部分,名称真诚而土气。按照老大的计划,趁着 10 年聚会要把当时的“路”再走一遍,结果发现找不到路。那家竹园火锅早就倒闭了,“吸引力”真冰场也被万达影院代替,精白沙在市场上消失不知所踪,卖游戏的小店现在则经营着手机配件。
这些变化更显现在学校里,宿舍楼又刷了一层白浆,仿佛美人迟暮时脸上的白粉,“英语角”变成了学生超市,男生都在满头大汗的排队买冷饮,女生都云淡风轻的躲在阴凉处等着吃冷饮,看不出她们是艺术系还是法语系的。
于是我们摇摇晃晃的上了天台,一身的烟酒气和疲倦,外加一路的胡言乱语,有点儿像丧尸。

老大一把我推到她身边,奔奔则在一旁“吃吃”的发笑,天台的内容没变,还是床单、被罩,天际线尽头的小山,被怪兽鳞片式的楼群慢慢遮盖,看不出“植物造林”还在不在,然后我没忍住打了个内容丰沛的嗝。
我想起当时还指着天边,给她画出了一栋虚拟的房子,很认真的说要永远在一起,但现在想来幼稚得比打嗝还尴尬。现在天边真有了房子,而且还不止一栋,可这些真实房子的均价,当时已突破 1.2 万每平方米,我根本买不起。
她默默的笑了,不知道是因为过去的幼稚还是因为现在的房价,或者我刚刚打的嗝。也许我们都在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以后会挣钱,但最终挣不到什么大钱,我们以后会有事业,但也不算多大的事业,我们以后都会拥有所谓的爱情,但那份爱情也就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美好的鱼都活在想象的水域,它爬不上现实的堤岸。”
唯一不变而又有悬念的只剩《生化危机3》,吉尔可以固执的认为这是她的最终逃脱,卡洛斯坚信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一切,追击者可以义无反顾的高喊“S.T.A.R.S!”,整个浣熊市可以在蘑菇云中迅速幻灭,又在某个时段再次冉冉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