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夫之肖像(日本平福百穗摹)
在中国近现代,明末大儒王夫之(号船山)受到不同派别、集团的推崇,出现过“人人都说船山好”的现象。曾国藩、郭嵩焘等晚清中兴名臣所推崇的是理学家王船山,谭嗣同、章太炎、章士钊、杨毓麟等推崇的是民族主义者王船山,在现当代,人们推崇的是哲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王船山,甚至是启蒙家王船山。这其实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在明清之际寂寂无名的王船山及其哲学是如何被不断升格的?
《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1864-1982)》是首次系统地考察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船山升格运动”,围绕着“船山升格运动”所展开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对于船山哲学的诠释史与接收史出发,来管窥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并揭示“船山升格运动”背后的哲学史逻辑发展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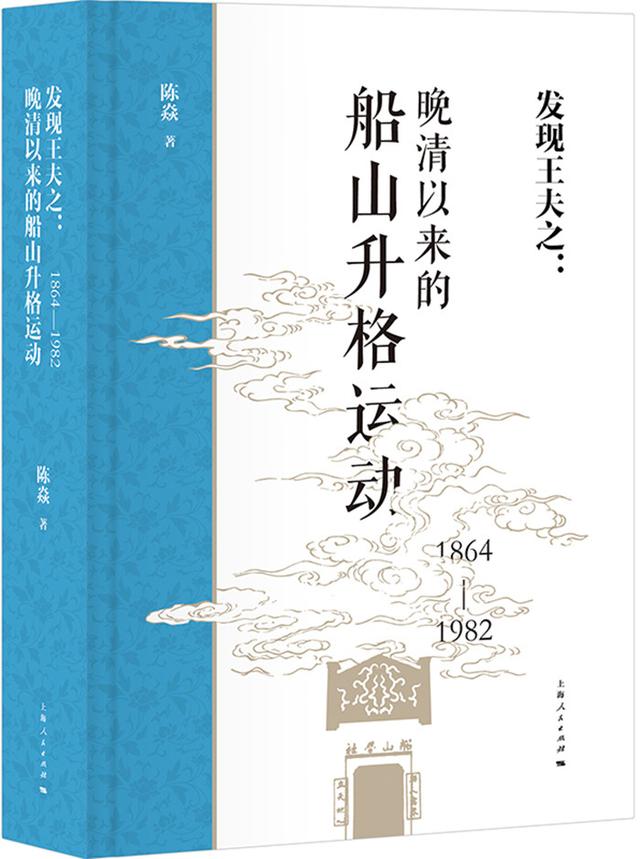
《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1864-1982)》
陈 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序
陈卫平
这是陈焱副教授第二本研究王船山的专著。此前他的博士论文《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范式的反思与转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6 年出版,这本著作是其博士论文的延续和深化。现在不少博士毕业后新入职的高校教师往往存在这个问题,即对于博士论文完成后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感到茫然。对此陈焱的经历可能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些启发。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搜寻和阅读了前人研究王夫之的较多论著,并将有关综述附录于论文。博士毕业后我建议在这基础上以中国近现代对王夫之思想的阐释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目标。后来他以此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本书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这告诉我们,新入职的“青椒”们对博士论文的“接着讲”,也许是明确研究课题的可行之路。
陈焱的这部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关于王夫之的研究作了相当详细和深入的阐述,核心的观点是把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王夫之的一百多年(1864—1982)的历史进程概括为“船山升格运动”,用冯契先生所说的“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视野对此予以考察。这样的概括和视野对于船山研究具有自得创新的意义。具体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是揭示了“船山升格运动”嬗变的历史轨迹。作者把近120 年的“船山升格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晚清的社会变革与“船山升格运动”的初起。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而展开,晚清的洋务自强、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这些社会变革推动船山从寂寞无名走向思想前台。倡导洋务运动的曾国藩、郭嵩焘提出船山“从祀孔庙”,变法维新的重要人物谭嗣同认为船山对于“孔教”的发扬光大乃“当空绝千古”,都是试图另立儒家新道统,以此作为他们进行社会革新的精神滋养;力主“排满革命”的章太炎等,以民族主义解读船山的夷夏文野论,用以瓦解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论证推翻清政权的正当性。“船山升格运动”由此开端,贯穿着走出原有道统而迈向近代(现代)阐释的思想足迹。其次,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与“船山升格运动”的展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对经学的否定,哲学由此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五四时期开始构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船山升格运动”在这个领域得以展开。从梁启超的两种清学史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嵇文甫的《船山哲学》到贺麟的《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从王孝鱼的《船山学谱》和张西堂的《王船山学谱》到侯外庐的《船山学案》,虽然他们各自研究船山的立场、重点、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运用哲学话语体系诠释船山,将其升格为在中国哲学史上与朱熹、阳明比肩而立者。由于这样的哲学话语源自西学,因而就产生了以此诠释船山是否模糊了船山思想的民族特性的问题。这是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现代性与民族性如何统一在船山研究中的反映。再次,认同、怀疑、摒弃“日丹诺夫范式”与“船山升格运动”的高潮和退落。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主流。成为主流则有可能被教条化。新中国成立后盛行一时的“日丹诺夫范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产物。因此,学界在船山研究中经历了认同、怀疑、摒弃的曲折。其间,船山研究一方面将船山升格为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甘于被这个范式所束缚的倾向。这是那个时期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为教条化范式作注脚还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两条路径对立的缩影。
二是揭示了船山哲学范畴取得的新内涵。作者指出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背景下的“船山升格运动”,对船山哲学的范畴进行分析、诠释,一方面使这些范畴的涵义变得清晰起来,一方面将这些范畴推陈出新而具有新的意义。这是贯穿于全书的。郭嵩焘以“办理洋务”的眼界阐释船山的“理”“势”范畴,使船山的理势论转化为以理合势、因势定理的“洋务派的根本的哲学逻辑”;谭嗣同用船山“一卦有十二爻,半隐半见”之《易》说说明“不生不灭,仁之体”,将《易》与儒家根本概念“仁”联系起来;他对于船山将宋明理学偏重于天道观的“道”“器”范畴发展为人道观(历史观)的识见予以彰明,赋予船山“无其器则无其道”具有引向历史进化论的意义;章太炎对于船山的夷夏文野之分,作了夷夏“化有蚤晚”即进化时间有先后的解读。“船山升格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是在中国哲学史领域进行的,因而对于船山哲学的范畴如理气、道器、天人、性命、理势、体用、动静、能所、格物、知行、言象等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命题,都作了比较明确的界说。范畴是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是理论体系之网的网上纽结,因而在梳理船山哲学范畴的同时,也对船山哲学予以体系化。作者指出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嵇文甫和侯外庐。前者认为从学术谱系上,船山“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围绕“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根本思想”而形成“一贯的体系”,这样的体系体现了正、反、合的辩证法,即程朱是“正”,陆王是“反”,而王夫之是“合”;后者认为宋明以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集中于理气观,船山对此阐明了“气为第一次的,理为第二次的”,这在“船山学说中是最光辉的”,揭示了船山哲学是以气一元论为核心的体系,它“蕴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即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批判总结。以后的“船山升格运动”大体是侯外庐这一观点的延续和发展。由此可以说,本书的研究揭示出“船山升格运动”是同船山哲学范畴和命题涵义的明晰化、理论的体系化相联系的。这就阐明了这个升格运动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内在的联系,因为这样的明晰化和体系化正是后者所要求的。


《船山遗书》曾氏金陵刊刻本
三是揭示了“船山升格运动”把西学与船山思想相融通。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中西合流中展开的反映。中国近代哲学与向西方寻求真理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在历史上借助先辈的传统演出新场面的现象,“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中国近代用西学诠释船山思想正是如此。本书借用的“反向格义”之说对此作了阐述,指出这样的“反向格义”是两者融通的过程。本书特别注意到近代中国用以格义船山的西学基本上是在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近代思想,这实际上表达了如下的学术见解:如果说上述的赋予船山哲学范畴新内涵,最终是把船山升格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最高峰,那么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格义船山,则是把船山升格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先导者。后者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近代思想乃“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称“清代思想之光辉,亦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因而船山是中国早期启蒙的杰出代表。本书指出这样的“反向格义”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船山升格运动”揭示了船山思想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思想相似的社会意义。如谭嗣同说船山含有“兴民权之微旨”,梁启超认为船山“发民权之理”以“裁抑专制”,章太炎推崇船山为“民族主义之师”,嵇文甫指出船山“乾坤并建”包含“思想上的民主精神”,侯外庐以魁奈的经济学说解释船山“国民之富的主张”。其二,由于“船山升格运动”后来主要展开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因而关注船山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相似的理论意义。比较典型的观点有:梁启超指出,在西方近代“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是从这个方向出发”;嵇文甫以欧洲“历史哲学成为现代形态”的过程来分析船山历史哲学,指出其中的四个要点“不能不加以称赞”;贺麟认为黑格尔提出的“理性的技巧”,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里,“不惟得到印证默契,而且得到解释和发挥”;侯外庐特别强调船山哲学“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陈焱对于中国近现代的“船山升格运动”既有纵向的历史梳理,又有横向的理论考察。不过,就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视域来说,还需要注意近代创造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既对传统哲学推陈出新,又努力会通中西。就是说,研究“船山升格运动”还应当考察这些理论体系如何把船山思想作为自身的资源。本书在“余论”中对此有所涉及,但未能展开,这大概是它的一个缺点。这里借此略作提示。就船山对五四以后哲学理论体系创造影响最大的,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即综合唯物、理想、解析的“新唯物论”。熊十力用“尊生、彰有、健动、率性”概括船山哲学,也用同样八个字概括其《新唯识论》,表示“《新论》之作,庶几船山之志耳!”(《读经示要》卷三)事实上,他对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的吸取是十分明显的。熊十力不同意船山为唯物论者的观点,与此相反,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则有意于继承发展船山为代表的唯物论。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自宋至清有三个哲学潮流,一是程朱为代表的“唯理论的潮流”,一是以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的潮流”,一是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而这个潮流“足以为现代思想之前驱”。他的“天人五论”体系正是表现了踏着前驱的足迹而前进的自觉,对此已有不少“天人五论”的研究者作了阐发。彰明船山思想在近代中国哲学家构建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就是揭示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旧哲学中之活的潮流”(《中国哲学大纲·结论》)的发展,这对于我们当代中国哲学是有借鉴意义的。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体系(如冯契的“智慧说”)的建构中,船山思想依然是重要的传统资源。这意味着船山思想并不因为“船山升格运动”的消退而失去生命力。
作者:陈卫平
编辑:蒋楚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