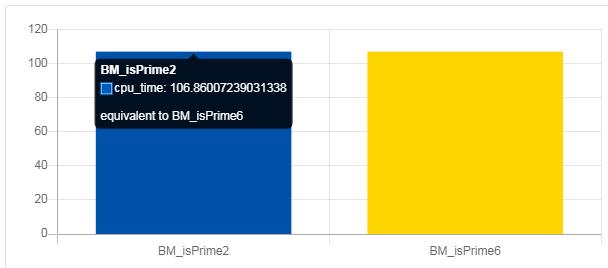婆
文/田定方
婆,一个古老的名词,从远古传来的最美称呼,让我们一叫,就叫了千年。
婆,隔辈亲,关于婆的记忆,总是温暖的。这温暖给我的感觉,就好比是你站在高山之巅,享受那春风拂面;就好比是在炎炎夏日下,你徜徉沙滩,海水涌来,亲吻你的脚踝;就好比是在收获的季节里,你看着那累累果实,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喜悦。
——题记
小姨子给妻子打来电话说,最近晚上睡觉,经常梦见婆,不知道是啥原因。妻子调侃道,得是婆想你了啊!要不,你回来给咱婆烧些纸,送些钱。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我爷和我外爷,还有四位老人,印象较为深刻,那就是我婆、外婆、妻婆和顺义婆。而我婆,应该是印象最深的了。关于外爷,我以前专门写过。对于我爷,多篇随笔中写到关于他老人家的情况。
1930年的春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婆缠着小脚,蒙着红盖头,骑着毛驴来到我家,嫁给我爷,就像电影《红高粱》中九儿出嫁的场面那样,只是少了吹鼓手,可能是贫苦人家的儿子娶媳妇,请吹鼓手要花钱,因此作罢了。
1960年,全国闹饥荒,我外婆的第一个丈夫出去跑活路,可好几年了,始终不见回家。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外婆带着我母亲一路讨饭,从甘肃天水跑到陕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叩开了我外爷家的大门。
1950年5月1日,为了进一步解放女性,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其中明文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时候,青年男女处于从包办婚姻到相对宽松的转型状态,男女开始有恋爱的过程,但主要还是靠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1952年妻婆嫁到了大樊的妻爷家。不过,还是像包办婚姻那样,结婚前,妻婆只知道妻爷的姓名,家住哪儿,至于妻爷长啥样子,个高还是个矮,胖还是瘦,光脸还是麻脸,妻婆是一概不知的。
顺义爷家是从山东迁移过来的,落脚在流曲镇顺义村,全村均为高姓,一门子的人,大门大户,有钱人家。1944年,顺义婆十六七岁时,由自己的舅舅保媒,嫁到了顺义爷家。其实,顺义婆的舅舅是顺义爷的姑父,这样的亲上加亲,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遍的。顺义老爷和老婆人很好,待顺义婆如亲生女儿一样。
我婆和妻婆人都长得瘦瘦的,瓜子脸,丹凤眼,很好看。外婆和顺义婆微胖,花眼棱双眼皮,人长得富态。我婆和顺义婆个子高点,妻婆和外婆个子稍矮点。

我婆
我婆嫁到我家时,家里有大小十多口人,我爷在弟兄辈排行老大,我婆作为长子媳妇,一家子的日常家务就落在了她的身上。结婚后不久,我爷到兰州当相公去了,谁知这一走,三年没有音信,我老爷和老婆托人四处打听,也没有个下落。村里人都说我爷可能“魂”没了【意思是我爷变心了】,就给我婆出了个主意,把我爷穿过的鞋烧了,朝着兰州的方向喊三声我爷的名字,我爷就会回来的。我婆半信半疑,可也没其它办法,只能试试了。说也奇怪,鞋烧了有一个月后,我爷竟然出现在了家门口。第二年,我大伯父就出生了。可好景不长,大伯父三四岁时,染了病,命没有保住。在那个少医缺药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司空见惯了。伯父夭折后的第三年,姑姑出生了。又过了六年,我父亲出生了。
我婆头上经常包着一方白手帕,身上穿着用自己织的黑粗布亲手缝制的大衿上衣和大裆裤子,裤褪下常年束着,一双堪称三寸金莲的碎脚上穿着自己做的布鞋,极干净利落且朴素整洁。一年四季几乎不变的一身装扮,在我的童年及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每次我婆准备走路,她在站起来时,就要在原地先踏步几下,似乎在找平衡点,然后才慢慢地拄着拐棍向前移动,她小脚走起路来总是晃晃悠悠的。
婆大约每隔半个月左右洗一次脚,到了冬天,她总是把洗脚时间放在天气晴朗,有温暖阳光的中午饭后,洗脚水就用刚蒸完馍后锅里的热水。她在屋里后院子的桑树下洗脚时,总不忘叮咛我快去把家里门先关上,还让我站在门口放哨,若有人来串门,就要立马告诉她。我看着婆放在洗脚盆里那几乎弯曲了180度、踏到脚底扭曲变形的四个脚指头,心里不禁生出好奇,就问:婆,你脚咋是这样子的?婆笑着说,你老外婆说这样子好看,给我用布缠成这样的。说这些话时,婆很坦然。等我工作后,偶尔在网上搜索“缠足”,出来的内容令我目瞪口呆,无法想象我婆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苦痛和折磨。
我婆一生勤俭持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连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的生活都极度困苦,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夏季收麦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婆就戴个草帽,静静地坐在打麦场边上一个用麦草编的蒲团上,把碾过的麦草或麦糠再很仔细的翻一遍,拣拾里面遗漏的麦颗,一粒也不轻易放过。
我会走路时,婆就常引着我到耙沟窑老姨家串门,坐在火炕上的老姨只要一见到我婆来,就热情的打着招呼,还用手拍着炕沿,边拍边说,快跟娃上炕来坐。我婆走到炕边,先坐在炕沿上,用放在炕边的小条帚把自己鞋底的土扫一下,就连着鞋坐到炕上去。我的印象是,当时的农村老太婆白天上炕是不脱鞋的,火炕上面就只铺着一张芦苇编的席,席子下面垫着麦草。我不上炕去,就独自一个人在屋内的地上玩耍。两个老太婆盘脚打腿地坐在火炕的席上拉起了家常,俩姐妹一见面,总也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婆对吃穿一直都不讲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饭菜和穿戴弹嫌过。婆有好吃的,总不忘留给自己的孙子们吃。我姑来看望我婆和我爷时,总会带些洋糖、麻饼和鸡蛋糕什么的,她总是舍不得吃,并留些用手帕包起来,当每次看见婆偷偷招手示意我过去时,我就喜出望外,知道一定有好事;在当年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亲给婆和爷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在全家人都吃用玉米等杂粮馍的情况下给他们吃麦面做的白馍,我婆在吃白馍时就经常偷偷地掰一小块馍,快速地塞到我的手里,自己再去吃黑馍。
每次看见婆梳头时,我就安静地坐在旁边等着。婆和往常一样,把梳下来的头发卷成团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把头发塞到墙角的胡基缝里。当听到村子里有货郎担子来时,那“头发换洋糖、换盆、换碗......”的连续不断的叫卖声,伴随着悦耳的货郎鼓声由远而近时,我就立刻振奋起来,飞快地跑回家,从墙缝里取出头发,然后直奔叫卖声而去。
天气晴朗的午饭后,婆常会在门口小坐一会儿。这时,邻家的老婆婆们便会拄着拐杖、挪着小脚,聚拢过来。常有老婆婆鼻涕一把泪水一把地诉说着自己儿媳妇的不是和自己受的委屈。这时候,我婆总是静静地听着,还时不时地劝说对方几句,她从来没有在人背后说过我母亲的不是。婆婆们散开时,发泄委屈的老婆婆站起来时,拄的拐棍还不停地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似乎余怨未尽。
1976年,我爷去世,家里日子过得还苦,父亲在队上借了粮食,给爷过了事。那年,伟人逝世,全国人民都处在悲痛之中,我爷的丧事过得也就简简单单,连个吹鼓手都没能叫成。1989年,我上初三那会,婆得了重病去世了。曾在耀县剧团拉头把弦的姑父请的乐人,着实给我婆在村里热闹了一番。
外婆
在外婆和母亲到来前,外爷的结发妻子因病已过世三年,留下了一个男孩。外爷和自己父母,还有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在外爷父母的撮合下,外婆和外爷搭伙过起了日子,那个男孩也就成了我的舅舅。后来,外婆和外爷再无生育孩子。
外婆烙的锅盔大如锅盖,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这也正如西北女人特有的大气和豪爽,外婆说话、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舅舅和妗子生育了五个孩子,舅舅在县城大修厂上班,家里人的吃喝拉撒全由外婆和妗子打理。常年的劳作,使得外婆手上布满了裂口,以至于后来做针线活时常会袢着线;到了冬天,脚上的裂口用胶布贴也贴不住,走起路来生疼。
四个表哥中,二表哥算是最调皮的了,不是今天把人家的庄稼破坏了,就是明天又把邻家孩子的头打破了,外婆不是给东家赔礼,就是给西家道歉。错就错了,外婆从不偏袒我们。
外婆虽是半路到外爷家的,可对人情世故却很练达,不论是家门户族,或是近邻远亲,她都能应付自如,门庭里各路亲戚络绎不绝,不管是谁,都要留下人家吃了饭才走,远路上的歇一宿才让回去。外爷是贫协主席,有时下乡来的蹲点干部也常安排在家里休息和开会,总之一应吃住全由外婆里外张罗,粗茶淡饭不缺,家里很是热闹。
农闲时节,每天早饭刚吃过,外婆家里就会来三四个老头,他们是来找外爷打麻将的,白天是在院子里,晚上就挪到了养牛棚里了。这些老头根本就不讲究卫生,浓痰吐得到处都是,他们有抽卷烟的,也有嘴里噙着旱烟锅的,外婆家的院子和牛棚里,总弥漫着浓烈烟味,呛得人直打喷嚏,直流眼泪。这时,外婆总会骂上几句,看把你们这些老不死的咋办呀!可骂归骂,到吃饭时了,还是给外爷的这些老伙计们把饭做得好好的。
上小学那会的寒暑假,我大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多了,融雪形成的冰凌,可以从屋檐口一直挂到地面,小伙伴们争着扳下来,扛在肩膀上疯玩,到了晚上,鞋子里都让脚汗弄得湿湿的。每天早上外婆做早饭的时候,都会将我们的鞋子放到锅灶的“老虎洞”里炕,等我们起来穿的时候,都是干蹦蹦、热乎乎的。早饭做好之后,外婆会塞几个红薯在灶堂里,让脚火将它烤熟。当我们掏出来的时候,红薯皮已微微有些焦了,剥开来里面是热腾腾的金黄,咬上一口甜丝丝的一直滑到心底。曾经在街头烤红薯的摊子上买过,却再也尝不到那种沁心的焦黄香了。
外婆生性善良,谁家有难一定会伸手相帮,被她接济过的人数不胜数,村里的人都念她的好。那时候经常有外地逃难来的人来要饭,别的很多人家不想给会放狗咬,外婆总是厉声喝住自家的狗,给人家装两碗粮食,赶上饭点还会请人家吃一顿饭,她常说:“能帮人一把是一把,少吃一口咱又饿不死。”
文化大革命初期,外爷被村里一群不怀好意的人莫名地定成了走资派。一天,外爷家里来了一群臂戴“红卫兵”字样的男女青年,他们一个个笑嗬嗬的,见了外婆反而十分拘谨了,其中一个人把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放在堂屋的方桌子上,大声说:“婆婆,首先我们声明不是来抄家的,只是贴几张大字报让你们反省反省。”外婆好客惯了,更会息事宁人,便说:“娃们,欢迎你们来,我这就去烧浆糊。”去了厨房片刻,却端来十几碗荷包蛋,弄得这些红卫兵们大不自在起来。趁他们吃的机会,外婆就着热锅打好浆糊,端出来沾上扫帚朝墙上刷了一遍,这些红卫兵们丢下碗过来帮忙张贴,足足贴了七八张,最后也没有开会,啥话题也没说,连声道谢便走了。
叶落总会归根,人也一样,人老了,心里就会想着故土和亲人。外婆年老时,总念叨着想再回天水老家去转转、看看。考虑路途遥远,外婆身体状况,就未能如她老人家心愿。好在外婆的一个侄子,也就是我母亲的表弟从天水过来,落户在了我家附近,时时能去看望外婆,外婆去世前一两年,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记忆力也衰退的厉害。周五我下班回到家里,外婆好几次都认不出来是我,追着我母亲一直问:这是谁啊?跑到家里来了。有时,外婆思路却很清晰,看见我回来,就拉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外婆的手绵绵的,很温暖。
2008年的九月三十日下午,学校放国庆假,我和妻子准备第二天到浙江去参加小姨子的婚礼,出发前,到舅舅家看望外婆。到外婆家时,听舅舅说我母亲早上才回去,给父亲蒸些馍,再来服侍外婆。我和妻子进了外婆房子,看见外婆紧闭着双眼,躺在炕上,我叫了好几声“外婆”,她才疲惫地睁开眼睛,不过,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和妻子,努力地要坐起来,思路也开始变得清晰,不停地问我们吃饭没有,人看起来也很精神。其实,舅舅说外婆已经好几天几乎没进食了。外婆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妻子。我明显感觉外婆的手心里没有了温度,也不像以前那样绵绵的。
从舅舅家回到老家时,刚和父母亲说了一小会话,表姐就打来电话,说外婆可能不行了,让我母亲赶快来。等我们赶到舅舅家时,外婆已经咽气了。我再看外婆,她很安详。听表姐说,我们走后半个多小时,听到晴朗的天空中响了一声惊雷,外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没了声响。
妻婆
对于妻婆和顺义婆的记忆,都是在我结婚后才有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第一次见到妻婆是在妻子娘家的老屋里。那时,妻爷早已过世,从岳母和姑姑们的口中得知,妻爷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
1998年,经人介绍,我和妻子认识了。谈了一段时间后,我提出了去认认门,看看父母,妻子欣然同意了。
妻婆很瘦小,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可走起路来很有力,眼睛里透露出的也是一股坚强。由于是第一次登门,我难免有些拘谨,那天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只记得妻婆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些,眼里满是热情和老人对晚辈的那种慈爱。
听妻子说,妻婆很爱他们姊妹三个,尤其是疼爱自己的弟弟。妻弟上高中时,每到周五或周六下午,不乱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妻婆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头墩上,向东张望。当看到妻弟骑着自行车从门前公路上过来时,妻婆就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我对妻婆印象最深的源于一包冰糖。有一次,学校放假,我和妻子去看望妻婆,刚一进门,妻婆看见是我们,那高兴劲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她打开房子里的柜子,半个身子探了进去,摸索了好一阵,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笑着说,定方,听你娥姑说冰糖对咽喉好,你给娃们讲课,又抽烟,肯定费嗓子,这包冰糖是你娥姑给我买的,你拿上。我没有推辞,欣然接受了,无形中心里升腾出一阵阵暖意,犹如沐浴在那三月的春风里。
2007年后半年,妻婆眼睛开始变得模糊,感觉老是有影子在眼前飘来飘去,到医院一检查,是白内障,想着妻婆年纪也不算大,就做了手术。可手术一个来月后,妻婆的头脑变得时而清晰,时而糊涂。有时姑姑们和妻婆开玩笑问,妈,你认得我是谁吗?妻婆略带怒气地说,不认识!如果姑姑们还再问,妻婆就会拿起扫炕的笤帚拍打她们,这和以前那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相比,有些大相径庭了。我知道,妻婆是得了常见的老年痴呆症。快到腊月天时,妻婆走了,永远地走了。
妻婆有六个女儿,大女儿成年后,给招了女婿,是顺义高姓人家的三儿子。若干年后,他们成了我的岳父和岳母。
顺义婆
顺义婆,也就是我岳父的母亲。在妻子姊妹三个的记忆中,小时候她们每次去顺义婆家,顺义婆就变着法地给她们做好吃的,特别是那油炸面食,有些带馅的,有些不带馅,带馅的多为白糖或核桃仁或芝麻。每当炸好面食,小姨子总会抢先的。顺义婆就笑咪咪地说,吃慢点,小心烧,还多着哩,吃完了婆再给额娃炸。
顺义婆家的院子和屋前有三四棵枣树,到了秋天,下面时不时就围着一群小孩子,眼巴巴地瞅着树上的红枣。顺义婆看见后,不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哄赶孩子,而是用竹杆打些枣下来,分给孩子们吃。
说到顺义婆了,很有必要提及一下顺义爷。顺义爷是读书人,学习俄语,军大毕业,留学苏联,先在西安李家村武警总队工作,当过随军记者,后在地质部任俄语翻译。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两国关系走上了公开恶化的道路。同年7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援建专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就是在这个时候,顺义爷从地质部返回家乡,在立诚中学任教。文革开始,顺义爷被定为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丢了公职,被遣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批斗和改造。直到1972年,顺义爷才得以平反。随后,在曹村中学、刘集中学、王寮职中等学校任教。1995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当时的《富平报》曾刊发了顺义爷去世的讣告。
顺义爷在外工作的日子里,一年几乎回不了一两次家,更不可能给顺义婆帮忙家务活或地里的活路了,顺义婆是忙了家里,又忙外边,含辛茹苦拉扯着五个孩子。上又有顺义老爷和老婆需要照料,下还有五爷、小爷及老姑们需要抚养。顺义婆作为长子媳妇,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了。1960年顺义爷回来后,顺义婆的艰难日子得以缓解,可也最多是在周六日或学校放假时,顺义爷才能帮得上忙。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顺义爷被戴上了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造反派们拉着游行、批斗,受尽了羞辱和折磨。顺义婆也难逃噩运,跟着顺义爷担惊受怕,不得安宁。有气不敢出,有话不能说,村里人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自己受到牵连。那几年,顺义婆遭的恶言恶语、白眼和冷遇,多得数不清。就连孩子在外面受了人家欺负,自己也只能牙打烂了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可顺义婆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清清白白的,现在的不公待遇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好日子总会到来。
我曾问过顺义婆,那些年最大的遗憾是啥,顺义婆说,自己受罪吃苦没啥,就是孩子们【我的丈人们】跟着遭难了。这个我清楚,除了我的五丈人是文革后考的大学外,其他四个丈人都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和权力,就连五爷和碎爷也是如此。
每年,我和妻子也就能去看望顺义婆三四次,而回回去,顺义婆都很高兴,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做好吃的。回回要离开时,顺义婆总是依依不舍,我们走远了,她还站在门口望着。
2014年7月,瘫痪在床多年的顺义婆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是刻在我脑海里她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
【后记】对于婆的记忆,说来惭愧,很难清晰,多为零星片段的拼凑。关于婆的更多事情,都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了。
贤惠善良、吃苦耐劳、包容大度,这些赞美中国传统女性的词汇,用在我的婆们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怀念我的婆婆们,是因为老人家曾经给我温暖和关怀。在我的儿时,乃至成年后,她们的做人做事影响着我,指引着我。
生活平顺时,她们安静、平淡地活着;艰难困苦时,她们那颤巍巍的小脚走出的是慷锵有力的步子,看似软弱消瘦的肩膀扛起的是一家人的重担,被岁月刻画成沟壑的脸上总洋溢着自信、不屈和快乐。
我的婆们从旧社会中走来,有过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日子。都说包办的婚姻没有爱情或感情可言,可在我眼里,她们很乐观,也很幸福。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这话,让我的婆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可时常觉得怀旧也没什么不好,天生如此,没有办法。我婆也好,外婆也好,妻婆、顺义婆也好,还有我爷、外爷、妻爷和顺义爷,他们曾经都是我的亲人,虽然去了另一个世界,成了我的先人,偶尔怀念一下过去,怀念一下他们以及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岁月,想想受过他们的恩泽,想想身边还有哪些需要眷顾关怀的亲人和朋友,想想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如斯,那么还有什么烦恼忧愁抛不开?还有什么心事纠结放不下?
人啊!就这一辈子,这一辈子不长,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从前”。余生,让活着的每一天都变成向阳而生,也不忘对未来的怀念。

作者简介:田定方,富平县宫里镇雷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