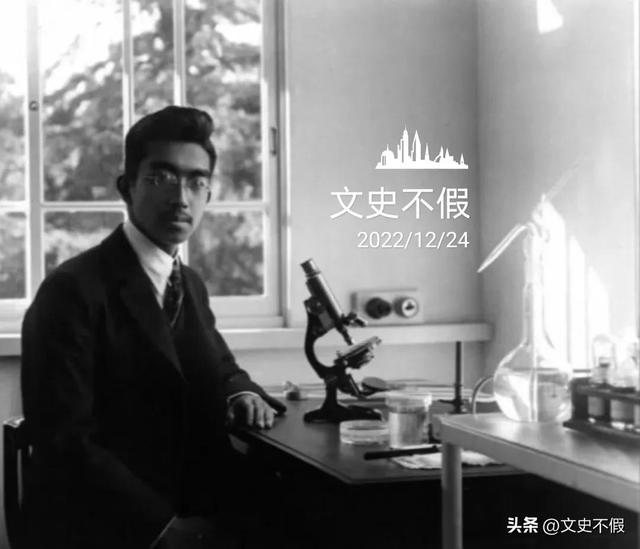本书就是围绕中国能够担当起这样一种枢纽性的地位而展开。

通过阅读此书,可以使得我们理解与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前提;而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我们在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
首先在空间上我们需要关注的四个时间坐标点: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这次转型之后,开始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开始出现了。第二次转型,是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原从分封割据的局面,进入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开始超越于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和对抗,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揭竿而起的是陈胜,打败暴秦的是项羽,取代暴秦的是刘邦。第三次转型,是唐宋之变,就是从唐朝到宋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从此,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第四个转型,就是清朝末期开始的古今之变,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艰难转型。转型仍在继续,还未完成。而到了近现代历史上,就反过来了,海洋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时候变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我们再解读一下世界秩序
包含着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是象征性的说法。
海洋秩序:可以说是由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组成;
大陆秩序:与其的组成者正相反,它们或者是对全球化抱有质疑,比如过去的苏联,或者是难以参与到全球化当中,比如今天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秩序的存续与活力,需要理想、财富、武德这三种要素。
理想使秩序得以自觉,财富使秩序得以滋养,武德使秩序得以自立。
三种要素的担纲群体不一定重合,倘若分立的三者能和衷共济,秩序会充满活力;倘若三者之间发生冲突乃至分裂,秩序将失衡、瓦解。
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一个中介性力量,正是它的存在,能够连接起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使得全人类的秩序连为一体,这个中介性的力量,就可以被称作世界秩序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担当起这样一种枢纽性的地位呢?原因在于,中国本身内在的就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中国有它自己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它自己的大陆区域,就是广大的西部地区。
这样一种超级的多元复合性,在世界各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它让中国能够同时嵌入到世界的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当中,从而连接起这两方。
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多元复合体系的国家结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溯到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去了,正是这几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种区域和人群,逐渐地整合在一块,并锻造成为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但这个大帝国,是作为一个内在多元的体系存在的。前边我们说的那些地方被整合在一起之后,各个地方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跟当地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比如,雪域高原上从元朝开始,便能够持续地从中原和草原获得军事和财政资源的输入,高原内部的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而蒙古草原上从高原获得藏传佛教的输入,草原上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全变了。又比如,在草原的生态条件下,你只能游牧,没法按照儒家所要求的定居化的方式来生活,就不可能变成中原的样子;但是,被整合在一起之后,每个地方也都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因为它能够从其他地方汲取自己所没有的特殊资源,自己就会发生改变。
接下去我们可以以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特征作为线索,解释三个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
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
第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
第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首先“超大规模性”是理解中国历史的钥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直到100多年前,这个比例才开始下降,但仍然长期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古代,世界各国都是农耕经济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同时就对应着财富的数量,因此古代中国也长期占有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
- 其次,中原地区拥有大规模连成片的农耕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里人口密集、土地平坦、地形简单,这种条件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这样的人口和财富的汇聚规模,再加上连片农耕土地的规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个超大规模性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
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
就古代中国历史而言,长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国,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但因其文治孱弱,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国,主张精神的普遍性,却因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迷失在狭隘的特殊视野当中。
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草原获得展开,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中原获得自觉。西域和雪域通过特殊的精神输出,刺激着中原与草原在精神秩序上的各种重构;后者则以其政治力量反向输出,让前者获得超出小共同体范围的秩序。
在超越这诸多区域的多元帝国当中,古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其普遍性,作为体系的中国,也才获得其精神凝聚力。能够建立起多元帝国的担纲者,不会是来自纯粹农耕或者纯粹草原的任何一方,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与治理逻辑;担纲者只能来自农耕草原的过渡地带,也就是东北地区或者长城沿线。过渡地带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脚,便必须能够同时理解农耕与草原,一旦天下大乱,他们是唯一有能力整合两个方向资源的人群,从而担纲起结合草原的视野与中原的精神的使命,建立一个覆盖大疆域多族群、实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国。
各区域有各自的区域性历史记忆,更有因诸区域之共生关系而形成的,超越于单个区域之上、为诸区域所共享的历史记忆。
这种共享历史记忆的表达,才是真正的“中国”史。
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
既然超大规模性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那是不是无限发展这个特性,就能给古代中国带来更多红利?超大规模性也会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叫做内卷化,这个词是美国加州大学一群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出来的,就是说社会和经济会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线上,没有任何办法向前进步,就是内卷化。你会看到,超大规模导致的内卷化,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落后的重要原因。
先来说说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到了清朝达到什么高度。19世纪,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达到了四亿,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国人口只要达到一亿左右,往往就会因为人口过剩,人多地少,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然后流民四起天下大乱。
但是历史进入清朝时,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让人口过剩走向流民四起状况的门槛,大大提高了。一个变化是,清军入关后,带来了和平红利。清军入关前,中原老百姓要养活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一支是明朝的军队,另外清军靠从中原抢战利品来维持自己,所以老百姓相当于养两支军队,而且它们天天打仗,动员强度很高,老百姓的财政压力也就很大。
但是清军入关之后,老百姓只要养活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够了,财政压力急剧下降。另一个变化是,雍正在全国推广摊丁入亩,也就是不再按人头征税,而是按照土地征税,这就意味着手上没有地的老百姓,税收负担也减轻了。这两个变化让底层老百姓的财政压力降低,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人口才能大幅度增加。
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把经济和技术锁死在一种很低水平的状态下,也就是前边说的内卷化。这些过剩人口,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这就使得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不可能出现了。这进一步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出现了,因为工业革命正是以那种技术变迁为前提的。
没有工业革命,你的过剩人口问题消耗不掉,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农业经济肯定消化不掉。但正因为人口过剩,又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就这样自我锁死了,这又是因为超大规模所带来的。中国历史演化到这儿,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要想突破这个关口,中国就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这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从哪里来呢?在当时,只能来自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是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了,否则中国会自己把自己困死。西方的到来肯定不会是和平的,但是大清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全是屈辱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看看,大清反倒因为西方的到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这个例子就是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事。从历史规律上来看,当时人口已经到达了四亿三千多万,差不多到流民四起的临界点了,肯定要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了。而且,只要出现那种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一定会灭亡,你看历史上,从东汉的黄巾大起义,到唐朝的黄巢大起义,再到晚明的李自成大起义,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为什么王朝扛不过去呢?因为流民四起之后,他们一定得往有饭吃的地方跑,哪儿有饭?一定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那个地区也一定是帝国的财政核心区。那么流民把帝国财政核心区一占领,帝国财政就会崩溃,你就没钱发饷,没钱养兵,没钱镇压起义,那帝国彻底完蛋了。
但是清朝是个特例,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还出现了同治中兴,延缓了灭亡的时间。是因为太平军没有占领核心区吗?当然不是了,帝国的财富核心区就是长江中下游,那会儿完全被太平军给占领了,大清的财政也已经濒临崩溃,那为啥大清还能扛过去呢?作者认为,是当时国门被打开后,对外通商的功劳。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要追溯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团练,也就是地方武装力量。他们给士兵发的军饷是很高的,但是国库没钱,钱从哪儿来?朝廷说,你们可以征收厘金,也就是各省之间商品的过境税,用这个钱来养活军队。曾国藩的湘军规模,在巅峰时期达到12万人,从湘军成立到平定太平天国,军费前后花了两千多万两的白银。这意味着,曾国藩收的厘金规模相当大,厘金就是各省的过境税,那也就意味着,大清的内贸规模足够大。为什么内贸规模会这么大呢?这又是因为外贸规模非常大,外贸拉动了内贸。
那外贸规模是怎么变大的呢?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在此之前,大清只有一口通商,外贸规模比较小,五口通商后,外贸规模急剧扩大,从而拉动内贸,能够提供大规模征收厘金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却在无意识间帮助清政府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大清有了这种能力,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怀着多么大的好心,但我们就此要知道,对于近代历史的评价,是要非常谨慎的,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情。
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起着怎样的作用
超大规模的人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内卷化的困境,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超大规模人口才会导向内卷化;但是,一旦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比拼劳动力价格,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谁也拼不过中国。
不过,要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要把所有人、至少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给动员起来,愿意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这就叫完成了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用传统的办法是没办法带来中国的政治整合了,那就意味着,只能进入现代革命。这就进入到从清末开始,贯穿了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革命时期了。但是咱们还得多追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完成这种整合呢?还是跟超大规模性有关。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像泰国、韩国,如果他们愿意加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靠外部世界的拉动,可以一把把他整个国家全都拉动进入到现代经济世界。但是中国规模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整体性地拉动起来,只能拉动你的局部,比如上海、广州、天津,拉动这些口岸地区,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口岸地区跟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的联系,远远大于它跟200里地之外乡村的联系,这样国家在经济层面就彻底被撕裂了。这种经济撕裂一定会引发社会撕裂,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内战。内战发展得严重了,甚至会把你之前的发展成果一把清零。
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这种方式,完成了政治整合。在这之后,中国便整体性地投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也迅速释放了出来,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优势。
比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低的优势,从比较初级、简单的出口加工行业做起,吸引着很多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完成了最初的积累。
在构建整个供应链网络当中,有无数个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用专业化来确保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些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并且这种配套关系还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用动态重组的能力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中国就是发展起这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几乎都在向中国转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供应链网络当中有一个核心变量,就是它的规模。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内部的小企业就可以越专业化,从而提升效率;同时规模越大,意味着小企业互为配套关系的组合可能性也越多,从而提升弹性。
所以,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使得成本控制当中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能不能把生产流程嵌入到一个供应链网络当中。所有这些,都使得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以至于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在向东南亚转移呢?这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研究报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的贸易品都是半成品和零部件,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贸易这些半成品才有意义。说明中国和东南亚还是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的。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为全球海洋与大陆秩序之间的枢纽。这一枢纽地位不仅仅是具备经济意义,它同样在世界秩序的构成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于中国枢纽地位的这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意义的理解,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和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前提。
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我们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
更简单的可以理解成为做一位有理想、有价值、有用的人应该所具备的精神素养,同样这也会反哺你成为更为优秀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