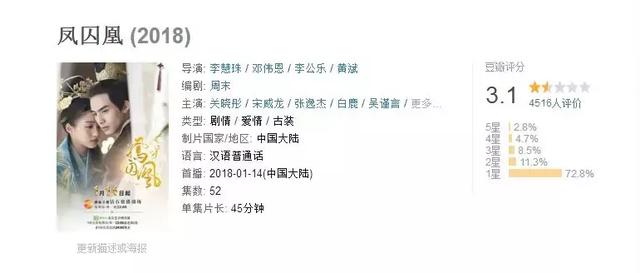#影视杂谈##黑泽明#
在马尔克斯看来,唯黑泽明有资格将《百年孤独》拍成电影。马尔克斯逝世于2014年,黑泽明早在1998年逝世,两人曾于1990年有过一面之缘,但并未提及《百年孤独》改编一事。

马尔克斯与黑泽明
八年后,有制片人征求了马尔克斯的意见,说可以改编了,指定的导演仍是黑泽明(由作家选导演,这在电影史上极其罕见),当制片人正要联系黑泽明时,却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黑泽明已与世长辞,《百年孤独》因此无缘荧屏。
换个角度看,即便导演不是黑泽明,这部电影也可以拍,问题是可不可以拍成功,且不说在拍摄过程中把控剧情、调度场景,光是做剧本且不破坏情境就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这正是马尔克斯本人最顾虑的地方。
我们从黑泽明之于马尔克斯之于《百年孤独》的间接关系中,可以感受到黑泽明在影界的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别忘了,马尔克斯也是很懂电影的。
黑泽明导演的影片中,战争题材颇多,提及战争题材,我们会想到好莱坞大片中狂轰滥炸血肉淋漓的暴力美学,还有国内影视剧所执着的大场景,后者存在一种现状,十万人的场面用一二百人拍出,这种通过特效做出来的大场景是否违和,有无史诗感,观众自有评判。
黑泽明有意避开这些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在他导演的影片中,人物不多,道具朴拙无奇,场景不求华丽,(比如《七武士》《罗生门》),他要的是更深层次的表达,来支撑理想信念、剖析人性的隐秘、传递人文关怀。
有的电影作品虽说非战争题材,却与战争有着忽明忽暗的关联,比如电影《梦》和《八月狂想曲》,《梦》由三个梦组成,仅有其中一个梦和控诉战争有关,而《八月狂想曲》则是将对战争的追问和思考贯穿始终。
众所周知,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和军人伤亡,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破碎的长崎
虽然二战结束了,但战争阴影并没有很快散去,在漫长的岁月里依旧笼罩在世界人民心中,核爆给日本国民特别是核爆幸存者留下了深深的后遗症。黑泽明在《活人的记录》中控诉了这场旷古未有的大灾难,表达了对核弹的深恶痛绝。
时光总会改变人的心境。四十年后,黑泽明拍了《八月狂想曲》,对这次恐怖的核爆炸进行追问和反思,这部影片是黑泽明有生之年倒数第二部作品,上映于1991年,获得1992年第1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项。
影片采用人物穿插的叙说方式,以孩子的视角及老人的回忆,向我们讲述了一段看似平淡无奇但情感暗涌的八月乡村故事。
在影片中,奶奶收到旅居美国七十年将要不久于人世的锡太郎的邀请,让她去一趟夏威夷,来弥补兄妹两人天各一方不能团聚的人生遗憾,而爷爷多年前被美国投放的原子弹炸死,这让奶奶无法释怀,所以并未立刻答应,这时,美国侄子来访,通过亲情上的交融,心灵上的沟通,奶奶缠绕心中四十多年的疼痛与仇恨终于得到化解。
先是一组空镜头:白云漫浮的蓝天,刺耳突兀的模拟性蝉鸣充斥其中,长崎方向出现一朵蘑菇形状的云。
值得注意的是,这片云在影片中定格了六秒之久,当然了,这样意象定格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一,隐喻45年前在长崎腾起的蘑菇云。
第二,与片末“奶奶的脑子往回转,转到了爷爷照片的年代,看着天上的云和原子弹爆炸的云一样,就往长崎方向跑去”相呼应。
接着镜头转向纵男弹奏日本童谣《野蔷薇》这一生活化场景,钢琴年久失修,音阶不准,旋律不自然――黑泽明以他特有的方式,来隐喻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心中的伤痕,像钢琴一样修理不好了,正如影片中奶奶所言:我老了,钢琴也老了。
然后收到美国夏威夷的来信,纵男铿锵顿挫地读起来,孩子们从信中得知要去美国夏威夷,兴奋得手舞足蹈,奶奶却颓然垂首,一言不发,读完信后,纵男向大家展示附带的照片,通过特写,我们看到照片上的人穿着美式服装,背靠一辆豪车,其中包括纵男的爸爸和姑妈,再看身边的奶奶,衣着朴素,身无二彩,跪坐在世代传承的老房子里,由此及彼,可见两代人价值观是如此的不同。
知悉信的内容后,奶奶迟迟不肯确认锡太郎是她的兄长,小民(纵男的妹妹)明白,奶奶之所以不肯前往,是因为美国的缘故。小民带着表弟表妹围着长崎的街道转了几圈,想要了解关于原子弹爆炸的事情,但长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像从未发生过这件事似的。于是三人站在山上,向长崎方向的一所小学校望去,那里曾是爷爷任教的地方,小民认为,到那里可以了解到关于原子弹爆炸的事情。
一个连贯式转场,三人身处学校。小民凝视着核爆过后遗存下来的钢筋骨架、残缺不全的雕塑,顿感“所有的天使都在哭泣”,她念着捐赠给长崎慰灵碑(或纪念碑)的国家的名字:巴基斯坦,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苏联,中国……偏偏没有美国。画面与人声、自然声、音乐声相结合,震撼人心。
长崎一行,让兄妹四人渐渐明白奶奶为什么不肯去夏威夷,纵男一语中的,说这是父母的一种外交手段或者阴谋、实用主义,是为了不想失去好不容易攀上的阔亲戚,他们把奶奶当成了工具。
至此三组人物类型赫然呈现:返璞归真却隐痛不止的奶奶,天真无邪又善解人意的孩子,世俗拜金且淡漠亲情的大人,这为剧中矛盾的交织冲突做好铺垫。

长崎之行
纵男给夏威夷亲戚回电报,提及原子弹爆炸的事,说8月9日是爷爷的忌日,祭奠活动一完,奶奶就去。此时,纵男的爸爸和姑妈从夏威夷赶来,兴奋异常,他们大谈特谈锡太郎家族的菠萝园,罐头厂,说他的家像座城堡,他们虽说是来看奶奶的,却绝口不提奶奶,利欲熏心的一面显露无遗。
随后夏威夷来信,锡太郎孩子克拉克要来,信中说,纵男的回信中提及祖父被原子弹炸死一事,他们非常悲痛。克拉克的突然造访,让大人们惶惑不安,甚至恼怒,他们认为克拉克是来和他们做个了结的,夏威夷之行将成泡影,三代人的矛盾由此激化,大人们怨怼纵男在电报里写了实情,奶奶怒斥大人们,怒斥他们讨厌回忆,善于遗忘,顺势质问原子弹爆炸的始作俑者美国――让他们说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说原子弹是为了制止战争?战争结束45年了,原子弹爆炸的后果依然存在。
接下来,黑泽明将奶奶的话推向人类世界的高度――人类的相互残杀依然存在,这都是战争的罪恶,人们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惜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后果将是自身的毁灭。在笔者看来,此处的说教意味过于明显,可以淡化些,让台词更符合日常语境。
大人们很难脱离世俗的世界,奶奶和孩子们则以赏月的方式远离它,奶奶说,看看月光,心情会特别好。影片中,月光代表人世间美好、纯真的一面,除此之外还有瀑布潭、蓝天;坏了的钢琴、铃吉强迫意念里的眼睛则代表残缺、不美好的一面。
奶奶如是描述那颗眼睛:不是人的眼睛,也不是蛇的眼睛,那是天的眼睛!天空开了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露出一颗巨大的眼睛,我和铃吉都被眼睛盯着……影片借奶奶的幻觉重现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蘑菇云轰然腾起,天空瞬间开裂,接着场景转向虚幻,那颗可怕的眼睛突然睁开,令人颤动不安。

可怕的眼睛
通过影片可以看出,黑泽明善于捕捉生活化的意象,月光、瀑布;钢琴、眼睛,两组意象属性相异,互成悖论,折射出剧中人物的心境及影片主题的矛盾性――是继续伤痛还是自我疗伤,是延续仇恨还是反思谅解,是烟消云散还是刻骨铭心。随着锡太郎的儿子克拉克的到来,一切似乎得到了解释。
大家和克拉克来到爷爷任教过的学校,面对冰冷扭曲的钢筋骨架,他们心绪起伏。孩子们下课后冲到操场,雀跃喧哗,将这个特殊的日子视如往常,并不在乎45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当年死去的孩子们的同班同学(现在都已成为老人)缓步走来,他们在钢筋骨架前默哀,然后布置祭奠现场,一言不发,他们小心而专注的擦拭纪念碑,痛苦写在脸上,他们经历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失去了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能不痛苦吗?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我们虽未通过电影看到原子弹爆炸时万物摧毁的惨烈,但人类共通的情感让我们无法不同情这些死难者和幸存者。
晚上,克拉克陪奶奶赏月,他说,由于不知道爷爷的事情,非常抱歉,姑姑是长崎人,我们没有想到,是我们不对。祖母表示原谅,这时钢琴修好了,伤痕平复了,纵男又弹出了优美的旋律。

赏月
8月9日这天,老人们诵经边度亡灵,克拉克向死难者家属鞠躬,死难者家属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随后是特写镜头:一群黑蚂蚁陆续爬上带刺的玫瑰,向顶端的花蕊涌去。
对于黑蚂蚁爬上玫瑰花的象征意义,观众存在一些分歧,象征战后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抑或亡灵游走于人世间?笔者认为这个镜头存在多重象征意义,既包含前者,又包含后者,依照剧情,应该有象征亡灵的意象出现,但从影片的时代背景角度来看,战后特别是四十五年后美日关系处于什么样的节点,黑泽明也应有所表现。
影片末,奶奶得知兄长离世的消息,痛哭流涕,错过的永远错过了,无法再来。
剧情出现陡转,奶奶歇斯底里,幻觉不断,仿佛又回到了45年前恐怖的一天,她看着天上的云和原子弹爆炸的云一样,撑伞向长崎方向跑去,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奶奶的雨伞开了花,还是奔跑,孩子们在后面追赶,他们在追赶奶奶,更是在追赶过去的伤痛,日本童谣《野蔷薇》响起,奶奶举步维艰,孩子们相继跌倒……

在暴雨中奔跑
长达五分钟的桥段里,黑泽明再次利用“天气美学”,将影片的气氛与基调进行渲染,人物内心镜像也映画得细致入微。
祖孙三代雨中奔跑的行为看似乖张、歇斯底里,却合乎逻辑情理,并不让人感到唐突、造作。通过这一行为,影片上升到“人与自然合一”的终极意义,如剧中奶奶所讲――“在这世间相遇,终要在一起”。
在黑泽明的电影里,普世价值多有体现,《八月狂想曲》也不例外,高悬在神社的匾额上的文字“俱会一处”也在表达这一价值观,俱会一处――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有些观众并不买账,认为黑泽明对二战的反思存在局限性,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日本人对二战的反思不够客观全面,电影是塑造人物、表达人物性格的载体,黑泽明的电影有它的现实意义,从不避讳日本民族的弱点、缺点,而是深深地探入,如《七武士》中的善良的农民也有其庸碌、懦弱、自私的一面;如《乱》中混乱战国时代人心的残酷、狰狞、涣散;如《罗生门》中人本性的虚伪、阴暗、猥琐。
《八月狂想曲》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时代日本国民的精神写照,奶奶说,虽说战争也死了许多日本人,但也死了许多美国人。
二战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并非仅存于美日两国之间,难道中国人、韩国人不是受害者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对自己关心的东西力求完美无缺,对他人所关心的则被放在很低的位置甚至无处安放,但这并不代表全部,因为依然有一部分清醒的日本民众认为:无视历史意味着伤害,破坏和平意味着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