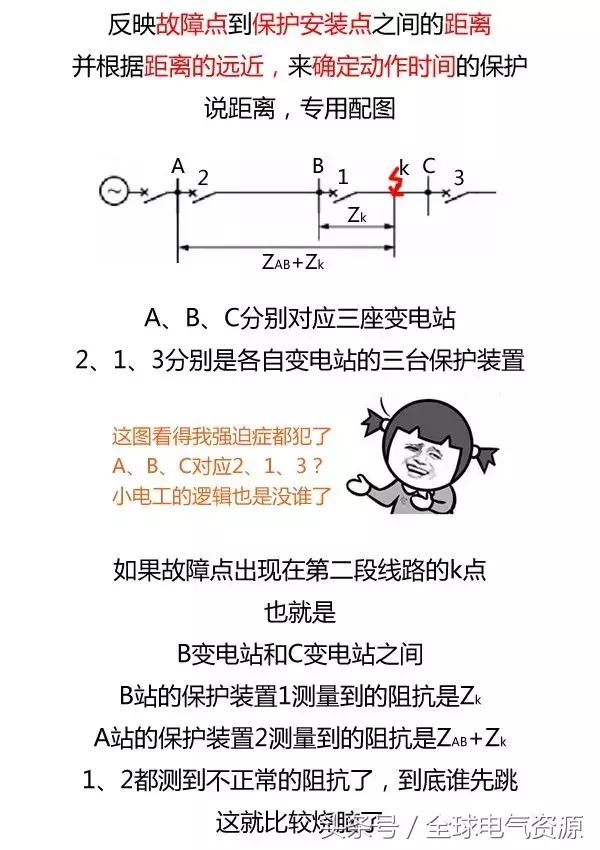南直凤阳府有一个姓李的屠夫,娶妻张氏。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李泽天,老二叫李泽明。
同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可是不一样的。
泽天自小聪明,读书过目不忘,顺利地考取了秀才。
泽明资质一般,念了几年书,连童生也没考到。李屠夫就让他从学堂出来,跟着自己一块卖猪肉。
泽明很想留在学堂,向父亲哀求:我能否继续留下来念书?
李屠夫骂他:你没有兄长聪明,再读下去也无用,只是在浪费钱财而已。
泽明心里很难过,但无力辩驳。
父亲说的是事实,自己确实比不过兄长。只能把书袋收拾起来,从此跟着父亲出外做事。
李姓几代没有出过一个取得功名的子孙,李泽天是第一人,这让李屠夫脸上着实有光。
故,夫妇俩对这个儿子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相较之下,对待李泽明则要冷淡许多。

两兄弟长大娶妻后,二老连带着对两位儿媳妇的态度也不同。
大儿媳王氏,勉强算是书香人家里出来的。她的父亲虽说没有考取秀才,但少年时也曾考取过童生,是个喜爱读书的人。
而二儿媳陈氏,她娘家就是普通的农户。她自己本人,大字不识一个。
所以在夫家,她也跟着受冷遇。做事不光比大儿媳多,吃的饭菜也常常比她的要差。
陈氏心有不满,日积月累之下,总是会爆发的。
有回干完家务活,给她留的又是残羹剩食。她心里委屈,夜里跟丈夫诉苦。
“你和兄长都是爹娘生的,为何会偏心到如此地步?”
泽明面上带有惭愧之意:“是我没用,不会读书,让爹娘看不起。现在,还把你给连累了。”
听他自怨自艾的口气,陈氏不好意思再埋怨下去。泽明过的日子与自己一样,同样好不到哪去。
“睡吧,明日我俩还要早起做事。”
说完这话,她先倒头睡下。但同时,心里叹了一口气。
家里的活儿,现在主要是自己两个人在做。即便累得很,也不能流露出半点情绪。否则,婆母就要骂人。
这日子过得相当压抑,陈氏很想与他们分开来吃住。至少,不用每天都吃锅巴和菜汤。
不过,这种事情,她和泽明是不敢主动提出来的。一旦他俩开口,就会担上不孝的罪名。若被告上官府,一顿板子必定少不了。

有意思的是,三年后,陈氏的这个想法居然实现了。
提出分家的是李屠夫,他为何会主动提出呢?
全是因为大儿子泽天,他去参加乡试,再一次地落第了。
这已经是第二回了,下一回考又得等三年,怎能不叫李屠夫着急?
李泽天说,家里太过于吵闹,弄得他不能静心念书。
王氏阴阳怪气地在旁边补充:“就几间房屋,却住了这么多人。”
李屠夫一番思虑过后,给了泽明夫妇二两银子,让他们搬出去另外过活。
家里的其他财物,肯定是不会分给他们的。至于住在哪,也需他们自己想办法。
陈氏心里很气,她对李泽天的那番说辞很是嗤之以鼻。家里就多她和泽明两人,这就叫人多吵闹吗?
几年来,她一直无所出,而王氏则是生下了两个儿子。若说家里吵闹,也是他家孩子吵。整日里屋前屋后的乱跑,追鸡打狗的,现在反倒全把过错赖到了自己和丈夫身上。
她无奈地对泽明说:“我两个在家里做着最多的活儿,吃着最差的饭菜,最后还要被人嫌弃赶出去,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泽明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他劝慰妻子:“算了,不计较这些了。好歹爹还给了二两银子,我们拿这钱去租个屋子住。”
陈氏心里的怒气难消,说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就二两银子能做啥?还不让你再去卖猪肉了,连吃饭的工具都收走,让我俩以后要如何生计?”
泽明边收拾衣物,边笑着说:“宁伯那里我已经说好了,虽是茅屋,但后院还有个猪圈,养几头猪是不在话下。自己养猪自己卖,兴许钱还能多赚些。”
陈氏摇摇头,没再说话。
衣物收拾起来很快,泽明去外面叫了辆牛车,两人就这么出了李家。

李屠夫不让泽明再卖猪肉,这里头是有个隐情的。
每日所卖的猪肉,本是去乡下收来活猪,然后自己宰杀,再拿到集市上去卖。可泽明不敢杀猪,他和另一个同伴去杀猪匠那儿得人家宰杀好了的猪,一人得一半。
这个猪的价钱,可就比自己宰杀的要高上不少。再加上泽明卖猪肉太实在,从来不肯缺斤少两。遇上确实有难事的,还会送给人家一块。他这样做生意,能赚几个钱?
李屠夫一辈子精明做事,攒下的钱财可不想被儿子这么败了去。
不仅他不想,儿媳王氏也不想。她比李屠夫还精明,算准了李家有多少家财。那些钱拿去放贷收利钱,都比让泽明做生意划算得多。
于是,怂恿丈夫,让他提出分家。
李泽天一个读书人,算账自然比妇人要厉害得多。不用妻子多言,他也知弟弟实在不是个做生意的料。一直这么下去,自己必定要被他拖累。
索性找个理由,让父母把事情解决掉。而最好的理由,莫过于把自己不中第的原因推到他们身上。
他心里很清楚,从小到大,只要一说有什么事情妨碍了自己读书,父母绝对会帮自己扫除障碍。
前面说了,李屠夫是个精明的人。家里的吵闹声源自哪里,他如何会不知?长子的弦外之音,他也能听明白。
思忖一番,决定遂了长子的意。毕竟,光耀门楣的事,只能指望他。次子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做生意,留下来无用。
和妻子商量,打算拿出二十两银子,让他们搬出去另外过。
李妻连忙制止:“使不得使不得,王氏心眼小,知道了必定要闹个不休,影响泽天读书。我瞧着,二两银子就已经足够了。”
见李屠夫还有迟疑,她接着又道:“泽明娶妻,我们是出了彩礼的。这次分家,陈氏必然会带着她的嫁妆离去。若他们的日子真到了过不下去时,她就会把嫁妆拿出来贴补家用,实在是不需要我们操心。”
李屠夫想想是这么个理,就按了妻子所说的行事。

泽明夫妇俩是不知道自己被家人这般算计。当然,就算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家中长辈说了算,他俩没有说话的份。
早与宁伯联系好的茅屋有三间,收拾好了,还是不错的。
说是茅屋,也不全然如此,其实是和瓦房相结合建成的。夫妇俩对此居住环境,还算满意,从心底里很感激宁伯。
宁伯家里是养猪的,泽明和他结识是个意外。有回下大雨,路上泥泞难走。宁伯由外头赶回来,不慎因路滑摔了跤。正巧被泽明遇见,背着他回了家,就此相识。
茅屋的后院,有个不大不小的猪圈。宁伯送了六头小猪仔给他们,说是乔迁之礼。
泽明不好意思地拒绝:“您没收我屋子的租钱,还要送如此大礼。惭愧得很,我们实在是不能接受。”
宁伯大笑:“这茅屋没人住,空着容易坏,我还得感谢你们帮忙维护它呢。这几头小猪,是我那几个儿子硬要送给你的,与我可没关系。”
宁伯有四个儿子,今天有两个跟来了,正在院子里帮着修葺猪圈。
其中一个大声地说:“泽明,这猪仔不值几个钱,你收着就是了。等养肥了需屠宰时,你说一声,我们来帮你。”
宁伯一家都是重情记恩之人,泽明内心相当感动,很庆幸自己能结识到他们。
善良,就像一束阳光,能够驱赶人们心中的阴霾。离开家时心里的怨艾,在此刻,都化为了乌有。

安顿好后,为了生计,泽明仍是要去杀猪匠那儿得猪肉,再拿到集市上去卖。
没本钱,做什么事情都难。如李屠夫两公婆所料,陈氏确实把自己的嫁妆拿了出来,换了银两,给丈夫当做生意的本钱。
泽明觉得很对不起妻子,让她吃了很多的苦。
但陈氏觉得,以前的忙碌是为了那一大家子人,而如今,却是真正为了自己。
没有了公婆和嫂嫂的故意刁难,她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有日,猪肉不太好卖,泽明弄到天黑了才归家。
路过城边的一条河时,在皎洁的月光下,他见到有个人坐在岸边。
心中觉得奇怪,这么晚了,这人怎么还不回家?
怕此人是有轻生的念头,他放下手中的推车,走过去问:“你需要帮助么?”
那人没吭声,仍是一动未动。
等再走近些,泽明看清此人原来是自己认识的,故语气放轻松了许多。
“沈婆婆,你怎么还不回家给孙子烧饭?”
心中闪过一丝疑惑,老人家里有位将近六岁的孙子,这个时辰了,按理应当在家里陪着他,怎么会在这里?
沈婆婆微微侧了侧头,看到泽明笑了笑:“我累了,走不动。”
泽明仔细看她,衣服好似湿了,问道:“您是不是掉水里了?”
沈婆婆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泽明想都未想,说道:“我把您放在推车上,可以送您回家。”
沈婆婆缓缓地应道:“好。”
泽明将婆婆背起,小心地放在推车上:“我知道您家住哪,您安心坐好。”
沈婆婆家里非常穷,一个人带着小孙子,过得很辛苦。平常泽明有卖剩下的肉,会特意绕去她家送块给他们煮着吃。
一路上,泽明怕沈婆婆闷,就与她说了些闲话。但沈婆婆像是真的很累了,很少应声。

走完这段小路,再拐个弯,前面两间破瓦房的屋子,就是沈婆婆家了。
她的小孙子名叫赵子墨,此时坐在乌漆抹黑的门前,瞪着眼睛往前面看。见到有人来了,怯生生地站起,不说话。
泽明笑着跟他打招呼:“子墨,我把你婆婆送回来了。”
子墨没有吭声,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沈婆婆没有叫子墨,而是跟泽明说:“辛苦你了,把我放在一旁就好了。泽明,能不能再麻烦你件事?”
泽明弯了弯腰,拿了之前子墨坐的凳子放进屋里。将她放在凳子上,又扶她坐稳。
开口问道:“婆婆,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开口。”
沈婆婆微笑着说道:“我今天很累了,不想再动。可孙子还没有吃饭,能不能麻烦你给他做顿饭?”
泽明一口答应:“这有何难,您先歇息,煮饭的事情让我来。”
米缸在灶间,泽明点了盏油灯进去。淘好米先把饭煮上。再出来到推车上拿了一大块肉重又进去,将肉切成小块,放锅里煮了。
他做事时,子墨跟着他进进出出,但就是不说话。
这孩子身世可怜,父亲在他两岁时为了救人,不幸溺水身亡。
去年不知为何,他的母亲又在河中溺亡。自此,这孩子就不再开口说话了,整日里神情都是木木的。
等肉熟的时候,泽明把他抱起来,从怀里掏出中午剩下的馍馍递给他。
“你饿了吧,饭还没这么快熟,先吃个馍馍垫垫肚子。”
子墨接过,将馍馍使劲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显然,他是饿极了。
馍馍很干,还没等泽明提醒他吃慢些,子墨就被噎住了。
泽明赶紧去屋里找水,桌子上有把茶壶,他伸手摸了摸壶身,是冰凉的。将壶提起,有点份量,里面应还有小半壶水。
顾不上那么多,倒了些在杯子里,就这么将就着喂给子墨喝。
这番忙碌过后,泽明顺便看了眼坐在屋里歇息的沈婆婆。发现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没敢打扰,轻手轻脚地走去灶间,烧了壶热水。
饭菜熟了,他用碗盛出来,摆在桌上。
“子墨,你先吃。等婆婆休息好了,你记得叫她吃饭。”
子墨不点头,也不吭声,还是静静地看着他。
习惯了他这样子,泽明没有当回事,自顾自地把余下的事情做妥当。
夜已经很深了,怕妻子在家等着心急。他没有叫醒沈婆婆,再叮嘱了子墨几句。把手上的水渍擦干净,推起自己的推车,回家去了。

果然,陈氏在家等得心急如焚。一见丈夫回来,便急忙问道:“你去了哪里,怎这么晚回来?”
泽明笑着安慰她:“我就是去了趟沈婆婆家,给他们煮了顿饭菜。”
陈氏面露同情之色:“那孩子真的是很可怜。”
泽明点点头:“是挺可怜的,今儿沈婆婆掉水里去了,做不动事。子墨那孩子饿得不行,给他块馍馍,都吃噎住了。”
陈氏的神情有些古怪:“你说……沈婆婆今儿掉水里了?”
“是啊。”泽明边收拾推车上的东西,边说:“怎么了?”
陈氏疑惑地看着他,稍顷,说道:“可……她今天下葬了呀。”
“这怎么可能?”泽明惊呼道:“我晚上还在河边见到了她。”
陈氏再一次向他确定:“这是真的。沈婆婆前日去河边洗衣服,不慎掉进水里。被人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村里的人每家凑了些钱买棺材,这才将她入土安葬。”
顿了顿,又道:“我们家也凑了一份,不信,你可以去问宁伯。”
泽明摇了摇头,仍是觉得难以置信:“这事,你怎没跟我说过?”
陈氏很纳闷:“昨天一大清早,曹家婶子上门来收份子钱,我跟你说了呢。不过,你在给猪喂食,没搭理我,我就直接拿钱给人家了。”
泽明细细想了一遍,好似有些印象。当时几个猪仔在嗷嗷叫,自己也不知她具体说了什么。
叹了口气,说道:“怎么他们家三个人,都被水给溺了!”
忽地想起一事:“不好,那子墨岂不是一人在家?”
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我再去趟他家瞧瞧。”
陈氏连忙跟上:“我也一道去。”
两人把屋门锁上,急匆匆地往外走。

沈婆婆家,灶间的灯还是亮着的。
赵子墨坐在门口的地上,呆呆地看着前方。前面是一片漆黑,不知他在看什么。
桌上摆放的饭菜,还如泽明离去时的那样,他一口都未动。
旁边屋里的凳子上,沈婆婆已经不在那儿了。
泽明忍住泪水,上前一把将子墨抱在怀里:“傻孩子,你怎么不开口跟叔说一声呢。”
子墨伏在他的肩头上,仍是没有说话。但泽明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肩头上的衣裳湿了。
轻轻地抚着子墨的背,对他说:“别害怕,婆婆虽然走了,但你以后可以跟叔叔婶婶一起过。”
陈氏也正有此意,她对泽明说:“孩子饿了,先喂他吃些饭。吃完,我们就带他回家里住。”
子墨像听懂了般,没有拒绝。眼里含着泪,一口口地慢慢把饭菜吃完,然后由着泽明抱他离开。
第二天,泽明去找里长,跟他说明情况。
子墨的一家人是外乡人,除了沈婆婆告知的事情,别的情况里长也是一无所知。
他正发愁不知该拿子墨怎么办呢,现在听泽明的意思,是想收养他,这就太合自己心意了。
连声说道:“好好,那以后就劳烦你们夫妇俩辛苦照看子墨了。”
末了,又问道:“是否要将他的姓,改为和你一个姓?”
泽明连忙摆手:“这怎么可以,赵家只剩他一个,我怎能抢人家的骨血。”
里长知道李家此子素来为人本份,不再多言。只说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上门来找他。

这事情在当地惹得不少人议论,有说泽明夫妇为人善良的,也有人说他们很傻的。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李屠夫夫妇听说了此事,气得跑来骂泽明:“混账东西,你屋里那个生不出孩子,不晓得娶个妾再生过么?偏要捡别人家的孩子来养,这算什么事?”
陈氏听到了,不敢出来,躲在屋里哭。子墨站在她身边,很是不知所措,也跟着流眼泪。
泽明见状,心里很难受。以往对待父母的责骂,他从来不会回嘴,这回实在忍不住了。
“妻子生不出孩子,不见得是她的事情,有可能是我的原因。我何必要再娶一个,去害人家呢?再者,我觉得子墨这孩子跟我很投缘,我是一定要养他的。”
李屠夫气得上前扬起巴掌打他,被闻讯赶来的邻居们拉开。
宁伯他们始终挡在李屠夫面前,不让他打到泽明。
李屠夫哪里会不知道这些,他用手指着泽明骂道:“以后,不许再进我李家的大门。”
说罢,带着妻子扬长而去。
他还真的说到做到,过新年时,泽明买了礼物给二老送去。结果,东西被扔出门,没让泽明跨进大门一步。
事情被宁伯知道后,以后每到年节时,他一家人便拉了泽明夫妇和子墨上自己家吃饭。
人情的冷暖让泽明常常感慨,家人还不如外人。
子墨还是如以往一般,呆呆地不说话,但泽明能看出他心中有极大的不安。故常常叮嘱陈氏,一定要对孩子好一些。
陈氏明白这个理,待子墨视如己出。家里有口好吃的,都先让着他吃。
子墨与他们夫妇俩亲近了许多。有回,居然肯开口说话了。
这让泽明惊喜不已。但惊喜过后,又仔细想他突然肯说话的原因。

每天一大早,泽明会从井边担水到家里的水缸,洗米烧茶水喝都用的是缸里的水。但陈氏洗衣服需大量的水,这缸水显然是不够的。
天冷时,陈氏会去井边打水洗。井水温温的,洗衣时手不会觉得很冷。这段时间天热了,她便拿了衣服到河边去洗。
前几回,因泽明回来得早,她便没带子墨去。那日总等泽明还没归家,陈氏不想等了,又不放心留子墨一人在家,就带了他一起去。
哪知才站到河边,还未蹲下,就被子墨扯住衣服拼命往后拉。
他哭喊着:“不要去,不要去……”
陈氏想,他是不是担心自己会掉入河里呀。
笑着跟子墨解释:“不怕的,这里的水浅,婶婶不会掉下去的。”
但子墨仍是哭闹着不停,拉着她的衣角就是不松手。
没办法,陈氏只好带着他重又去井边。
泽明听完陈氏的述说,以为子墨是因为他家人都因水而亡,从而对水产生恐惧。有心让他远离水,但又觉得因噎废食实在是不可取。
认真思忖一番,还是觉得应该教会他游水。一方面,可解除心头的恐惧;另一方面,多学样东西,总会有些好处。
这么想过后,泽明卖完猪肉回家早,就会带子墨去河里戏水。
奇怪的是,子墨非但不怕水,还玩得很开心。
泽明就觉得疑惑了,这跟自己想得不一样啊。
更让他不解的是,陈氏见他们玩得高兴,会拿着衣服过来,边洗边看着他们玩。
子墨见了,大惊失色,立即又要拉着陈氏离开河边。
总之,他不能看见陈氏站在河边,一看到就急。
泽明有些怀疑,是否子墨亲眼见到了他母亲溺亡的过程,才会如此容易激动。
于是,他让陈氏以后别去河边洗衣裳了,以免刺激到子墨。

每当子墨玩得开心时,泽明都试图让他开口说话。慢慢地,子墨不再像个闷嘴的葫芦,可以正常的与他们交谈了。
过完年,子墨被送去街上的一个大学堂念书。泽明已经打听过了,很多人都说那里的夫子学问高。
陈氏赶了几天工,做了个漂亮的新书袋出来。给子墨背上,再三叮嘱他要听夫子的教导。
去的前两天还挺好的,可到了第三天,他回来时,头发乱了,衣服破了,书袋也被人扯断了带子。
陈氏惊问他:“你是与人打架了吗?”
子墨摇头不说话。
陈氏没追问下去,连夜为他将衣服和书袋缝制好。
翌日,亲自送了他去。到放学时,又去学堂门口接他。
接送的这几日,都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偏巧有日临时有事,她去接晚了。结果,让她知晓了一个大秘密。
她去的时候,正见到几个大孩子在推搡着子墨。
为首的那个,嘴里骂着:“快滚,滚出这个学堂,不许再来。”
子墨回了句嘴:“你害死了我娘,才不敢看到我。”
那孩子恼羞成怒,又骂道:“你娘就是个短命鬼……”
子墨气得弯下腰,用头使劲去顶那孩子,把他顶到地上去了。
另外几人见状,一起上前要来打子墨。正好陈氏跑过去,护住了他。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合伙欺负一个比你们年纪小的孩子,好意思吗?”
那几人见有大人来了,一哄而散。
地上的孩子还没起来,见到陈氏,用手指着子墨先倒打一耙:“婶婶,是他先打的我。”
陈氏一瞧,这孩子自己认识。是李泽天的长子正誉,比子墨还大两岁。
她不好骂他,耐心地劝解道:“子墨现在是我们家的孩子了,也就是你的弟弟,你不能欺负他。”
正誉爬起来骂道:“哼,我才没有这样的弟弟。我要回家告诉祖母,让她来骂你们。”
说罢,他连身上的灰还未拍去,就跑了。

子墨惴惴不安,低着头跟陈氏说:“是他们先骂我的,每天都要我滚出学堂。”
陈氏摸了摸他的头,怜爱地问道:“真的是正誉害死了你娘吗?若不是,这种话不好乱讲的。”
子墨猛地抬起了头,看着陈氏的眼睛说:“婶婶,就是他害的,我亲眼见到了。他在水中喊救命,我娘去救他。他抓住我娘的手往岸上爬,上去就跑掉了。我娘却一头栽进水里,磕破了头,流好多血死了。”
陈氏很吃惊,对于子墨亲娘过世的原因,她多少有些耳闻,没想到里面还有这样的隐情。
带着子墨回到家,见泽明已经回来了。陈氏让子墨去写字,自己拉了丈夫到一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觉得,李家真是亏欠了赵家。子墨的娘为正誉丢了一条性命,嫂嫂他们一点表示都没有。”
泽明心有内疚之意,还未开口说话,门口处就响起了吵闹声。
原来,是王氏带着正誉,还有泽明的母亲蔡氏吵上门了。
王氏骂道:“捡了个野种到家里,还真当宝贝来养了。为了他,连我家正誉也打。”
蔡氏也骂:“陈氏,你给我滚出来。自己生不出儿子,就来打侄儿。”
陈氏皱起眉头,对泽明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连他的衣服都未触碰到一下。”
在另一间屋子里写字的子墨冲了出去:“李正誉撒谎,婶婶根本没有打他。是他带人骂我、打我,还侮辱我娘,我才用头顶的他。”
“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小小年纪就学会打人,看我怎么收拾你。”王氏一边骂,一边扬起巴掌就要打子墨。
“住手。”泽明出去,及时制止了她。
王氏悻悻地跟蔡氏说道:“娘,你看泽明,尽护着外头的人。”
她不好拿泽明怎样,但蔡氏可以啊。
果然,蔡氏扬起巴掌就对着儿子一阵乱打。

泽明没躲,对陈氏说:“你带子墨回屋去。”
陈氏点头,连忙扯着子墨进去了。
他们走后,泽明才跟蔡氏说:“娘,你怎么打我都行,但欺负一个七岁的孩子,就是不行。更何况,子墨的母亲是因为救正誉而死。你们这样待他,不是恩将仇报吗?”
蔡氏听了莫名其妙:“他娘的死,怎么可能和正誉扯上关系?”
王氏扯着嗓子喊:“没有的事,你不要听那小东西胡说八道。”
泽明没理她,耐心地把方才在屋里陈氏跟自己讲的话,又说了一遍给母亲听。
蔡氏半信半疑:“还有这样的事……”
王氏硬是不承认,捏了捏正誉的手:“你跟祖母说,有没有这样的事?”
得到了母亲的暗示,李正誉说话爽爽脆脆的,像是在下保证:“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蔡氏一向相信自己的孙子,以为是泽明胡说骗人,又开始打骂起他来。
宁伯走了进来,拦住了蔡氏。
“我在隔壁听到你们说的事,特意过来说句公道话。”
他说话客客气气的,蔡氏不好再撒泼,只能听他说下去。
宁伯说:“沈婆婆的儿媳妇救了一位李姓秀才的儿子,因此送掉了自己的命。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们可以出去找人问。”
蔡氏一愣,出口就是一句:“秀才多呢,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家的?”
宁伯似是嗤笑了一声,回她道:“我们这个地方,总共出了三位秀才,除了城东的邓秀才,还有城北的吴秀才,再就是你们李家的秀才了。前面两位年纪大了,且都迁去了别的地方,你说剩下来的还有谁呢?”
其实,蔡氏讲出那句话时,就知自己说错了,正后悔着呢。现在听宁伯这么一说,自知理亏,就不吭声了。
可王氏还是不依不饶的,嘴上硬得很:“别什么事都赖上我们家,以为我们家好欺负么?”

屋外面早就围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有人请来了里长。
里长见王氏不通情理,进来向蔡氏证实:“那年,沈婆婆的儿媳妇确实是救了你家孙子,有人看到了。”
说着,用手向左前方指了指,那儿站了一个年轻妇人。
年轻妇人点头,证实里长所言非虚。
“你孙子从我身边跑过时,我抓住了他,他还咬了我一口。所以,我记他记得很清楚。”
王氏还是不愿认账,强词夺理道:“就算她救了我儿子,那又怎样?你们不是把她从水里捞出来了吗?她的死,跟我儿子还是扯不上关系。”
她的话,泽明都不好意思听下去了。这事情再怎么说,都是因李正誉而起,王氏说话是一点担当也没有。
忍不住说了她一句:“嫂嫂,你是读书人家出来的,也是识了字的人。不会不知道穷人一旦受了重伤,无钱治病是种怎样的结果吧?”
沈婆婆带着子墨近乎是在讨饭过日子,她们怎么可能拿得出钱去治病呢?
年轻妇人叹了口气,也道:“当初,有人劝沈婆婆去找你们家要钱。沈婆婆没答应,她说你家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不是存心做错事的。”
蔡氏听了,只觉得一张老脸没处搁。王氏还待再狡辩,被她一把拉走。
“回去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大儿媳妇怂恿孙子当面说慌,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虽然对泽明很不满意,但是非对错还是能分清的。
她们走后,邻居也纷纷散去。里长和宁伯安慰了泽明几句,也跟着走了。
泽明以为,这事情就算是这么解决了。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此事,日后却招来了一场更大的祸事,险些让他家破人亡。

第二天上学,子墨不肯再去了。他说学堂里的夫子没有叔叔婶婶公平,看着他挨打,也不肯上前说句公道话。这样的夫子,是不可能教出好学生的。
小小年纪说出来的话,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泽明不勉强他。
附近还有所村子里办的私塾,里面只有一位夫子。虽说他时不时地要外出游历一番,但胜在极有才学,且人看上去还挺和善的。
跟子墨一说,他没有拒绝。于是,就把他转去那儿上学了。
三个月后的一日深夜,泽明睡得正香,突然梦里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她皱紧眉头一个劲地叫着泽明:“快醒醒,快醒醒。”
泽明仔细辨认,发现是沈婆婆,就问她:“您是不放心子墨吗?”
沈婆婆点点头:“大难临头了,有人要来杀他,麻烦你赶紧带他离开。”
泽明觉得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人要他的命?”
沈婆婆没有解释,只说:“日后你就会知晓,现在赶紧把子墨带走。”
又嘱咐道:“小心你兄嫂,他俩不是好人。”
泽明大吃一惊,这事怎与自家兄嫂有关?再想细问,沈婆婆却不见了。
蓦地惊醒,坐起身,把梦里所想的回忆一遍。觉得此梦必定事出有因,决定按沈婆婆的话照做。
唤了唤身旁的陈氏:“你赶紧回娘家躲躲,我需带子墨离开这里。”
陈氏朦胧中听得他这么一说,立即清醒了:“你睡糊涂了吧,大半夜的说这种话。”
泽明大致地解释了几句:“沈婆婆说得那么急,怕是时间来不及了。”
边说边起床,去另一张床上把子墨抱起来穿衣。
子墨还未睡醒,半闭着眼,伸出手配合着。
陈氏问泽明:“天这么黑,你们真的打算进山里去?”
泽明点头:“沈婆婆是这么说的。”
陈氏从床上爬起来,去灶间拿了昨夜里吃剩下的几张烙饼,找张油纸包了,塞进泽明怀里。
“带点干粮,别把孩子饿着了。若这里没事,我就去山里找你们。”
泽明皱了皱眉:“不是让你先回娘家躲躲吗?你一人在此,我怎能放心。”
陈氏看了看屋外:“娘家的路那么远,天还这么黑,你让我怎么回去?再说,我还要留在这里给你们通风报信呢。”
泽明想想也是,犹豫间,子墨拉了拉他的袖子:“带婶婶和我们一道走。”
陈氏摇了摇头,对他说:“叔叔带着你一个,可以走快些。我走得慢,会拖累你们的。”

时间紧急,来不及多想,泽明背上子墨,对陈氏说道:“你一个人在此,我也不放心。走,我们一起从后面抄小路上山。我识路,不会误事。”
就这么着,这三个人连屋里的灯也未点,静悄悄地从后门出去,朝大山的方向走去。
陈氏细心,拿了几件衣服。又怕山里凉,会冷着子墨,还抱了床薄被在手里。
没想到,这被子很快就给用上了。
三人才进山不久,天上突然下起雪来。且雪片还很大,纷纷扬扬的。
泽明觉得纳闷:“这六月的天,怎会下雪?”
陈氏边拿薄被盖住子墨,边说:“许是山里的天气多有变化吧。”
泽明不认同:“长这么大,我头一回遇上这种事。”
因急着赶路,他们也没多想。待再往山里走深了些,竟然又没下雪了。
陈氏抬头看了看天,说道:“这天好古怪。”
又看了看前面,问泽明:“我们是否去土地祠躲一躲?”
“不,去过一个地方。”泽明用手指了指另一处:“幼年时,我就发现那边有个山洞,不易被外面人找到。”
泽明说的这个山洞,确实不错,里面还挺宽阔的。
两人将洞里打扫干净后,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陈氏抱着裹着薄被的子墨靠在洞壁上歇息,泽明则出去找吃的,顺便打探下外面的情形。
站在山势高的地方,可以鸟瞰到山下的村庄。
这一看,可让泽明吃惊不小。只见山外白茫茫一片,很显然,昨夜的那场雪非常大。
他心里很奇怪,为何山上一点雪都没有?
回去把事情跟陈氏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在山上一呆,就是半个多月。这段日子,让泽明夫妇感觉度日如年。但对子墨来说,却是欣喜得很。
他跟泽明说:“叔叔摘的果子甜,烤的野鸡又香。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生活下去,那就好了。”
泽明苦笑:“现在这天气还好,等天凉了,怕是我们都得冻死。”
要在山里躲多久,他不知道,沈婆婆没有告诉他。这段日子,也没再梦见过她。
又过了几天,子墨早晨起来,跟泽明说:“叔叔,我梦见婆婆了。她说,我们可以下山了。”
泽明心道,为何沈婆婆没有托梦给自己呢?
故而半信半疑地问他:“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子墨很认真地回答:“是真的,婆婆说赵家的仇报了,我可以回家了。”
泽明和陈氏对视了几眼,两人都听着糊涂,但还是选择相信子墨的话。收拾一番,就下山了。

三人一进村,立即被人们围住了,大家七嘴八舌。有问他们这大半个月去哪儿了的,也有告诉他们家里出事情了的。
泽明虽听得稀哩糊涂,但有一点还是听明白了。自己家的没了,被人一把火烧掉了。
两夫妇看着那黑乎乎的一片断垣残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宁伯过来,让他们先去自己家里住,这里另外再想办法修葺。
去了不到一个时辰,官府来人,又把泽明和子墨请走了。
在这里,泽明才了解到事情的始末。
原来,子墨的身世很不一般。他的祖父原是太傅,极有学识。只是被奸臣所害,诬告其有谋反之意,结果被弄得满门抄斩。
官府抓人的那日,正巧赵太傅的小儿子赵良瑜陪着新婚妻子巩氏在岳丈家,他的乳母沈婆婆偷偷前去报信,让其带着巩氏逃离。
为了躲避贼人追杀,逃亡的路上无比辛苦。巩氏早产生下子墨,子墨身体孱弱。有回生病,赵良瑜上街为他抓药,被贼人盯上,惨遭杀害。
沈婆婆为了给赵家留一条后,来不及掩埋他的尸骨,匆匆带着巩氏和子墨逃走了。
来到此地后,为了掩饰身份,沈婆婆就说巩氏是自己的儿媳妇,子墨是自己的孙子,而儿子为了救人不幸溺亡等等话语。
赵太傅的门生遍天下,他们当中有许多正义之士,都觉得自己的老师是冤枉的。并且有不少人在暗中收集证据,只等合适的时机为老师申冤。
说来也巧,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村私塾的那位夫子。他叫吴若峰,是赵太傅的得意门生。在赵家出事后,他就辞官远离了朝堂。
最初见到子墨,他只是觉得这孩子眼熟,有几分像赵良瑜。后来无意中见到他胸前挂着的金锁,就很确定子墨就是赵良瑜之子了。
金锁本就是由吴若峰所设计,并亲手送给赵良瑜的。金锁里头有机关,他打开后,发现里面藏有奸臣的罪证。
他将其取了出来,表面上说是要出外游历,实际上暗中去了京城,联络其他同窗。

那夜,天降大雪,下到天明也未停止。这地方六月居然下雪,是何等的稀奇!
天有异象,此事必然惊动了皇上。
赵太傅的生前好友、以及他的门生们联名上奏,说六月下雪,必有天大的冤情才会如此。
他们把奸臣诬陷赵太傅,并且追杀其后人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又呈上奸臣叛国的证据,这才让皇上相信自己误杀了好人。龙颜大怒,当场下旨,诛杀奸臣九族。
赵太傅终于洗清了冤情,重新恢复名誉。赵家唯一的后人子墨被皇上派人欲接进京城,送到国子监去读书。
说到这里,还有件事情不得不提。为何那晚会有人去泽明家里放火?子墨的踪迹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
这一切全是拜李泽天所赐,这个人确实是聪明,只是聪明没有用对地方。
王氏在泽明家里大吵了一顿后,回去跟泽天告状。说起子墨娘的受伤,是因无钱医治而死去,跟自己的儿子无关。
一般人听到这里,不会多想。可李泽天不同,他立即嗅出当中有不寻常的味道。有可能是真没有钱,还有种可能,是为了躲避什么,不敢声张出来。
想到几年前赵太傅的案件,他把赵子墨跟那事自动关连上。一心想着升官发财的他,毫不考虑自己是否在昧着良知做事,带着王氏一起,立即去找人告发了子墨。
王氏心里恨着泽明和子墨,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还真被她说对了,别人一比对,立即查出子墨就是赵家的后人。由此,才有了前面的暗杀。
整场事情听完,泽明沉默了。他没有想到世事如此艰险,而人心居然这么叵测。

子墨得知自己要离开此地去京城,哭闹不休,抱着泽明不愿意松手。
他这一哭,让泽明心里难受得很。怕子墨这番前去,不得受人妥善照料。
吴若峰似是瞧出了他的心事,劝说道:“如今我已经官复原职,也正要入京,你们不妨跟我们一块走。反正你这里的家已经烧没了,到京城去,还可以谋个更好的事情做。”
泽明想想,是这么个理,也就答应下来。
回去和宁伯一家、以及乡亲们告别,带着陈氏一起随子墨入京。
只是,他没有回李家,没有想着去和自己父母说一声。
他的心凉了,对他们失望透顶。
李泽天夫妇其实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好处的,有人气愤他们的小人之举,特意在皇上面前告了他们的状。
由皇上下旨,从李泽天这代算起,三代不允许考功名。李屠夫想靠着李泽天光耀门楣的梦,彻底地被打碎了。

接子墨回京的官员,是赵太傅的门生。他感恩泽明对子墨有相救之恩,邀了几位同窗一起,大家捐资在国子监附近买下一个宅院,送给泽明夫妇住,这样也方便能照顾到子墨。
妥善安排好后,子墨自此安心读书。他的几位夫子,有曾是赵太傅门生的,也有仰慕赵太傅才学的人,对于子墨的教导,无不尽心尽力。
子墨本就是聪慧之人,几年内广览诗书,九经三史,无不通晓。十八岁便高中了状元,为赵家光耀了门楣,续写了他这一代的传奇。
不过,子墨成亲后生下的长子,并不是姓赵,而是姓李。
李泽明夫妇没有亲生子嗣,子墨就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儿子,故而长子姓李。生下次子后,才取了赵姓。
泽明夫妇二人,一直由子墨侍奉到老,寿至九十,无疾而终。而子墨的才学如他祖父般过人,屡受褒封。
两子长大后,先后登第。虽为两姓,但兄弟交好。至今两族子孙繁盛,多为有才学之人。
(此文由笑笑的麦子原创首发)

生活是很真实的柴米油盐,一箪食,一瓢饮。我是笑笑的麦子,谢谢您的阅读,欢迎在下方评论或留言!如果大家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希望大家能为我点个赞,并关注我一下,最后别忘了帮我分享,转发一下哦!特别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