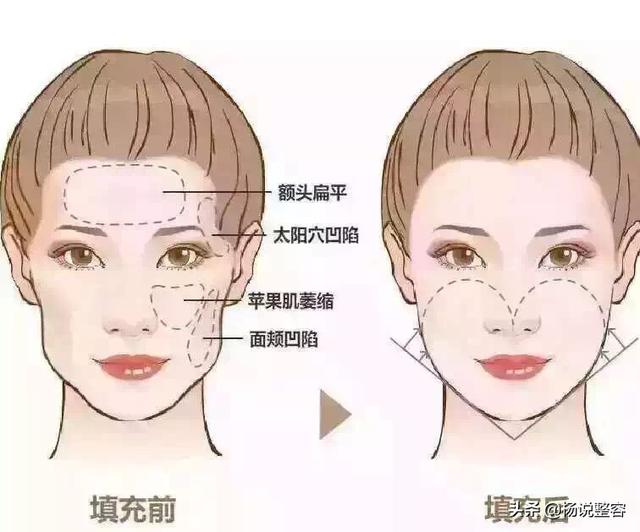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瞿鹊子问长梧子:“孔夫子说,‘圣人能游乎尘埃之外,对她而言,以无限面对有限,一切变幻终为泡影,稍瞬即逝,一切都在时间里变化消融。所以她不执着于‘不常’。她不问世事,她不趋利,她不避害,她不喜求,她游离于人道之外。人世有多少的言语,有多少的观念,有多少的价值,能经得起人世的抢夺与杀戮!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经得起世事的无常!它们也如同生命一样,起起灭灭。前后之间,也许有传承,也许有相似,但所有的共同不过是因为人性的不变。‘无谓有谓,有谓无谓’。既然如此,即便我告诉你真理,它也会消失;即便我不告诉你,你也会找到。它如同人一样,在经历着生生死死;也如同人一样生生不息。’孔夫子认为这是无稽之言,我却认为这是道之奥妙。你认为呢?”
长梧子说:“这些话即便是黄帝听了都茫然,孔丘又怎会明白呢!不过你的想象力是真的惊人,见到鸡蛋就想到了鸡鸣报晓,见到弹丸就想到了烤得香喷喷的鸟肉。好吧,我姑且说说自己的见解,你姑且听听吧。圣人的世界不止在人间,更在日月星辰。她对宇宙万物的变幻感同身受,她明辨万事万物的无常。世人执着的是非尊卑不过是一种无常。圣人有至大的视野,她无私无情,她不偏不倚地看待世间的一切。她在万古的时间长河中,她看着一切起起落落、生生灭灭又生生不息。她不为物喜,不为物悲,她参透了无常,亦参透无常背后的常,她体悟了这世界的本源。有限是建立在无限之上的,正因为如此,有限才能衍生出无穷的变化。万物既常又无常,万物如此。世人只为无常熙熙攘攘,而圣人视无常如平常,无波无澜。
人只知生前,从不知死后。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贪生不是自己被迷惑着呢?你怎么知道怕死就不像迷途羔羊般不知归途呢!守疆人之女丽姬是一个大美人,她刚成为晋王的女人时,哭得衣衫湿透。但等到晋王带着她离开边疆,来到辉煌的宫殿,和王同眠,与王同吃人间美味之后,她才知道当初不该哭泣。同理,你又怎么知道自己死后不会后悔当初的恋生呢?
梦里饮酒欢庆,你醒来却面对一堆悲伤的事,你知道昨夜的梦只是梦。梦里悲伤不已、痛哭流涕,你醒来要进行的却是一场狩猎快事,你知道昨夜的梦只是梦。但你身在梦中之时,却不知其为梦也,醒来方知是梦。如果梦中还有梦,那你怎么知道是梦还是醒呢。只有大知大觉之人,才会发现生命亦如同梦一场,方生方死,无不以待尽。生命存在了又消逝了。觉也好,梦也好,未来都有一个结束的必然。你觉了,你是在梦里;你梦着,你也在梦里。统治者在梦中,被统治者在梦中。孔夫子在梦中,你在梦中。即便是我现在能告诉你生命如梦的真相,但我亦是在梦中,在生命的梦里。
这些话超乎一般人的常识,因为他们的认知仅限于自己生活的所知所及,而这以外的内容是蒙昧与黑暗的,他们看不到听不懂。当我告知他们认知空白领域的内容时,他们肯定觉得吊诡荒诞。万世以后,若有人了悟到这些内容,我们一样能穿越时空的限制成为知己!”

随记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跨越时空的知己。
圆觉经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圆觉经的这段话跟庄子对梦的表述是不是极为类似。
圆觉经说,“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
庄子《外物》篇说,“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参万岁而一成纯”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一意各表。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
是圣人能游乎尘埃之外,所以能“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是结果,而非原因。
逍遥游“天地之正”那段是从正面描述,这里则从侧面描述。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
以人的角度来看,世事难有一帆风顺。顺逆时有,利害时有。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若一切都以外在参照,顺时顺,逆时逆,最后如池水中飘叶,随风飘零打转。
以人事的目的来看,所有让目的偏离的路口都别选择。通往目的的路时上坡路,偏离目的的路是下坡路;或者通往目的路是下坡路,偏离目的路是上坡路。
以世事的变化来看,利害得失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所有的价值,所有的观念,所有的信仰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处在其中不代表永恒,人的生命实在短暂。
若人的生命长一百倍或短一百倍,人所有的东西都会被重构。其实不用一百倍,即便两倍,现有的一切也都会被颠覆重构。
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
不痴迷于一“不常”。人之道亦无常。
缘常,不缘不常;缘一,不缘分;缘本质,不缘表象
人之道无常,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道注入属于自己的内涵。人之道常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能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止一种。人之道为生产关系做现世的注解与支撑。故常新。
天之道只能知,不能达。可望不可及。退而求其次,才有人之道。人之道,承于天而及于人。天道无限,人道有限。人之道如同生命一样,起起灭灭。
所有人能适应的内容都无法摆脱人的极限。人能践行的道,最适合的就是人之道,是人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
人会参考天道,但只能践行有限度的天道。这些被践行的内容最终演变成人道。
无谓有谓,有谓无谓。
以无限面对有限,无限中有无限变化,但一切变幻终为泡影,稍瞬即逝,一切对立都在时间里变化消融。有多少的言语,有多少的观念,有多少的价值,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经得起世事的无常,能经得起人世的抢夺与杀戮。它们也如同生命一样,起起灭灭。前后之间,也许有传承,也许有相似,但所有的共同不过是因为人性的不变。既然如此,即便我告诉你真理,它也会消失;即便我不告诉你,你也会找到。它如同人一样,在经历着生生死死;也如同人一样生生不息。它在,它也不在。它不再是曾经的样子,但又有曾经的影子。
有限如何趋向无限,庄子的话很传神:“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价值,是非,利害,人之道等等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因为它们都是实在。
张岱说,“昭庆寺,自狮子峰、屯霞石发脉,堪舆家谓之火龙。石晋元年始创,毁于钱氏乾德五年。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天禧初,改名昭庆。是岁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建,廉访杨继宗监修。有湖州富民应募,挚万金来。殿宇室庐,颇极壮丽。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乱,恐贼据为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舆家说,辟除民舍,使寺门见水,以厌火灾。隆庆三年复毁。万历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止。崇祯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及至清初,踵事增华,戒坛整肃,较之前代,尤更庄严。”
你从张岱的这段文看到了什么,原来昭庆寺一直在重生,但一直在重生的其实不止昭庆寺。那些我们耳熟的文化标记其实也都是毁了再建,毁了再建。每个时代的重建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但那个标记一直在。它既在,又不在了。这文化现象其实很有意思。
人之道是从天之道中抽取变形为人需要的。或者直接从人的一切抽象得到人之道,自得的人之道与天之道有某些相似。这种相似有人认为是传承。我认为相似是必然的,无论你如何得到它,因为它源自现实世界。
如果从“物为道之形”来理解,人之道其实也是物的一种。
以道观之,物无分别,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物有分别,物无贵贱。
以人观之,物有分别,物有贵贱。
人之道其实已经坍塌为规则,精神,价值,观念。与天之道能衍生万物是区别极大的。一着有限,一者无限。人道有限,天道无限
无限才是真正的全,但生命永远达不到无限。因此人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全。
人最长久的生命是人自己的历史,人失去了历史,人将失去最宝贵的财富。历史里有人最大的时间尺度,有人最多的变化累积。
人依附于地球,而地球在宇宙中是极小极脆弱的存在。宇宙的时间尺度相对人来说是极大的。若将宇宙的生命浓缩为一年,宇宙尺度的一秒,相当于人尺度的千万年。
吻合,体验全部变化历程。我经历了你的一切。
相蕴,常与不常相蕴。
连续的世界。
你梦里饮酒欢庆,你醒来却面对一堆悲伤的事,你知道昨夜的梦只是梦。你梦里悲伤不已、痛哭流涕,你醒来要进行的是一场狩猎快事,你知道昨夜的梦只是梦。但你身在梦中之时,却不知其为梦也,醒来方知是梦。如果梦中还有梦,那你怎么知道是梦还是醒呢。只有大知大觉之人,才会发现方生方死,无不以待尽,生命亦如同梦一场。来了然后走了。觉也好,梦也好,未来都有一个结束的必然。你觉了是在梦里,你梦着也在梦里。统治者在梦中,被剥削者在梦中。孔夫子在梦中,你在梦中。即便是我能告诉你生命如梦的真相,但我亦是在梦中。在生命的梦里。
有人说这梦就是天之牢,谁也逃不脱。
你知道人会做梦,但你又知不知道生命本身就如同梦一场。
罗贯中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村上春树说,“你睡了,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梭罗说,“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
杜卡尔说,“宇宙万物亦真亦幻,即像一个梦境,又似一场电影——眼前的景象犹如雾里观花,水中望月,须臾变换,捉摸不定,其浩瀚无边的整体展示让人不可思议,但对当下的生命而言,它却似乎又是真实的。”
方生方死,无不以待尽,生命就如梦一场。来了然后走了。觉也好,梦也好,未来都有一个结束的必然。你觉了是在梦里,你梦着也在梦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还重要吗。
有人说这梦就是天之牢。
普里高津说,“古人是完全知道世界是流动性的,是变动不居的……但他们虽然认识到这个事实,却又惧怕这个事实,而设法逃避它,设法建造永久不变的东西,希望可以在他们所惧怕的宇宙之流中立定。他们得了这个病,这种追求永恒不朽的激情。他们希望建造一些东西,好让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人,是不朽的。这种病的形式不下千种,有物可见的如金字塔,精神性的如宗教教条和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
马拉美说,“所有的语言都是残缺不全的。……当我想到语言无法通过某些钥匙重现事物的光辉与灵气时,我是何等沮丧!”
郑开说,“譬如海德格尔分析‘自然’这个词,他觉得这个词本身就是绽放、涌现,‘事物的涌现’,‘自身开放(如花的开放)的涌现’。又比如说‘真理’,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真理就是去掉一种遮蔽,进入澄明之境。真理是一种敞开,这是他反复强调的一点。”
郑开说,“《庄子》中的神明,也是一种光亮,不仅驱散了黑暗也同时呈现了自己。其实,我们对‘道’的解释,也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郑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你要想毁灭一切,什么都不需要去做,你只需要取缔人类关于上帝的观念就可以了。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因为上帝代表了人类正面的价值。人之所以能得到拯救,人之所以能生活、能有希望,都是因为上帝,整个西方文明就建筑在上帝的观念之上。你把它去掉,旧的世界观自然轰然倒塌,其中的一些旧的道德也将全面覆灭。这样一来,新的东西才会出现。我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这一点在气质上和道家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比较接近。庄子直接去除圣人的观念,包括尧、舜、禹、汤,甚至也包括黄帝。我们知道,战国中期的时候,黄帝的地位正在形成,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被确立为一个圣人,确立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但奇怪的是,在《庄子》这部书里面,黄帝的形象有点游移不定,他有时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有时却又是一个祸乱天下的罪人,甚至连小孩都不如,是一个对道的真理非常隔膜的人。那么,这其中透露出什么消息呢?其实,答案已经给出了:对于这些偶像,庄子要全面地推倒。”
郑开说,“无论是尼采还是庄子,他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个体,每个生存的个体、有生命的个体都面临着与存在---那个更本质的存在,那个比我们生命更广阔、更复杂的存在的联系和交涉,并且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棘手的困难,难在不易或者说无法谦诸抽象思维、概念语言来表达(那个存在)。”
郑开说,“倘若从‘物’的角度来看‘化’,从‘道’在物中不离于物的角度来分析,这其中还贯穿了一层‘不化’的意思。”
郑开说,“如果说汤川秀树设想了一个最基本粒子,它不像传统的原子论理论模过下的基本粒子,这样一种最基本粒子似乎可以称之为‘无’!”
郑开说,“苍茫时分的暮然回首,灯下偶然的惊鸿一瞥,半梦半醒之间的惺惺之悟,游离于喧哗与骚动的若有所思,痛苦与狂喜之心潮沉寂后的妙音,凡此生活中闪现思想光辉的瞬间,都会有某种空谷足音、他乡遇故交的莫名感动,当然还有那种不可解释的兴奋。庄子就是这样的空谷足音,神交已久的故旧,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章太炎说,“‘无谓有谓’者,《寓言》篇云‘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谓无谓’者,《寓言》篇云‘终身言,未尝言也’。”
章太炎说,“知生为梦,故不求长生;知生死皆梦,故亦不求寂灭。”
福永光司说,“一日孔子门下弟子瞿鹊子向得道者长梧子问道:‘我的老师孔子曾说,圣人,也就是绝对者,他们超脱于世俗之外,不沾染任何俗世。将利害视为一物,既不趋利,亦不避害。不因为人所求而欢喜,也不一味拘泥于道而墨守成规。而且,他就算沉默,也是在用不能言物之语诉说着什么。就算他说话,所说内容也只是无心之言,与沉默没有区别。他虽然置身于世俗之中,可他的心却远远逍遥于世俗之外。然而老师本人却否定了这由他亲口描述的绝对者,认为这般境界,到底是现实不需要的,至多不过是虚构的言论、观念的游戏罢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顿悟大道的绝对者该有的高尚实践。您又如何认为呢?’
长梧子听罢答道:‘绝对者的境界, 据说就连被称为无上智者的黄帝听了后,都无从判断其中真伪,更遑论孔子?他无法理解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是一个将‘未知生,焉知死”贯彻得很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孔子如此便罢了,可你竟然也同样急于求成,居然以为那点儿肤浅的理解就算是看透了绝对者的伟大了。你看,不是有这样一个比喻吗,见到一颗还未孵化的蛋,就想着让它打鸣叫早;看到一粒用来打鸟的弹丸,便想着要吃烤鸟肉。你且听好,接下来,我就为你仔细讲讲,绝对者真正的伟大和他真实的姿态。不过,这真实之态并非是语言能够描述得清的。所以这至多只是姑且说明之,我也无法保证能将那真实说出几分来。你可要记住这一点。
所谓绝对者,他那伟大的德行仿佛普照万物的日月光辉;那伟大的包容力甚至能将这浩瀚无垠的宇宙轻松夹于腋下。他与道一实在本身融为一体,摒弃一切区分与安念,将暗淡摇曳的‘不明之明’,当作自己的智慧,将自我置于奴隶般的卑贱地位,从而尊重所有人。世人一味沽名钓誉,一生过得犹如拉车的马匹,苟延残喘。绝对者则不同,他舍弃是非区分,将利害得失视为一物,在无心忘我之境中安然享受自我的愉悦。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与一个愚钝之人并无两样。他融入永恒的时间中,与时间本身合而为一。以这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维持自身的纯粹性。在他眼中,一切存在的矛盾与对立保持着原本之态,他将万物纳于与道为一体的自我之中。所谓绝对者,便是将此境界作为自身境界的至高至大之人。’
‘之前那些说的主要是绝对者的伟大。接下来就顺带着再多说几句吧。’
‘其实我吧。’长梧子继而说道,‘不理解世人为何会因生而喜悦,因死而悲伤。世间之人为生而喜,但这欢喜的感情不正是人们可悲的安执吗?世俗之人憎恶死亡,但死亡难道不是人类回归原本自然吗?自幼背井离乡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四海为家,虽然可能会忘记自己本该归去的故乡,但失去故乡之人真正的悲剧,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憎恶死亡吗?’
‘古时候有一美人,名为丽姬,本是艾国一守疆人的女儿。最初,晋国俘虏她时,她为自己不得不被掠到他国去的悲惨命运而悲伤,眼泪如雨点一般沾湿了胸前的衣襟。然而当她终于被带进了晋国的官殿,与晋王同卧一塌, 每日珍饶不断,她感到了无比的幸福,不禁为之前自己流的眼泪感到后悔。谁又能保证,生与死的变化就一定与此不同?为自己曾哭喊着想要继续活而感到后悔。死去之人也许同样会因自己曾哭喊着想要继续活而感到后悔。’
长梧子仍旧娓娓道来。
‘另外,在梦中饮酒作乐之人,月落日升,便会因悲哀的现实痛哭流涕。相反,那些在悲伤的梦境中涕泗横流的人,到了白天却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地出门打猎。身处梦境之人,是无法意识到此处便是梦中,甚至还会在梦中再起梦中之梦。只有在真正醒来之后,才会发现那竟是个梦。人之一生,也是如此。无数人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梦境活着,又在这梦境般的,生之中追求着无止境的梦。然而,清断意识到这是梦的人,竟能有几个呢?
不过,若想要意识到这梦境的真面目,就必须要经过一次伟大的觉醒。只有伟大的觉醒者,也就是顿悟了绝对真理的人,才能从那巨大的梦境之中解放出来。然而那些愚蠢的世俗之人,自认为已从梦中清醒,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将自己看重的人尊为君主,如对待奴隶一般轻贱自己厌恶的人。这都是些爱憎好恶的偏见,他们却引以为豪。简直是冥丽不灵、无药可救。
说到底,孔子把绝对者的存在说成是‘孟浪之言’---荒唐无稽的观念游戏,你却还大赞孔子的这种言论为‘妙道之行’---是解脱者的伟大实践。你们两个都做着一场春秋大梦。不,不止是你和孔子。我认为你和孔子都在做梦,但我自已其实也是身处梦境之中。不过,像我这样把一切都说成是一场梦,这种言论实在是很奇特怪异,从常识来想是很难接受的吧。所以我的这种论调才被称为‘吊诡’,也就是迥异于世俗常识的至极之言---怪诞之谜。但是,能够揭开这谜团的绝对者,恐怕几十万年也遇不到一个吧。就算几十万年中有幸遇到一个,与绝对者的相遇,甚至可以说是如同在每日日出与月落之间相遇一般,皆是十分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