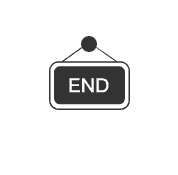摘要:以福建平潭为例,采用统计法与空间分析法对海岛地名类型进行划分,探究其命名内涵、特征及其反映的人地关系。研究发现:海岛地名以方位、地形、方言、聚落为主要命名依据。命名突出形象性、通俗性、实用性、大陆渊源性与海岛个性。其中以物产、方位、宗教等命名的地名反映出人类对海洋环境的认知与主动适应;而以人类意志命名则反映出“人定胜天”的人地观。最后,提出海岛“地理环境—人—地名系统”概念,阐述地名与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过程:最初地名是人类对地理实体的直观反映,命名形象直观,实用性高;随着人在人地关系中主导作用越强,命名依据越脱离地理实体特征,而更多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特色。地名与人地关系存在时空错位,前者变化常滞后或超前于后者变化。地名具有调解人地关系矛盾的作用。关键词:海岛地名;命名特征;人地关系;机制;过程;平潭县作者:纪小美 付业勤 程珊珊地名学是研究地名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地和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与地理学研究对象——人和地之间有很大的交叉处,地是二者共同的研究对象。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以区别地理实体及其类型间的差异性,是人类认知与实践活动作用于地理环境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景观。因此地名与人地关系存在密切联系。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者关注到地名所反映的人地关系及其区域特点:王彬等分析了广东地名层形成的原因,发现历史时期移民的繁衍和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加剧了区域内人地矛盾,而这一矛盾推动族群地名文化不断扩散;何彤慧对比研究了“沙”与无“沙”地名,揭示了人类干预下的毛乌素沙地环境变迁;王荣等分析了盐池县聚落地名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并提出了地理环境—人—聚落地名系统,发现盐池人地关系以稳定为主,但也存在人地关系紧张现象,北部风沙区人地矛盾很突出。而国外已经开始关注居民对地名的感知及其差异,借此来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当地生态可持续管理、优化景观布局等。
盐池县自然景观
相比上述对大陆型地名文化的研究,学者对海岛型地名文化的研究侧重其个性化特征及其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王建富、孙峰等从海防、围垦、迁民、殖民、盐业、海岛地名独特性等方面对舟山群岛地名文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彭静发现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塑造了涠洲岛的地名文化景观,其地名文化景观反映出了海岛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杜娜研究了历史上移民在海南岛上的分布与迁徙路线,朱竑阐述了开疆文化在海南岛上的扩散过程及其区域影响。对台湾海岛地名的研究侧重两岸地名渊源关系,台湾独特的殖民文化、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两岸文化认同等。Weslager发现美国奥克拉科克岛的地名简单且平淡,反映了海岛渔村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Mead研究了所罗门群岛圣安娜地区民俗对地名命名的影响;Gunter基于景观类型制定了海岛地名的分类方案。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地名在人地关系研究中价值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目前仍以大陆地区为主,对海岛地区的研究较为薄弱,而主要涉及其地名的渊源、特点、类型;虽然已有学者探讨了地名体现的人地关系,但还未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进行探讨;国内学者多关注省、市尺度的海岛或著名的旅游型海岛,还未关注一般海岛县的地名。因此,文章以福建平潭县为例,矢量化《平潭县行政区划图》(1:100000),提取归纳相关地方志资料中涉及到的平潭海岛地名。采用统计法与空间分析法从人地关系视角研究平潭海岛地名命名特点及其与人地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过程。一则有利于认识海岛地名在海岛人地关系研究中的价值;二则从新角度了解平潭县人地关系状况,给予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过程中人地矛盾的调解一定启发。
一、
海岛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
海岛是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复合区域,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隔绝,构成一个相对封闭而又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人类在海岛上的活动创造了海岛的人文环境及其文化。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与贫乏的资源条件造就海岛相对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对人类活动反应更为敏感,因而成为研究人地关系及其演变的典型区域。平潭县海岛自然与人文特色鲜明,人类活动足迹由来已久,当地居民对海岛环境的认知、适应与改造而产生的人地关系及其演变对于海岛人地关系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平潭县地理环境概况
平潭县地处福建东部海域,位于北纬25°16′—25°45′,东经119°32′—20°10′。东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大陆与台湾距离最近的一个县;西隔海坛海峡与福清、长乐、莆田3县市为邻。平潭地处海上南北交通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海防重镇。全县陆域面积321.38km²,海域面积6000km²,海产丰富,渔场遍布。平潭县由近千个岛礁组成,其中有名岛屿126个,礁石500多个。岛屿岸线曲折,基岩、沙质和泥质海岸兼具。主岛海坛岛因其形似坛、兀峙海中而得名,由于岛上经常“东来岚气弥漫”,又称“东岚”简称“岚”。主岛面积278.61km²,属大陆岛,为我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地形以海积平原、丘陵为主,中部多海滩平川,南北低山丘陵面积占全岛的40%左右,最高峰君山,海拔434.6米。东海岸多海湾、港口及暗礁,西海岸多泥沙、滩涂。河流短小,季节性强,水系不发达,淡水缺乏。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变律大,旱涝无常、风灾频繁。石英砂、贝壳、海盐、海洋生物等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匮乏,多为坡地、沙壤,全县风沙地占土地面积30%,易水土流失与盐碱化,不易种植水稻,以花生、番薯等旱地作物为主,产量低。植被种类稀少,群落结构简单,多为解放后为防风固沙用而栽植的相思树、木麻黄、黑松等逆行演替的人工植被。产业上历来以渔业和农业为主,产值占到全县GDP60%以上,城镇不发达,渔村、农村占主体,除城关镇外其他所有乡镇均从事渔业生产。
平潭县地图
(二)平潭县海岛人地关系演变
平潭历史文化悠久,从壳丘头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可以判定早在五六千年前其境内就有闽越族人活动的迹象,并且当时自然环境优越,植被茂密,物种繁多。“海坛在县(福清)东大海中,广袤七里,又名东岚,去县道百二十里。旧产马,故唐为牧马地,宋初设牧监,即废”。可见唐代伊始海坛岛的植被已退化为以草本、灌木为主。五代,中原移民大量迁入海坛岛,至宋代,岛民以农业为主,渔农杂耕,人丁兴旺,“八百里,户三千”,并增兵驻守。宋末元初,大陆居民因战乱大量迁入海坛岛导致人口再次大幅度增加,至元末明初已“户以万计,第宅相望,多渔业”。平潭这一称呼始于清初,嘉庆年间人口增至6万而设平潭厅。明末清初明郑水军驻扎于此与清兵对峙,伐木造船,进一步破坏了岛上生态,良田不断被海沙侵蚀,土壤肥力下降,农业转以花生和番薯等旱地作物为主,民众以地瓜为主食。1912年平潭立县,辖境人口12万。清末至民国期间,平潭自然灾害多发,加之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自然环境恶化,虽然有识之士也倡导过“种草护埔,严禁采樵”,但社会秩序混乱,无暇顾及,人地矛盾突出。民间信仰盛行,寺庙遍布,香火缭绕,民众多期盼神灵的超人间力量去战胜天灾人祸。建国后,生产关系彻底变革,生产力迅速提升,开展大规模围海(湖)造田,城镇建设,工业发展,营造防护林等改造自然的运动,满足人类社会发展所需。人地关系中人开始起主导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将生产(大)队作为全县聚落通名可窥一斑。直至当今,平潭县大规模资源与空间开发的态势有增无减。
二、
海岛地名类型统计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到平潭县现存海岛型类地名1124个,可分为自然地理实体、人文地理实体两大类,大类又可细分为若干亚类(表1)。由于部分地名可由多个要素组合而成,同一个地名可能同属于多个类型区,因此,分类后的地名要素量要大于统计到的地名总数。地理实体类约占6成(排除类型交叉地名),其中相对方位(26.96%)、相对大小(8.54%)和地形(6.32%)比重较大,与水体有关的地名(2.67%)比重不突出。可见相比与水,地形要素对居民择岛定居的影响更大,也符合岛上多丘陵台地少河塘的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实体亚类中聚落(11.83%)、方言(12.46%)和重名更名(6.85%)位居前3,早期渔民出海活动范围有限,因此岛礁、港湾和岬角通常以附近聚落为参照命名,命名方式多为:方位词+聚落名称;方言类地名则反映当地民众独特的思维与语言表达方式,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平潭海岛地名中保留了大量方言的谐音字和自创字。重名现象的产生与海岛生活、生产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以及高相似性有关,重名更名则是适应当今海岛日益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规范化做法。
三、、
海岛地名命名特征
(一)命名的形象性与通俗性
地名产生之初,其文化内涵单薄,形象思维占主导,用词朴素。这类地名大量存在于平潭地区,表现为将生活用品(畚箕、斗笠、舂臼、鼎、秤锤)、食物(光饼、馒头)、渔具(网、箩)、家禽家畜(牛、马、鸡、猪)、海洋生物(鱼、蚶、螺、鲎、龟)、飞禽走兽(鹭鸶、虎、兔、鹿、猴)等的名称都搬进了海岛地名,直观描述岛礁的形态、便于记忆。另外,历史上移居平潭的民众多为迫于生计的普通百姓,渡海的危险和艰辛使得文人墨客很少涉足于此,历史上平潭县科举及第之人也寥寥无几,在官方海域地名普查前,平潭许多岛礁地名口语化色彩浓厚。例如棺材石、鸡屎礁、牛屎礁、拉鸟屎礁等,统计到带“屎”字的地名就有16处之多,地名规范化后多用“使”替代“屎”,但部分原地名仍为民间所沿用。此类地名多分布于主岛周边岛礁,而主岛上的城镇街道地名则普遍较前者文雅。
(二)命名的实用性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与认知能力的提升,地名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不断改进,实用程度越来越高,更有助于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在人地关系中发挥出人的能动性。
1、指明物产、生计。平潭县花岗岩、石英砂、海盐、风力潮汐等资源得天独厚,滩涂、海滩辽阔,岛礁众多,渔业资源异常丰富,充分反映在海岛地名上。指明岛礁、湾澳附近存在的海洋生物:以鱼类命名有鳀礁、虾礁、鲙撮礁、石鰶礁等,以鸟类命名的有鹭鸶磹、鹭鸶岛、老鹞屿等;以植物命名的有草屿;以海洋软体动物命名的有蛏土澳、福螺礁,壳屿等。指明聚落生计环境的有砂美村、盐田村、渔屿村、渔庄村、鱼塘村等。2、警示危险。多用令人生畏的“虎”、“蚶”或“蟹”(暗喻船只好像被钳住而触礁)、“棺材”、“鬼”、“魂”、“翘”等词来命名那些曾经发生过海难的岛礁(特别是暗礁),以警示后人,牢记教训。例如五魂礁,纵横五礁,潜伏海中,险礁,故名;虎礁,礁险恶,被称为虎礁。3、辨明方位。在被参照地理实体地名前后加方位词是平潭海岛地名最大特色,不仅可以避免重名,而且能够使后来人更加容易地辨明周遭岛礁的空间布局以及自己所处的相对位置,还利于航行定位,从而降低对陌生海域、海洋突发灾害的恐慌,加快对海岛特殊环境的适应。这类地名的比重最大,分布最广,实用性也最强。4、引导。位于航道上,并处于其他岛礁之间的岛礁,一般取“限”为通名,即方言“门槛”,有妨碍之意,统计到13条此类地名,有限门礁(位限礁屿,塘屿之间故名,是渔船的必经之路)、限屿礁(在天礁与塘屿之间,妨碍航行,故名)、中限屿等;部分岛礁作为水道航标,取“标”做通名,例如西标礁(位于峻山岛西,是船只经海坛海峡北东口水道的航标)、西标仔礁(因邻近西标礁,礁小而名)。
(三)命名的大陆渊源性
地质历史演变来看,平潭诸岛屿几乎都为大陆岛,自然景观与其西侧大陆有一定的相似性;平潭主体文化源于大陆,陆岛间频繁的社会经济交流,在海岛地名的命名上体现出鲜明的大陆文化特征。
平潭海岛地名以山(18)、坪(30)、江(4)等大陆常见自然实体作通名,充分反映了岛民以大陆的眼光出发、以形象命名地名的思维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对大陆生活的留恋和回忆。其中以“山”为通名用于面积较大、海拔较高或岩石形态较为尖挺的岛礁。姜山岛面积0.4km²,最高点海拔68m;山洲岛因其顶部尖如山峰而得名;尖山仔礁因礁顶部尖似小山而得名。以“坪”为通名用于岩石表面平坦、光滑的岛礁,有坪洲岛、坪礁、大坪礁、坪砚礁(礁石顶平似砚)等。“江”作为聚落地名,有江楼村、南江村、江斗门、江尾村。
秦汉以前,仅有闽越族聚居于平潭。唐末五代,卢皓、林甲自河南光州随王审知入闽,隐居于平潭小练岛。“后二姓繁盛,遂为福州巨族”。入宋后,大、小练岛已“居民环集,商贾辐至,号小扬州”。元末民初,平潭人口已达1万余户,明初“海禁”,岛上人口被迫内迁,居民锐减。至清初,海坛收复,人口不过2千余人。清代在平潭驻扎的1600多名大陆军人融入当地人口。平潭现存160多个姓氏,以福清、长乐、莆田、泉州等临近地区迁入为主。移民多同姓聚族而居,因此多以宗族姓氏命名迁入地,命名方式为姓氏+厝,例如陈厝、杨厝、吴厝、韩厝、何厝和李厝等。姓氏地名主要分布于海坛主岛上有充裕淡水与耕地地区,以便族群定居。鱼汛来时出海至周边海域捕鱼,又将这些聚落名称赋予附近的岛礁、湾澳等。移民在岛屿上安顿下来后,受传统大陆农耕文化中安居乐业的心理影响,倾向于将“福、美、丰、旺、龙、凤”等美好词汇赋予各地理实体,例如瑞龙街道、凤美村、钱便澳(取赚钱容易之意)、旺宾村等。清廷在平潭驻扎时建造的兵营、军事工程也成为后来的聚落地名,例如城关镇的后围、右营两庄就是清代官兵后裔的居住地。
(四)海岛文化个性
海岛宗教信仰习俗是海岛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平潭宗教信仰多元,本土与外来宗教信仰融汇于此,相安无事。庙宇、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580多座(2010年底),信众11万人,占总人口的1/4,其中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300处居首,遍布大小渔村,多建造于明代至民国时期。其次是道教104座,基督教103座。信众以基督教和道教(各4万人)居首,天主教2万人,佛教1万人。但中西方宗教在平潭辖境具有明显的东西分异格局,靠近大陆一侧的平潭西部地区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集中分布区域,以西北角的苏澳镇为典型;濒临台湾海峡的东部地区以传统和民间宗教为主,以东南端的敖东镇为典型。平潭各岛孤悬海外,既较好地保存了闽越族“信鬼好巫”的古老传统,又因其独特的海岛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宗教氛围浓烈。
表现为:①把各种节气、信风与神鬼结合在一起,形成指导出海作业的民谚;②相信神鬼世界的存在,并体现在民俗活动中;③有打捞海面漂浮的神像甚至死尸立庙供奉的传统。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也镌刻于地名中。与海神妈祖有关的地名分布于滨海渔村及其附近岛礁,例如北厝镇娘宫村与娘宫码头,妈祖印礁等。以宗教建筑命名有瑞峰屿,因岛上曾建瑞峰寺(今圯)得名;凉亭屿,因古时岛上建有小庙宇,渔民常到此乘凉得名。与观音信仰有关的地名最多,且多分布于东部海域,有观音石、观音澳、观音礁、观音磹等,多因岛礁上的岩石形似观音菩萨像而得名,而观音澳原名澳前澳,因观音显圣救民众于危难的传说而更名。
虽然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海岛地名仍有一定的原生性。其一,普遍使用自创字和地方特色字。如“石户”字,表渔堰,出现19处,有石户澳、石户鼻礁、塔石户屿、破石户岛等;捕鱼用的网,方言称“纟孟”,有纟孟尾礁。“磹”字,出现53处,当地方言称临水或入水的巨石为磹,巨石遍布是平潭岛海蚀地貌的一大特征,成为当地居民命名地物的主要依据之一,例如圆磹屿、白磹、南磹礁等。“平潭”亦得名于县城五福庙的一块平坦巨石,之所以不称“平磹”则与海岛缺乏淡水,居民长年与飞沙走石为伴,用“潭”字作为地名更能表达出民众对水的渴望。其二,一些不常见的岛礁名称是按方言音书写,而不能单从字形去理解。例如“耳爿”“寻险”、“雷洲”、“南班”等方言音地名对应的是鲍鱼、蟳醃、螺洲、南扳。以方言用词命名的岛礁名称有140个,占总数的12.45%,充分体现了海岛地名的原生性。
四、
海岛地名与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与过程分析
从自然宏观角度看地球是由陆地与海洋两大系统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人类活动与陆地环境,与海洋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以及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而海岛作为连接大陆与海洋之间独特的、过渡的地理单元,海岛人地关系则是上述两种人地关系的相互交叉、渗透的部分。海岛地名是人类在海岛地理环境中因生产、生活需要而用语言、文字与符号附加于人类作用或未作用的海岛地理实体的一种文化产物。海岛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与海岛地名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海岛地理环境—人—地名系统(图1)。该系统由海岛的地理环境、人类社会和地名三大子系统及其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子系统间与要素间的状态、组合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影响系统的演进。
(一)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提升推动地名系统演进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生产、交往是地名产生的主观原因,地理环境为人类命名地名提供本底与依据,语言是地名产生的客观条件,区域环境差异是地名类型分化的动因。随着人类地域活动范围的拓展、实践对象深度与广度的提升、语言文化的丰富,地名数量、类型越来越多,命名依据越来越多样,反映的地理要素与现象越来越复杂。随着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显著,推动地名系统向复杂化、高级化演进。地名产生之初,也是人依附于、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人地关系低级阶段,表现为人类通过感官对地理实体形态、属性和位置的直观反映,方便人类在有限的认知和生产水平下辨认方位,区分地物、开展生活、生产活动等。由于海岛文化具有相对滞后性,由这种形象思维命名的地名所占比重普遍高于大陆地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命名依据越来越脱离地理实体特征,而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历史文化特征甚至人的主观意志。地名功能也由单纯的指示、辨认增加到政治教化、文化认同、名望提升等。尤其是20世纪中叶“人定胜天”的人地观盛行的“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大量催人奋进、征服自然的地名。这一时期平潭县所有聚落的通名被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例如,“立新生产队”、“先锋大队”等。为发展生产力盲目围海造田,垦荒山、开沙荒,采石造陆,砍伐防风林带,导致原本脆弱的海岛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屏障的破坏导致自然灾害带给人类更大的损失,人地关系恶化。
(二)地名与人地关系变化的时空错位
地名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地名的主观要求,也是地名作为超时空文化现象存在的基础。一方面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迁以反映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滞后于环境的变迁,甚至永恒,忠实地记录其指代区域早期的自然、人文风貌,成为现在人类追溯过往的“文化基因”。进入近现代后,平潭城镇发展迅速,有别于传统渔村长期稳定甚至原始的人地关系,城镇区域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力度更大,资源、空间利用强度更大,原有的景观急剧变迁,但城镇地域范围内仍零星存在着反映农(渔)村景观的地名。例如,保留了以“垄、墩、屿”作为通名的村名。垄指田地分界高起的埂子,有斗食垄村、东垄庄;“墩”指海滨晒盐的盐墩,有黄土墩村;“屿”原本为岛礁通名,有香炉屿、霞屿、矶屿等,表明这些区域是填海造陆或者海岸变迁的产物。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人地关系未发生显著改变,地名却频繁变动,原因多为人文要素更强势于自然要素作用于人类意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的作用下,更改原地名以表达命名者的主观意愿,因审美需要,实用方便,民俗禁忌,政治教化而更名的现象古今都时有发生。例如,将苦屿改为乐屿。
平潭乐屿村
(三)地名在人地关系中的能动作用
地名是人类认知和改造地理环境过程中的意识产物,意识具有能动作用。人地关系这一矛盾体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作为人类意识外显表现形式之一的地名不单单被动反映了人地关系的状态,也可用来调节或缓和人地关系的矛盾。但地名不直接作用于人地关系,而是通过地名蕴含的倡导和睦相处的人际观、清心寡欲的价值观、保护环境的人地观而对当地民众的人地认知起到潜移默化的社教作用,进而引导人类约束过激的改造自然的行为,寻求人地关系的和谐。在平潭县这类地名有和平村、民主村、下鹤村、秀礁村、砂美村等。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类在海洋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岛礁因形似神灵而被赋予神灵的称谓,人们行舟至此,心里会感觉神灵就在身边保佑自己,并从中得到慰藉和勇气去适应严酷的海洋自然环境,战胜困难艰险。
五、
结论与讨论
以福建平潭为例,采用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划分海岛地名类型,探究其命名内涵、特征及反映的人地关系。研究发现:①自然地理实体类多于人文地理实体类,其中方位、地形、方言、聚落亚类的比重最大,重名更名而产生的新地名次之。②海岛地名突出其形象性、通俗性、实用性、大陆渊源性与海岛个性,源于海岛独特的移民、宗教、方言、渔业生产与生活以及海岛自然、人文环境。③不同类型地名的分布因城乡、海陆、地形、区位而异。提出海岛“地理环境—人—地名系统”概念,阐述地名与人地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过程。地名产生之初是人类通过感官对地理实体的直接反映,地名通俗直观,实用性高;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显现,地名命名依据越来越脱离地理实体特征,而更多地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特征。地名与人地关系存在时空错位,既响应人地关系变化而变化也常滞后或超前于后者变化。地名对人地关系矛盾的调解具有一定能动作用。
对平潭诸岛大规模的开发仍在继续,加剧其自然环境的变迁速度,人在海岛人地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愈发显著,人地矛盾的程度与形式不同以往。通过地名上表现为海岛传统村落、岛礁、古街巷地名的消亡而大量涌现出迎合投资商主观意愿、欧美化倾向的、单调序列化的社区、地产、港口码头、街道等地名。岛屿开发过程中,如何通过对地名的合理规划,保护平潭传统文化,发挥传统地名在调解人地矛盾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六期
作者:纪小美 付业勤 程姗姗
图片来源:网络
选稿:常宏宇
编辑:黄海红
终校:耿曈
审订:刘聪
重庆政区重复地名研究
河南县市地名由来初探
常州地名词源探析
从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看闽台地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