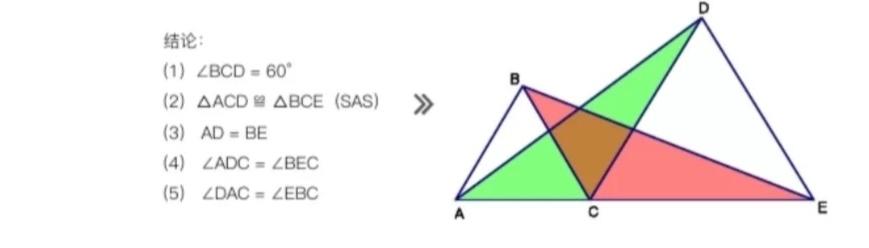母语教育的“死穴”究竟在哪里?(本文已经发表,丁帆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语文教育地位提高了吗?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语文教育地位提高了吗
母语教育的“死穴”究竟在哪里?(本文已经发表,丁帆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邓维策
《语文学习》发表了丁帆先生的文章《语文教育的“死穴”在哪里?》,他把板子打在教材和教师身上,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避开学科理论,就不可能触及“死穴”。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教学都需要理论支撑,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教材和教学两个环节出现的问题,根源在学科理论。理论界争论六十多年,学科对象尚不清楚,还没有建立合逻辑的学科知识体系,母语教学难以从经验走向理性。母语教育的病根在于理论研究者缺乏应有的逻辑训练和哲学素养,导致学科理论苍白,不能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
在某杂志的QQ群聊天,一位“语文”教授经常批评我太看重概念,他坚持认为,概念并非都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错误概念有很多。乍一听,这话似乎正确,但是,深入地思考,他的观点似是而非。观念有错误的,概念却一定正确。按照逻辑学对概念的定义,概念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换言之,只有把握到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才是概念,那么,凡称得上概念,就不能说是错误认识。从哲学上讲,概念是与对象相符合的认识,与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当然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知。这位“语文”教授的话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他的知识结构的缺陷,接受过一般的逻辑训练,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的教授在面对数百名的编辑、作者、读者时,是不会轻易犯知识性错误的,更不会固执地坚持错误。轻视逻辑,哲学素养不够深厚,这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
我们学科轻视逻辑、忽视逻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的逻辑瑕疵。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概念反映的是不同的事物,变换概念,事物及其关系随之而变。数学、物理、生物等保持其概念的稳定性,但是,我们的学科,在教授那里,就可以变为语言、言语、文化,或哲学,甚至于道德。在概念的关系上,有的教授能够说出男人与女人的概念是“人”,但是,在面对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时,不是按照逻辑选择“语言”,而是习惯性地选择了“语文”。几十年来,没有人用逻辑来考察“语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种概念,它们的属概念是语言,命名者不遵从逻辑,轻率地提出了一个不合逻辑的虚假概念。教授们接受“语文”这个虚假概念,提出观点时不惜违背逻辑。同一律要求,每一思想与其自身保持同一,保持着概念的确定性和一致性。违背这一逻辑规律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语文的规律’主要指向语言的功能即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的。” 对“语文”我们解释了数十年,是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看待的,而语言是一个具有确切含义的概念,“言语”在索绪尔那里也有明确的定义,“语文”、“语言”和“言语”是三个概念,论述“语文”,却马上转换到其他概念上,这是把有联系或者相似的不同概念当作相同的概念来使用,逻辑上称为“混淆概念”。混淆概念几乎是每个“语文”专家都犯过的逻辑错误。在概念的划分上,逻辑要求“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划分的子项之间应是互相排斥的”,有的教授把教材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四类,这种划分一个类型一个标准,四种类型的关系重叠、重合,严重违反了划分的原则。不服从逻辑,可以随意地提出理论主张,建立个人的理论体系。近三十年来,在学科对象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的研究专著超过一百部;各种教学流派层现叠出,乱花迷眼,大语文,真语文,本真语文,青春语文,绿色语文、生活语文、本色语文、智慧语文、生命语文、人格语文、心根语文、享受语文、感悟语文、生态语文,从逻辑上看,这绝对不是学科理论的繁荣,而是学科思想的混乱!
五年前,有位教授发表文章说,“语文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持这种观点的教授或博士,我记录下来的,至少有四位。名称问题早已经形成了一门成熟的学问,我们却仍在黑暗中摸索。1843年,穆勒出版了《逻辑体系》一书,经过弗雷格、克里普克、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发展,在名称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名称为分专名和通名,通名表达概念,既有内涵,也有外延,通名的内涵就是名称所指对象的属性,外延就是指具有这一特有属性的对象,通名的外延是由它的内涵决定的,凡是符合某个通名内涵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通名的外延。通名通过涵义描述对象的某些特性,从而确定名称的指称,不论它是单个的词或者是由若干个词组成的短语,都代表着某种事物,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事物就是这个名称的意义。学科名称是对学科的最深刻的抽象,是对学科本质的把握,数十年对“语文”涵义的争论,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看待的,如果不重要,为什么还要争论呢?应该说,“叫什么并不重要”的观点缺乏应有的名称知识的背景。
有一位教授用黑格尔的关于“中介”的哲学思想解释“语文”课程性质问题,他说:“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个方面,也只能在主体身上得到‘统一’。”把主体当“中介”,在黑格尔的两部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中都找不到,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辞典》对“中介”的解释,也没有这种说法。性质属于客观对象,主体是认识者,主体感觉到白、咸、立方,并不能说,看到白,主体就变成白的了,尝到咸,主体就变成咸的了,而是说,主体知觉到多样的性质统一于盐,从而知觉到盐的存在。同样,人们通过工具性与人文性来认识“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只能统一于学科对象。
对于母语教育的认识,很多方面借助哲学看得清清楚楚,完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课程标准把我们的学科规定为一门综合课程,很多学者解读课程标准,认为“综合性”是把几门学科合并起来组成的一门复合式课程,容纳了相近的学科的内容。也就是说,母语课程是杂凑的拼盘,由相近的学科堆积起来,而不是自组织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体系。学者们的解读,仿佛把几样东西摆放在一起,这就是综合。合并几门学科,这是外在的统一,从外表看,相近的几门学科集合起来了,这样的集合体是一盘散沙。他们完全忽视了同一性,综合是把具有同一性的东西统一起来,真正的综合、统一是以同一性为基础的综合、统一。综合的几门课程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个内在的同一性是综合、统一的标准和根据,把这几门课程纳入到一门课程中,而把其他的课程排斥在外,我们是按照这个根据进行选择的,这个根据像一条思想之线,把相近的学科贯穿在一起。这个思想之线,学科的根据恰恰被解读者忽视了。讲综合,必须找到“同一性”,否则,就不是综合,是拼凑,是凑合。
母语教育无论多么特殊,都不能否认其科学性。在我国,母语教育独立发展了一百多年,黎锦熙等人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使这门课程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然而,现在的理论研究却充斥着许多的非科学的东西,比较隐蔽的是“语文味”。“语文味”把生活中的感性经验直接当作理性认识,很能得到重视感性事物的人们的响应,但是,感性的东西无论多么生动,它都不是理论,理论必须是“灰色的”,它要走到感性事物的背后,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把捉到产生事物运动变化的始基。况且,哲学中,实体与偶性的原理已经告诉我们,“味”是依赖性的存在,实体虽然也需要“味”表现出来,但是,实体是“味”存在的基础,“味”离开了实体,就不可能存在,实体才是本源性的存在。“语文味”把实体与偶性混杂在一起,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方法上,也是背离科学的。
当然,“语文味”的非科学化是从内容的阐发及研究方法间接地体现出来的,更有学者公然提出“语文”课程存在着许多非科学性的因素,如非理性、非逻辑性、非线性、非系统性、混沌性、模糊性、无序性、 随机性、测不准性等。白内障患者想把白内障摘除掉,没有正常的人把眼睛弄昏浊。人们憎恶雾霾天气,不仅仅因为雾霾有毒,在感官上,灰蒙蒙带给人心理压力。清楚、清晰、明白,这近乎是人的本能的要求。母语教育追求的是正确理解和准确表达的语言能力,通过科学性的知识和科学性的教学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非理性、模糊性、无序性、随机性等非科学性的因素是母语学科的白内障和雾霾,是力求排除掉的。课程标准的陈述必须清晰,否则,母语教育更加混乱,口齿不清,说话含糊,思路紊乱,讲课比朦胧诗还朦胧,这样的教师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母语教师。从教学内容上来讲,许多诗歌表达含蓄,有的小说主题隐晦,教学不是让诗歌更加含蓄,不是让小说更加隐晦,而是要让学生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感情,把握主题。我们的母语理论够混乱了,非理性、非逻辑、模糊性、无序性等名词无论多么时尚,教授们还是放在一边为好。
逻辑是思维的科学,哲学是普遍的方法论,语言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要靠近这两个领域,建设母语教育的理论更应当依靠逻辑和哲学,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才可能整顿母语教育的乾坤。
批评一线教师的教授很多,像丁先生这样,“建议中学语文教师一定要打通对文史哲知识营养的全面吸收”,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但是,对教授们自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有鉴于此,笔者学舌丁帆先生,向教授们进一言:回归逻辑,加强哲学修养,真正地担当起教授的学术责任。
2013-10-12于星枫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