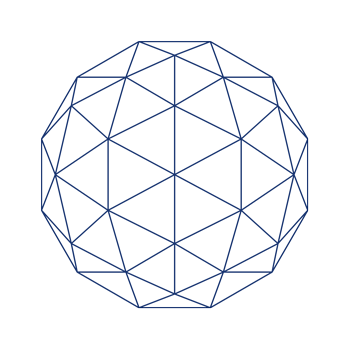陆俨少先生(1909—1993)
我认识陆俨少先生,应该是在1973年前后。那年,我的老师姚有信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我便常去画院问学,并到资料室去借阅图书。陆先生是资料室的管理员,地位远在承担创作任务的画家之下,等同闲杂,完全是“夹着尾巴做人”。但大多数画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说他画得不得了的好。虽然,对当时画院中的许多名家,我都慕名已久,但对陆先生,在这之前竟然完全不知道其人其艺!后来进一步了解到,直到1978年之前,除了江浙沪皖的个别小圈子,就是整个中国画坛,知道“陆俨少”这个名字的也非常少!在陆先生本人,当然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在旁观者,实在免不了“人生如此,天道宁论”之叹了。而陆先生的人生,还绝不止于“人不知”的寂寂无闻,更在于他的际遇多舛,跋前疐后,动辄得咎。在我认识的老一辈名家中,陆先生是生世最为困顿坎壈的一位;还有一位是后来认识的丁天缺。不过,讲到往来的关系,我于丁先生远不如于陆先生那样走得亲近。
虽然,“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苦难于艺术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正如钱锺书先生的分析:尽管“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但肯定“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诗可以怨》)。所以,当拨开阴霾,70岁左右的陆先生终于跳出苦海,迎来了灿烂的光明,几乎一夜之间,名声遍及全国艺苑,还从复兴路的蜗居搬进了延安路茂名路口一套宽敞的公寓,他欣然颜其新居曰“晚晴轩”。相较于他之前的斋名“骫骳楼”,两种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心情,判然若鲜花之于荆棘!不久之后,他的人事关系又正式调到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更使他春风得意,意气风发。每每回想起之前的艰难困苦,他总是心有余悸而又满怀感恩地表示:“老天有眼,终于给我熬过来了。今后再也不会过苦日子了……”但这样的好日子不过十来年,晚年的他又陷入到病痛的折磨之中,虽以其“扼住命运咽喉”的无比坚强,竟然也不得不“服输”了:“真是苦透苦透。”

陆俨少书赠本文作者扇面
陆先生的禀性是特立而狷介的。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导致了他在社会上对人事的疏离,从而在生活中不断地遭遇到挫折,而生活的挫折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特立狷介的性格并与命运作抗争。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绘画艺术,便是奇险、奇崛而又奇秀,从笔墨到景观再到意境。他以山水擅场,尤以画三峡、黄山、雁荡驰誉。三峡、黄山、雁荡成了他艺术成就的三大品牌,而他也成了三峡、黄山、雁荡的艺术代言。实在是因为这三处风景,与他的性格若合符契,达到神遇而迹化,简直可以说是山川即先生、先生即山川。
陆先生少年时从王同愈学经史诗文,从冯超然学绘画。冯在当时与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并称“三吴一冯”,皆以山水名世,出于正统派;冯兼工人物,出于吴门派。但陆先生在正统派方面下的工夫似乎并不大,尽管他后来给学生讲课时也提到过学习“四王”的好处,但冯超然生前对他的评价却是“一个不像老师的学生”。相比之下,他的同学郑慕康在嵩山草堂学人物仕女,就完全是冯超然的法嗣蕃衍,系无旁出。由此也可窥见陆先生不安分的奇崛性格。据他的自述,自己的绘画属于“科班出身”,即多从珂罗版画册上学习;后来虽也曾去南京参观故宫南移的画展,目睹了古代名家巨迹的原作,自称“贫儿暴富”,但都属于笔底丘壑、纸上烟云。至于从画册上、原作中,他究竟学的是哪几家?并没有说明。估计只要是他觉得好并适合于自己禀性的,没有他不虚心认真学习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生活才是艺术的活水源泉。日寇全面侵华后,在国恨家难的压迫下,陆先生携家避兵重庆,往还江陵,舟行三峡,云雨江波,鼓荡诡谲,奔腾盘郁,与其胸中磊落相激越,古人的笔墨与江山之助始相印证,一下子绽放了其险绝瑰丽的个性艺术境界!游历并描绘过三峡风光的古今画家并不在少数,但最能得其精采神韵的则推陆先生为第一人。我曾以三峡之文,郦道元《水经注》为第一;三峡之诗,李太白《早发白帝城》为第一;三峡之画,陆先生“峡江云水图”为第一。又剥元稹诗句称陆先生三峡云水之奇谲:“曾经三峡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陆先生欣然含笑以为可。这得之于峡江生活体验的独特的云水画法,从此便奠定了“陆家山水”“无常形而有常理”的根本,并由三峡而推广到其他一切风景的描写。陆先生的人生是险绝而后生,三峡的云水也是险绝而后生,则摩荡激发而为先生险绝而后生的艺术风格,宜矣!所以,1980年代初,当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卷仿真本传到大陆,人们纷纷欢喜赞叹时,陆先生把它展开到三峡一段,不无自负地说:“等我有空了,也要画一卷《长江万里图》,定当不让大千专美!”
至于黄山、雁荡的游历和描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黄山的奇崛,峰石松云,变幻灭没,不可思议;雁荡的奇秀,悬崖龙湫,层隐迭现,崔嵬难穷,与陆先生奇崛的性格、灵秀的禀赋也是颇为相合的,所以,与三峡一起成为最入于其画风的三大标志性景观,也就不足为怪。只是,三峡画以陆先生为独擅,黄山画、雁荡画却不以陆先生为专美,而是分别与刘海粟的黄山、潘天寿的雁荡为并美。刘海粟美在狂,潘天寿美在霸,陆先生则美在奇——于三峡则奇于险、于黄山则奇于崛,于雁荡则奇于秀。

杜甫诗意图/陆俨少
不过,人们对陆先生艺术的评价,主要的并不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三峡、黄山、雁荡的景观,而更在他戛戛独造的笔墨——“三百年无此笔墨”、“三百年来笔墨第一”,这是专业圈内对他众口一辞的称誉,他也当仁不让。他的笔墨特色也是奇险、奇崛、奇秀,一方面,他以如此的笔墨塑造了如此的景观、宣泄了如此的心境;另一方面,也正是如此的景观、如此的心境,造就了他如此的笔墨。但笔墨的创造除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还有一个“上法古人”,则陆先生笔墨的传统渊源又其来何自呢?由于陆先生对传统的学习如吴道子的实地写生,是“臣无摹本,并记在心”的,所以,人们只能揣测。一开始,不少人认为是石涛。但陆先生自己却不承认,并毫不谦虚地说:“石涛早已不在我的话下,董其昌的笔精墨妙才是我所难以企及的。”人们又认为他的渊源不是石涛而是董其昌。但问题是,陆先生这样说,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没有学过石涛而是学了董其昌的意思啊!从他的作品来看,屈折盘旋、粗细长短、轻重快慢、枯湿浓淡、疏密聚散的笔墨运施,点、线、面的随物赋形、随意生发,委婉如行云流水,刚健如斩钉截铁,嵚崎磊落,变态无穷,于痛快淋漓中内涵蕴藉沉着,实在是更近于石涛而有别于董其昌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陆先生在《山水画刍议》的第一条中便以石涛为“开篇”:
例如有人说:“石涛不好学,要学出毛病来。”我的看法,有一种石涛极马虎草率的作品,学了好处不多,反而要中他的病,传染到自己的身上来。但他也有一些极精到的本子,里面是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何尝不可学?要看出他的好处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石涛的好处能在四王的仿古画法笼罩着整个画坛的情况下,不随波逐流,能自出新意。尤其他的小品画,多有出奇取巧之处,但在大幅,章法多有牵强违背情理的地方。他自己说“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其实他大幅章法很窘,未能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用笔生拙奇秀,是他所长,信笔不经意病笔太多,是其所短。设色有出新处,用笔用墨变化很多,也是他的长处。知所短长,则何尝不可学。
这里说“石涛不好学”的“有人”,或许是民国时上海画坛的什么人,如吴湖帆便讲过:“后学风靡从之(石涛),不复可问矣!”这个“不好学”并不是“不可学”,而是“很难学”的意思。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石涛被公认为传统中最值得继承发扬的精华之一,似乎就没人再讲“石涛不好学”了;有之,则应该正是陆先生本人。而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也正因为他在学石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深知其中的甘苦。由于走的是“科班”之路,所以,他当初的学习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在,他学出来了,走过来了,就可以把“石涛很难学”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公之于众尤其是后学。包括从不讳言由石涛起家的张大千,也苦口婆心地劝诫过后学:“石涛……那种纵横态度实在赶不上,但是我们不可以去学。画理严明,应该推崇元朝李息斋算第一人,从他入门,一定是正宗大路。”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再看这长长一大段的评点,具体而又深刻,如果不是认真学过石涛并有切实心得的人,又怎么讲得出来呢?我们看“刍议”中讲到的古人不少,但没有一个比石涛讲得更透彻的!所以,这段话不仅不足以证明陆先生的传统渊源没有把石涛作为学习对象,反而足以证明石涛是他“第一口奶”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
进而,我们再来看其中讲到石涛的优点和长处,诸如“不随波逐流,能自出新意”,“小品画,多有出奇取巧之处”,“用笔生拙奇秀”、“设色有出新处,用笔用墨变化很多”等等,无一不正是陆先生自己的优点!而所批评的缺点和短处,诸如“极马虎草率”,“大幅,章法多有牵强违背情理的地方”,“大言欺人”,“大幅章法很窘,未能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信笔不经意病笔太多”等等,又无一不是陆先生在自己的画中把石涛的不足成功地克服了的方面。当然,有些方面克服得还不够彻底,尤其是大幅的章法。由于陆先生的创作,大多以一支加健山水笔管领始终、统摄全局,所以,凡四尺整张以内的“大幅”,他可以成功地做到“左右逢源”,而超出四尺整张的“大幅”,仍不免“有牵强违背情理的地方”。

杜甫诗意图/陆俨少
总之,结合陆先生的创作,这一段对石涛的评点,实在正是他学习石涛心得体会的夫子自道。至于他之所以自豪地认为石涛已经“不在我的话下”,显然也正是因为他在学到了石涛长处的同时,又成功地克服了他的不足,避免了“中他的病”。
那么,他又是如何避免“中他的病”的呢?这就与他对董其昌的认识有关。以我之见,陆先生于古人,学过石涛,学过唐寅,学过王蒙,学过郭熙……但要讲他学过董其昌,我认为应该是在学石涛之后,而且主要是精神上的学习,而不是形迹上的学习。石涛的笔墨,从形迹到精神都是嵚崎磊落的,董其昌的笔墨,从形迹到精神都是平淡天真的。而陆先生的笔墨,则在嵚崎磊落、强烈冲动的形迹中,内蕴了平淡天真、闲适恬静的精神。从这一点而论,至少,陆先生的笔墨境界已经高出于石涛之上,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不在话下”之说,绝非大言欺人。
钱锺书先生曾例举过两个文学史上的常见现象:无所成就的后人,往往要“向古代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以“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尽管他事实上与这个传统完全无关(《中国诗与中国画》);而有所成就的后人,明明是学的这个传统,却“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宋诗选注》)。在美术史上,后一种现象的典型便是石涛。石涛由董其昌而来,董其昌在画史上最大的影响则是“南北宗”论。石涛却说:“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把与董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则陆先生学石涛,和合以董其昌,虽其所言寓意于委曲而明眼人自识,则其开宗立派之功,较之于石涛,不啻青出于蓝,是尤其值得我们尊敬的。
20世纪后半叶的山水画坛,李可染和陆先生是众所公认的两座高峰,世称“南陆北李”。我们看李先生的画,无论境界、景观还是笔墨,都是庄严雄伟的,敦厚凝重如里程碑,安忍不动,风雨如磐,甚至连水也是凝固的、静止的;而陆先生的画,无论境界、景观还是笔墨,又都是险绝奇崛的,灵异诡谲如冠云峰,蹈光揖影,随意生发,甚至连山也是盘郁的、飞动的。这不仅是自古以来北雄南秀的水土使然,更与二人的身世遭际密切相关。李先生的一生相对安定平和,而陆先生的半世极尽颠沛磨劫。人生即艺术,艺品即人品,有以哉!每读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总觉得,这不正是对陆先生的人生和艺术最恰切的写照吗?
作者:徐建融编辑:吴东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