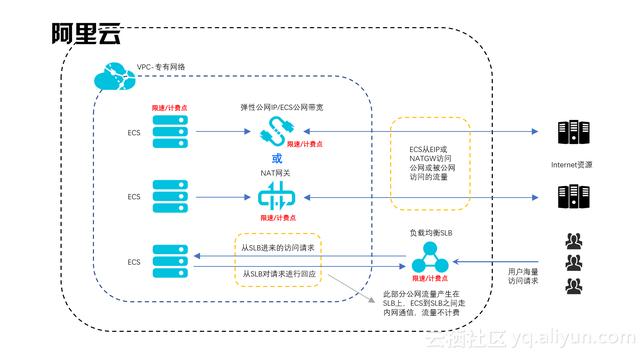光明

黑暗与光明
有人活在黑暗中,可能用黑色的眸子寻找光明
我活在光明里,却用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暗
你说那话的时候,有一缕微笑在唇角蔓延
像阳光下一朵慢慢绽放的金盏菊
噢,痛苦与欢乐,转换
如此地简单

零零零壹
那天,风和日丽,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驱散了一冬的阴霾
初见阿玦在那年的三月初。那天监狱组织开展了大型的法律与心理的咨询活动。监管区的坝子里,一溜儿的长桌摆放得整整齐齐,律师和心理咨询师依次就坐。那天,风和日丽,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驱散了一冬的阴霾。
在繁忙的咨询间隙里,我抬头望向齐齐整整坐在小凳子上的服刑人员,就只见一个“小伙儿”坐在中间,“他”东张西望地四处打量,目光来回地在老师们的脸上巡梭。这时,一个年岁很大的女犯缓慢地向我走来,刚站在空置的座位前,就见“他”像猛然下定了决心似的,几个健步从人群中蹿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坐在了空位上。年老的女犯悻悻地瞪了“他”几眼,转身走向了其他的老师。
阿玦就这样的出现在了我面前。

零零零贰
她卷起衣袖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还未及开口,眼泪就决堤而下,泣不成声
阿玦是个男性化的年轻女子,就像我最初的印象般,如果把那时的她放在人群中,所有的人都会把她当成男性。那天,阿玦向我提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说话时,她的声音低沉黯哑,也如男性一般。
我问她:为什么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阿玦说自己心里总像有一团怒气在燃烧,总想发火、想跟人打架,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控制住自己不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经常烦躁不安等等。说着说着,我猛然问道:你自残吗?她闻言呆住了,直愣愣地看了我一小会儿,才点头,旋即卷起衣袖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还未及开口,眼泪就决堤而下,泣不成声。

零零零叁
“我曾带人砸了我爸爸的家,你怎么看这事?”
再见到阿玦时,已是四月中旬。那次,刚一落坐,她就语出劲爆:“我混黑社会的,曾带人砸了我爸爸的家,你怎么看这事?”说完,紧紧地盯着我的脸,不错过我的一丝表情。
联想起阿玦所说的没法克制的愤怒,我瞬间明白了阿玦的情绪的来源,面对她的试探,微笑着说:“你砸爸爸的家,必然有你的理由,至于对错的评判,不是咨询师该做的事。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砸爸爸的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用砸的方式泄愤?”
“说来话长。”阿玦长长地叹了口气,收回目光看着别处,她说:“我不止一次地带人砸过我爸爸家,每次砸完了都要在墙上留下名字,好让他知道是我砸的;我在外面也看过心理医生,但都是狗屁,一听说我是混黑社会的,就如临大敌,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你倒好,身为监狱警察里面的心理咨询师,本该对这些最为反感的,却没有任何吃惊或厌恶。”说完,她转回目光凝视着我:“我想这次自己找对了人。”
“你都说我是监狱警察里面的心理咨询师了,面对的都是犯下各种罪行的人,再稀奇的事都见过了,还有什么值得吃惊的?!”我笑着说。
“这倒也是。”阿玦笑了起来,五官柔和下来,有一两分女孩子的模样。

零零零肆
“就这样做到的。”阿玦站起来龙行虎步地在咨询室走了一圈
“不过,我还是有吃惊的。”我接着说:“你是怎么做到把自己变得如此男性化的?从言行举止到气质,甚至到声音,无论从哪方面看,你都是一个男人。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在想女子监狱什么时候‘混’进了一个男犯?”
“我从9岁就开始当‘假小子’了,过去那么多年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女的,也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女的。刚被捕时,我走进的是男号。”阿玦露出回忆的表情开始叙述:“没有任何人质疑,要不是小姨探视,告诉看守所的警察我是女的,估计他们会把我当成男的判刑,再送到男子监狱服刑。”说着,她笑了起来。
“怎么可能?”我笑了。
“没有不可能!我还记得那天,小姨为了证明我是女性,还出示了我的身份证,他们才半信半疑,还让两名女警察验明正身,这才把我换去了女号。”说着,她想起那天的事,笑不可抑。
“你是怎么做到让所有人都产生了误会?”我越发不解。
“就这样做到的。”阿玦站起来龙行虎步地在咨询室走了一圈。是啊,这时候的她压根就不是女人。在我的恍惚中,阿玦坐回了浅黄色的沙发,她看着我说:“我决定了,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听。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想找一个人好好地讲讲自己的事情。”

零零零伍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却迷茫着,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阿玦的故事由此在我的眼前混乱地展开。
说实话,即使阿玦的叙述很主动,但她的咨询做得并不轻松。最初,阿玦滔滔不绝地讲述,有无数想说的话堆积在她的胸口,令她急切地需要表达;也有无数的记忆片段在她的叙述中来回地穿插,情绪、情景乱哄哄地涌来。初时的阿玦就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我在她的混乱且无序的叙述中头昏脑涨地聆听着,感觉自己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被来访者牵掣,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终于,在第六次咨询时,我问阿玦:“该讲的,你都讲得差不多了,对吧?”阿玦点点头。“那么,现在我可以提问了吧?”阿玦又点头表示可以。
我看着阿玦说:“我用了五次的咨询时间来聆听你的故事,每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想你需要表达的内容都在里面了。那么,从此刻开始,请你跟随我的引导,可以做到吗?”
阿玦点头,却又迷惑不解地看着我。我告诉阿玦,她的叙述很混乱,情绪也很混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不利于我们看清事物的真相,所以理顺情绪与感受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并找到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却迷茫着,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并且,在所发生的事物面前,我们也是无助的,有种命运被裹挟着,迫不得已继续向前的感觉。在这些事物,这样的感受面前,我一直觉得心理咨询师所做的事就是:拨开情绪的迷雾,用一根金线,把所有散落在记忆草丛里的零碎故事串联起来,还原整体故事的本来面目。
阿玦的故事,就始于那一刻,从处理与母亲的分离开始,我们慢慢地还原了她的人生……

零零零柒
阿玦也是如此,希望在家庭中替补缺位的父亲照顾病弱的母亲
阿玦出生于一个很不错的家庭,母亲是个大型国企的厂长,父亲是本厂的供销人员,家庭条件优渥。阿玦小时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留着长长的头发。那时,母亲很爱阿玦,也爱打扮阿玦,她也曾非常喜欢穿裙装。可一切都在阿玦九岁那年改变了。
从阿玦朦朦胧胧懂事开始,她就觉察到父母的关系不太好,爸爸经常不回家,回家也是跟妈妈吵架。时常地,夫妻俩大吵之后,爸爸摔门而去,妈妈在家独自饮泣。那时,阿玦的母亲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住院,小小的阿玦照顾着母亲,感觉很无助。
九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母亲忽然发病,晕倒在地。阿玦吓坏了,哭着喊着,用尽力气想把妈妈扶起来,移到床上。可是幼小的她,如何能搀扶起昏倒的成年人?阿玦没有办法,只能哭着敲响了隔壁人家的门。在隔壁叔叔的帮助下,阿玦把妈妈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阿玦说:“母亲入院的第二天,我就去剪了头发,换下裙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
阿玦从那之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男孩子。我们追寻着阿玦幼年的心路历程,她说看着妈妈昏倒在地,想把她扶起来,可是无论如何都扶不起来,隔壁叔叔一来就轻轻松松地把妈妈扶到沙发上,好羡慕他的有力。我问阿玦为什么没有想过找父亲?她说以前妈妈生病时找过,也拦过爸爸的自行车,求他去看妈妈,可那男人太无情了,说什么都不肯回去看看,我恨他!说这话时,阿玦的眼里露出仇恨的光。
“妈妈太可怜了,我要照顾她。然而,我只有变成强有力的男人,才能照顾好生病的妈妈”。这是阿玦心里的想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补位现象,当家庭出了问题,孩子出于对家庭的忠诚,对弱势一方的爱,会无意识地进行替补。阿玦也是如此,希望在家庭中替补缺位的父亲照顾病弱的母亲。

零零零捌
阿玦认为母亲的死跟父亲脱不了关系,要不是父亲经常在外沾花惹草,母亲也不至于气出病来,更不至于早早地就去世了。她说她恨,好恨!
十一岁的时候,妈妈把阿玦送到了北京,交给远在北京的舅舅照顾。妈妈告诉阿玦,北京的教学条件好,让她在北京好好地上学。阿玦很担心母亲,但母亲很坚决,一定要阿玦在北京念书,以便将来考个好大学。
阿玦在北京生活了一年,舅妈偏心自己的儿子,话里话外地嫌弃阿玦,总觉得阿玦是个累赘。阿玦不解,问舅舅,舅舅不说;问母亲,母亲也只是让她忍着,从小在母亲百般呵护下长大的阿玦渐渐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终于有一天,妈妈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阿玦慌了,找舅舅拿钱要回四川,舅舅不给,反而把阿玦身上的零花钱全收走了。这下,阿玦更加肯定妈妈和舅舅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阿玦偷偷地离开了舅舅的家,到火车站混进了站台,又偷爬上了火车,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川的路。她说那趟旅途走了一个多月,无数次地被从火车上撵下,又无数次地偷爬火车,也乞讨过,哀求过,捡过垃圾箱的食品果腹。凭着过人的毅力与方向感,十二岁的阿玦终于像乞丐般地回到了四川,她飞一般地向家里跑去。
家门还是那个家门,阿玦敲着、喊着,希望妈妈打开房门接纳自己。然而,开门的却是陌生人。阿玦蒙了,以为自己走错了楼层,反复地上下查看。这时,隔壁的人家开了门,将阿玦接纳了进去。邻居告诉阿玦,她妈妈死了,爸爸把房子卖了,搬走了。
拿着邻居给的父亲的新地址,阿玦明白了母亲送自己到北京的用意,也明白了舅妈话里话外的嫌弃。想必那时,妈妈已明白自己时日无多,想把孩子托付给舅舅照顾。回忆中,阿玦恨恨地说:“他们拿了我妈一大笔钱,却不肯好好照顾,让我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这样的亲人不要也罢。”
有了新地址的阿玦流着眼泪找到了父亲的新家,她的头脑里回响邻人吃惊的话:“你妈死了,你不知道吗?你爸爸把房子卖了,搬家了,也没给你新地址吗?”在这样的刺激下,阿玦敲开了父亲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打扮得很妖娆。母亲刚去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找了新欢,阿玦的情绪崩溃了,她歇斯底里地跟那女子闹了起来,父亲闻声从里屋出来了,看到阿玦很是吃惊,不分青红皂白地护住了那个女子,扬手给了阿玦一记耳光,情绪失控的阿玦第一次动手砸了父亲的家。她说此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带人砸他的家,他搬一次,我找一次,找到就砸。
阿玦认为母亲的死跟父亲脱不了关系,要不是父亲经常在外沾花惹草,母亲也不至于气出病来,更不至于早早地就去世了。她说她恨,好恨!

零零零玖
从此以后,阿玦就彻底男性化了。她像男人一样说话、做事,也像男人一样地抽烟喝酒、打架斗殴。
从此以后,阿玦就开始浪迹社会,再也没有投奔过任何亲人。她说:“在社会上,我认了一个师傅,师傅对我很好。他手下有好几个兄弟,号称‘七虎’,我是‘七虎’之一。那时,我们经常为抢‘地盘’打架斗殴,每次打架我都冲到最前面,打斗也是最不要命的,根本不管自己会不会受伤。”
“师傅不知道你是女的吗?”我问。
“不知道,就连同进同出的‘七虎’也不知道,只有师娘知道。”阿玦说。
“师娘怎么会知道呢?”我又问。
“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要来‘大姨妈’,师娘就知道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脸懵的我在师娘的帮助下手忙脚乱的处理着,吃上了停经药品。”
从此以后,阿玦就彻底男性化了。她像男人一样说话、做事,也像男人一样地抽烟喝酒、打架斗殴……
在细细的回忆中,我敏感地觉察到了阿玦内心隐藏着的孤独。我问阿玦为什么会有孤独感?阿玦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我爸能好好地对我妈,相信我们一家一定过得还赖,我也不至于犯罪。我妈那人嘴硬心软,心底其实一直都期盼我爸能回来,虽然她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

零零壹零
我们的生命是传承的,有些语言不需要叙述就能在血脉之中传递,且不受时空的阻隔
是时候处理阿玦的家庭问题了。我移来一张椅子,让阿玦想象母亲坐在那里的形象。阿玦闭上眼睛,开始进入想象,她的面容虔诚且期待。
当阿玦一字一句地向母亲倾诉着思念与懊悔时,晶莹剔透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从她的眼眶滚落。十四年了,这些话深埋在心底,从未有机会说出来,她哭着说着,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我想你!我好恨自己去了北京,连你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也好恨爸爸,他只会气你,却没能照顾好你!”
阿玦的情绪问题到此时完全呈现出来了,她恨母亲离世得太早,恨父亲的绝情寡义,也恨自己听从安排,丧失了与母亲最后的相聚时间,然而,她更恨与深爱的母亲天人永隔的事实。这是她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然而,现实无法逆转,唯有的只能是接受。阿玦的情绪平复下去后,我让阿玦坐在母亲的位置上,去接受母亲最后的遗言,以弥补未能见最后一面的遗憾。阿玦目露惶惑,这能感受得到?
能!我们的生命是传承的,有些语言不需要叙述就能在血脉之中传递,且不受时空的阻隔。阿玦怀疑地问:“你不会诱导或者暗示我,让我以为它是吧?”
我摊摊手:“我除了引导你进入状态,其他的一句话都不说,这你该信了吧?”
“好!那我就试试。”阿玦同意了。
闭目坐在母亲所在的椅子上,阿玦慢慢地把自己与母亲融为一体,重新回到生命共生的状态。然后,“母亲”睁开了眼,看着面前痛哭失声的“孩子”。“她”慢慢地开了口,轻轻地安慰着孩子,缓缓地诉说着自己的担心与牵挂,说着那些不舍与犹豫,也说着自己内心的期待与盼望。当她借着阿玦的嘴说出“不要记恨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了。”属于阿玦的眼泪瞬间夺目而出。
“好神奇啊,我好像真的听到了妈妈的话!”结束后,阿玦兴奋地说。是啊,十四年了,能再次与早亡的母亲隔着时空对话,这种感受真的很让人兴奋。 我很理解阿玦的感受。

零零壹壹
一次次地分享,一次次地巩固,阿玦的状态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明媚如窗外的阳光。
接下来的咨询也就顺理成章了,阿玦很快地就意识到自己所有男性化的行为方式和男性化的状态,都跟母亲有关,出于对病弱母亲的深爱与自己的遗憾!并且,父母关系不好,跟二人地位悬殊、父亲滋生自卑有关,跟他们的相处方式有关。阿玦回忆起了很早以前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的场景。这些记忆原本都被阿玦屏蔽了。
阿玦开始释然,一直燃烧在心底的怒火慢慢地熄灭了。随着阿玦状态的改善,她略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混账。老实地告诉你,我们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的,我伙同‘七虎’做了许多坑蒙拐骗和入室抢劫的事情。以前不以为然,认为生活就是弱肉强食,可现在才明白这种看法有多离谱,多荒唐!”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阿玦羞涩地笑了:“老师,我昨晚取下了紧身内衣,十几年了……我一直讨厌自己是个女人。如今感觉不一样了,我觉得做女人也没什么不好。”
“老师,我爸昨天来接见了,我第一次跟他好好说话了,以前不是怒目而视就是冷嘲热讽。你知道我爸爸是啥表情吗?他哭了,哭得鼻涕都流出来了,他也顾不得擦,就那么看着我。我这才发现他其实也老了,又被其他女人骗得好惨,也怪可怜的。”
“老师,昨晚我帮同改写信了,她们都夸我的字写得好好哦。我妈当年可是给我报过书法班的,我也是好好练过一阵子的。”
“老师……”
“老师……”
一次次地分享,一次次地巩固,阿玦的状态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明媚如窗外的阳光。她说自从意识到跟母亲的关系状态后,渐渐地理解了母亲的状态对自己的影响,更是在明白了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母女间的牵绊后,就渐渐地感觉当“男人”这么多年其实也很累,得拼命地伪装,就怕被人发现,入狱后不用装了,但却已经养成了习惯。眼下,她终于能从这个习惯中解脱,重新感受到自由,也能够慢慢融入生活了好几年的环境当中。

零零壹贰
关于过去,曾经以为生活是地狱,我正坐在地狱的火山口,如今才发现黑暗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心灵
咨询结束后,在阿玦刑满释放前,我们又见了一面,这次不是咨询,而是道别。当她缓步走进咨询室时,宽大的囚服套在身上,然而,属于年轻女性的袅娜依旧在浅蓝色的囚服中若隐若现。她的头发长了,顺滑地贴在耳畔。就在那淡黄色的沙发上,她轻松地坐下,喜悦地说明天要走了,爸爸要来接自己。旋即又有些扭捏地告诉我,父亲希望她穿着裙子出去,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她轻叹了一声,说十几年未穿了,很不习惯。沉默了一小会儿,她有些艰难地开口说,以后会不会再穿裙子也不知道,可至少会打扮的中性点,不会再让人产生性别的错位。说着,她面带羞愧地看着我,低低地问:“让老师您失望了吧?”神情中有种怯怯的味道。
我含笑地望着她,告诉她怎么选择穿着是每个人的自由,穿裙子也好,中性服装也罢,都只是一种装束,只要她内心确定了自己是什么人就好。她高兴起来,眉眼舒展了:“确定了,我是女孩子!”
兴奋的阿玦絮絮叨叨地道出生活计划与人生规划后,忽然变得很严肃。她沉凝地说道:“我发现身边的人,有的人生活得很苦,但能在痛苦中追寻快乐;而相比她们来说,我算是幸福的,可我却死死地盯着生活中黑暗的地方。关于过去,曾经以为生活是地狱,我正坐在地狱的火山口,如今才发现黑暗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心灵。”
梅子老师

梅子老师(王竹梅)
成都女子监狱心理健康中心资深心理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