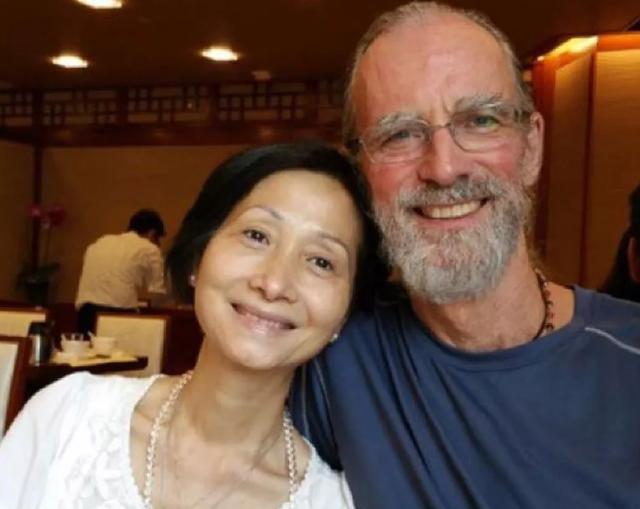对元祐元年的反变法派来说,苏轼的到来至关重要。
一方面,苏轼是昔日被变法派重点打击报复的对象之一。王安石对苏轼的厌恶程度曾经已经达到了“恨怒苏轼,欲害之”的地步,眼下大张旗鼓地起复苏轼,本身就是反变法派卷土重来的一种宣告;而另一方面,反变法派也确实需要苏轼这位“以文学显重于天下”的文学大家来做他们的“文胆”。
那么朝中缺这么一位文胆吗?你别说,还真缺。变法派的干将章惇曾说过:“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原来当年王安石变法,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科举改革,罢掉了诗赋、明经等科目,专以经义策论取士。这么搞了十几年,大家终于发现不对劲了——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新人,务实倒是务实得很,可是写出来的东西未免也太难看一些了吧?
所以苏轼很快就被安排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中书舍人,负责根据“词头”草拟诰命。

所谓词头,乃是一份提纲性文件。按照宋代制度,朝廷在形成正式命令之前,宰相机构会将命令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要求形成“词头”,然后送到中书舍人的手里。中书舍人便要根据这份提纲舞动自己的如椽大笔,形成正式诰命,很显然,中书舍人如何行文,是能够直接影响朝廷诰命价值取向的。
苏轼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待。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岩叟上疏弹劾狄谘、刘定,指出这两个人“上挟奸党,下附庸材”,导致治安恶化,必须严惩——这两人乃是当年王安石进行《保甲法》改革时安排在河北的具体政策执行人,曾于元丰四年带着四百八十位大保长进京汇报工作。苏轼大笔一挥,在 《狄谘刘定各降一官》中为他们的行为彻底定了性,说他们“烦酷之声,溢于朕听,公肆其下,曲法受赇,收聚毫末,与农圃争利,使民无所致其忿,至欲贼杀官吏”,巧妙地将矛盾集中到了“与农圃争利”五个字上面,借这两个人贬官的机会从官方角度对保甲法进行了否定。
而同年四月四日,反变法的范纯仁加官晋爵时,他又是妙笔如花,巧妙地把事情拐到了仁宗身上,说:“朕览观仁祖之遗迹,永怀庆历之元臣。强谏不忘,喜臧孙之有后;戎公是似,命召虎以来宣。”——而仁宗时的特色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不折腾”了。
一道道诰命从这位中书舍人的手上被起草出来,进而流传天下,而在残酷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变法派则彻底倒了霉,不光被贬官外放,还要在朝廷诰命中被狠狠地羞辱一番。比如吕惠卿被贬外放的时候,苏轼是这样为他定性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 ——这份文章写成之后很快便被天下传颂,而吕惠卿的名声也算是彻底臭了大街。
就这样,在苏轼的助推之下,司马光等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运动,朝中的变法派接二连三地受到了打击,一条条新法不断被废掉,而每当有人质疑哲宗皇帝这么做是“以子改父”的时候,苏轼等人就会把太皇太后搬出来——您瞧好喽,我们这可不是“以子改父,我们这是“以母改子”,名正言顺!
由于这段时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而依照惯例,中书舍人承受词头后必须当日起草成文,因此苏轼几乎成了反变法派里工作量最“饱满”的那个人,甚至跟友人抱怨到“为词头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暇”。
当然,中书舍人的工作不仅仅包括“草拟”诰命,实际上,假如苏轼认为上级下发的“词头”存在问题时,他甚至可以拒绝草拟正式命令,封还词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整个大宋权力体系的一道“安全阀”。
只不过司马光他们肯定想不到,这道“安全阀”,有时候是六亲不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