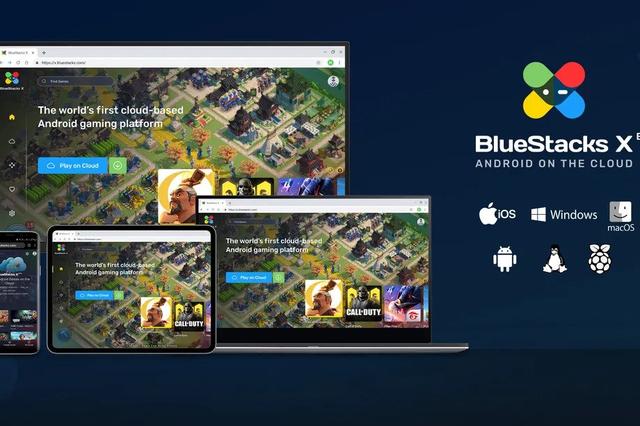今天讲点禁忌的话题,都是亲身经历。
禁忌,往往意味着诱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你来到豫东地区的一所小学,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五六岁的小男孩三五成群,发疯似地狂奔,追逐一群同龄的小女孩。张牙舞爪,惊声尖叫。杀猪般的嚎叫中,小男孩一把扯住小女孩的领口。抗日剧中鬼子进村也不过如此。
你若细听,操场角落里还有冲天的呐喊——打倒四人帮!解放台湾!扒了他的皮!
简直恍然隔世,头皮发麻。

1990年代,很多中国小学课间都是这种混乱又开心的游戏情形。
如果你在这所学校念过书,就不会太奇怪。这是小学生在做游戏,叫「老虎抓仙女」。
男孩是老虎,女孩是仙女,相向而立,一喊开始,仙女四散逃窜,老虎咆哮着扑向目标。地上有个画好的圈,抓到一个,就撂在圈里,再抓另一个。捕获仙女最多的老虎赢得王者的桂冠。
这游戏简单粗暴,触犯性别禁忌,触动悄然滋长的本能的快乐。
冲天的呐喊则来自其他游戏。「打倒四人帮」是跳皮筋的一种玩法,跳至最后一步,踩着皮筋的节奏,逐字喊出,打倒四人帮,就过了一关。

1990年代跳皮筋的小孩。
「解放台湾」则是来自一种神秘且难以言说的游戏——「一米二米三」。说它之前,先说「杠精杯」,豫东方言音译,多年来设法考证,也没弄明白这三个字的实际意思。
你一定知道猜拳,石头剪子布,或剪子包袱锤。「杠精杯」就是一种猜拳,不过是用脚猜。双脚并拢站立,是石头,前后岔步,是剪子,左右岔开,就是布。两人面对面蹦达,以同样的声调和节奏喊“杠——精——杯!”,第二个字要拉长尾音,高高吊起个升调,像念古诗一样喊出平仄。两双脚同时落地,胜负一目了然。我认为这可以叫「猜脚」。

猜脚。
「猜脚」比「猜拳」更讲究功夫。「猜拳」靠心思,瞬间定胜负,一旦出招,容不得变幻。「猜脚」的招式是透明的,腾空到落地,出的是明招,鲁钝实诚者就容易被看穿心思,灵活狡黠者则能会虚晃假动作。我读小学时,遇见过一个轻功好的,弹起后比常人高出二尺,脚上可石头剪子布连晃一遍,双脚互踢,腾起滚滚尘烟,堪称游戏界的无影脚。
当然,过分沉迷技巧,难免在迷糊对手的同时也迷惑了自己,高手绊倒自己的惨案我也见过。
一个人和一群人玩「杠精杯」,就是「一米二米三」,其基本形式是打擂。做庄的站一边,打擂的在对面排一纵队,依次玩「猜脚」,猜一次喊一句口号——一米二米三,三加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拾个冰糕棍儿,咱俩换换位儿。
六句口号喊完,打擂的如果没有一次能做出和庄家一样的步型,就是输了,换下一个上。若是做出了和庄家一样的步型,就赢了,成了新庄家,接受挑战。也就是说,石头剪子布的相克原则在此无效。
山东小孩也玩「一米二米三」,据说其他地区也有,但口诀不大相同。
有地方这么念:一米二米三,三乘以三,三面小红旗,走向台湾,台湾有座山,名叫阿里山,不当皇帝就当官。

建国后,我国非常注重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宣传,“一米二米三”这样的童谣、海报都是典型的宣传方式。
不提「解放」,却说「走向」,大概是鸽派,而非鹰派。
还有的版本里,「解放」竟然失败了——
一米二米三,三乘三,骑红马,过江南。三面红旗,解放台湾。台湾没过去,把你打下去。
无论哪种口诀,都提到「三面红旗」,可以判断这游戏可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了。哪三面红旗呢?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是指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工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统称。图为1968年3月《人民画报》发表的游行照片“三面红旗”标语。
总路线不提也罢,大跃进大家都知道,土法炼钢,亩产万斤,赶英超美。人民公社是拆自家小锅,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努力搞生产。
热火朝天的年代,这游戏的口诀想必喊的齐整响亮。

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就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凡是我不认同的,就一定是错的。学校和老师对游戏的判断也如此——凡是学校不提倡的,就一定是胡闹,是理应禁止的。
因此游戏便被分成两种,老师让玩的,和老师不让玩的。老师让玩的叫「做游戏」,老师不让玩的,是「瞎胡闹」。
跳「打倒四人帮」的皮筋,玩「一米二米三」是做游戏,有组织,有纪律,安全有序,在老师的控制范围。再如体育课认证游戏丢沙包、丢手绢、跳山羊、赛跑,都是健康的游戏,尤其是根正苗红的传统游戏丢手绢,那么多小孩参与,但跑得再快也是绕圈。但「老虎抓仙女」明显属于瞎胡闹,甚至可算得上暴力和不要脸。
除此之外,最被广泛禁止的是纸牌和玻璃球。我所遇到的大部分老师和家长,都基于统一战线,认定这两种游戏是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的敌人,滋生病菌,还总令人心驰神往而无心上课。
不合法的游戏,就像未报批备案的游行,是大禁忌。禁忌是压抑本能,也是惧怕本能。禁忌往往是诱惑,就是这个原因。
带画的纸牌,豫东地区的流行叫法很洋气,叫「希瑞牌」。无论牌上印的是变形金刚、百变雄狮、忍者神龟,还是葫芦娃、圣斗士,都叫「希瑞牌」。

希瑞牌。画得有点儿磕碜。
即便牌上是三国、水浒、西游、封神榜、杨家将和包青天中的人物,也叫「希瑞牌」。

印刷得非常粗糙的白蛇传“希瑞牌”。
这个希瑞,就是一九八五年美国动画片《非凡的公主希瑞》中的希瑞。这部动画的译制版于一九八八年引进中国,全国电视台都播。希瑞身穿低胸迷你连衣裙,拔剑之前先高呼一声:赐予我力量吧。既热血,又性感,是中国寻常人家儿童的第一个超级英雄偶像。

希瑞拔剑变身炫目效果。
如今却再没有这样的英雄偶像陪伴中国小孩。黄头发、低胸装,且有严重暴力倾向,怎么能给小孩看呢?在染发都犯忌的当下,这种偶像岂不是妖邪之物?
希瑞牌的入门玩法是「㧾hū」。「㧾」的意思是击打,也有拂拭的意思。对手的牌搁在地上,有画的一面朝上,你将自己的牌使劲㧾下去,掀起一阵气流,掀翻对手的牌,那张牌就是你的了。

一个拼了老命在㧾牌的小孩。
㧾牌要靠技术,攻守各有策略。进攻有三个核心:选对牌,找准缝,扇好风。这三点和打群架的方法论很相似:找准对手,选择时机,把握力度。
防守关键要在牌身上下功夫,买牌的时候要选择纸质厚重的,剪开后要适度把牌揉软,新牌轻薄,容易飘起。将牌放在地上,需和地面贴合紧密,令气流无缝可寻。因此,可把四角略微折一折,让牌像口小锅似的扣在地上。
有了经验和理论,一种叫「两面正」的牌腾空出世——用浆糊或胶布把两张相同的纸牌背面粘在一起。好看又好用,进可猛攻,退可固守。就算被人㧾翻,还有机会扯一番皮:这明明还是刚才那一面啊!
兵家有言,一寸长一寸强。㧾牌则是靠「大」取胜——买来整张新牌,不剪成单张小牌,而以二、四、六的组合将牌剪成大块,有如连环战船。进可扇起飓风,退可稳如磐石。
有好事的,将两种策略用到极致,十几张牌粘成一张山东煎饼大的「两面正」,还在中间夹片铝皮。这种憨货的下场往往是拎着超级武器在操场上寂寞地溜达,俨然㧾牌界的独孤求败。两位独孤求败狭路相逢会发生什么,我没见过。
粗略考证,㧾牌游戏最早一战时就有了。当时英美商人为在中国推销香烟,在烟盒里附赠一张宽约4厘米、长约6厘米的彩印欧美女子半身画片。这种画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毛子片」或「毛片」——难道这是「毛片儿」一词的最早源头?民国小孩玩「毛片」,叫「搧洋画」,多流行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

民国时期“红士牌”香烟广告,广告卖点就是其中附赠画片。
在印刷纸牌无法普及的城乡地区,出现了纸折的「面包牌」和「三角牌」,前者正方形,像块方面包。后者则是前者的一半,标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写这篇文章的间隙叠了一个。
玩这种纸折的牌,在南方一些地方被称作「打撇子」,在广东叫「拍公仔纸」,东北则叫「搧Pia唧」,绘声绘色。

搧Pia唧。
民国小孩还有个玩法,叫「拍毛片」,将纸牌放在地上,以手掌拍击旁边地面,靠气流将对方纸牌掀翻。这一传统在豫东地区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演绎出一种「吸牌」的玩法。直接将手掌往对方的牌上拍,再迅速扬起,以气流将纸牌吸翻。
高手吸牌,拿捏得好,手掌不宜充分伸展,也不能过分向里曲,而是形成一个微微向下的凹型。出掌轻快,收掌迅捷,赢牌不伤手。
玩纸牌很像赌,越赢越想赢更多,输了一心想捞本。有赌场的地方就有老千。有人㧾牌的时候牌不离手,用纸牌的边缘贴着地皮扒过去,掀翻别人牌,这是「扒牌」。但如果你不能像魔术师一样敏捷,最好慎用。否则一胳膊抡过去,掀翻的不是牌,而可能是指甲,就算你不留指甲,也会在中指指肚上留下触目惊心的血泡,一星期都得竖着中指吃饭睡觉。
老师抓玩牌的,主要看你掌心。黑腻腻一层,似肿非肿,必是吸牌惯犯。对另外一种游戏——玻璃球——的玩家,老师判断的则是手背。若食指、中指的指关节颜色有土色,往下到小指颜色逐渐变浅,说明这孩子是初犯,手指尚未被泥地染色。

玻璃球。
遇上玩玻璃球的老油子,手掌拍在泥地上,有变色龙的效果。闭上眼摸一摸,会误以为一只常年不缠绷带的拳击手的拳头,茧子硬得像脚后跟。这是久战沙场的勋章。
有些人不但手背黑,连手掌侧面也油亮,那是因为他不但像大部分玩家一样用拇指弹球,还擅长以手掌侧面支撑,用食指弹球,可能是个高人。

1990年代弹玻璃球的孩子。大部分玩家以拇指弹球。
弹玻璃球,豫东俗称「弹琉璃蛋儿」,有些地方又叫「弹蛋儿」。琉璃蛋儿有两种玩法,一种规范鲜明,有招有式,如华山派剑宗;另一种则很狂野,走哪算哪,可算是气宗。

电视剧《笑傲江湖》截图,风清扬指点令狐冲“独孤九剑”的招式。气宗、剑宗都是《笑傲江湖》小说中华山派的支派,剑宗讲究“无招胜有招”,较为自由。气宗注重内功,较为保守。
先说剑宗。把琉璃蛋儿放泥地上,一脚踩下去,留下个半圆的坑,叫作「窑」。
「窑」前方三五米处画一条横线,叫「杠」。三五玩家,先把琉璃蛋儿从窑弹向杠,按照停留位置与杠的距离排序,离杠最近的优先,有能把琉璃蛋儿停在杠上的最厉害。
接下来的战斗,是看谁先进窑,进了窑就算得了加持,可以去打别人了,打中了,就把别人的琉璃蛋儿赢走了。
没进窑加持的,可以尝试「扒皮」——猛击别人已加持的琉璃蛋儿,将它打出八拃以外,就是扒掉了对方吃子儿的能力,劲要再猛些,打出十六拃以上,就直接吃掉了对方。

弹玻璃球高手。
气宗的玩法不需要「窑」。随便定个次序,就地溜出,你追我赶,谁先击中对方就是赢了。放学回家路上,几个人一路走一路斗,能玩上几里地,玩得汗流浃背,满脸污泥,落拓不羁。
由于战线长,地势变幻多,野战不要求必须贴地弹,可以将琉璃蛋儿拿起来,从半空弹出去。这种自由式的战斗更讲究审时度势和准头。半蹲着瞄准几米开外的琉璃蛋儿,用力弹出,一条线斜切下去,应声命中。这叫“叮子儿”,高手的必杀技。手上的颜色和茧子只是经验的体现,真正比拼内功就要看“叮子儿”的命中率。
小李飞刀例无虚发,靠的是李寻欢“干燥、稳定”的右手,那只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异常的坚韧有力。”这一点在琉璃蛋儿界同样适用。
小学时的我自持为功力深厚的气宗玩家,练就一只强大的右手,成为街坊一霸。
那几年,我爷爷开了个小卖部。我带着邻居小孩去爷爷那里买玻璃球,然后就地拉开野战,把卖出去的玻璃球赢回来,放回柜台,让爷爷再卖给他们,如是者再三。
好不风光。
老师不让玩纸牌和琉璃蛋儿,理由可上纲上线,事关学业与人生。当妈的不让玩纸牌和琉璃蛋儿,理由多流于表面——“一群龟孙孩子满地爬,腌臜!”
因为这个理由,「砸杏核」、「挑棍儿」和「摔哇呜」也都是被禁忌的游戏。其实,这三种游戏看似腌臜,考验的却是心知识和智慧,不但涉及物理学中的力学和气压原理,深入研究还需要搞化学实验,架锅炉提炼金属。
砸杏核玩的是杏核。吃过杏子,留下核,洗净晾干。地上摆块砖,每人往上搁一颗杏核,作为赌注,再轮流用手里的杏核去砸砖上的杏核。能从砖上砸下来几个,就收走归自己。要是用来砸的那颗留在砖上,就成了赌注,不准拿回去。

杏核。
砸杏核讲规矩。站直了身体,从规定高度瞄准砖头,让杏核自由落体。个头儿高的沾光,质地密实的杏仁是强劲武器。
想赢更多,就需要炼高级装备。大致工序是这样,挑一颗质地好的大杏核,在水泥地上磨出细微小孔,用钉子将孔钻大,把杏仁捣碎弄出来,形成中空。再炼芯子,细保险丝、锡线或牙膏皮,生起火,用搪瓷碗煮。将炼出的锡水从小孔灌进杏核,冷却后就成“大母子”了。
大母子厉害。瞄准了砸下去,砖上的杏核乱蹦,像老鹰扎进鸡窝。方方在《汉口消失的游戏》一文里提到武汉小孩七十年代玩的一种游戏,规则和砸杏核一样,但用的是扣子。武汉方言叫「滴扣子」,“滴”字用得很妙。但我很不解的是,小孩哪来那么多扣子?
与砸杏核类似的是「打瓦」,不过打瓦是要横向击打,比拼装备之外,更需要准头。地上放几块砖,砖上放磨好的小瓦片或杏核,在距离砖头几米处划条线,玩家站在线外朝里扔瓦片,击中即得分。
有些地方,打瓦又叫“打阎王”或“打观音”。蒲松龄《聊斋俚曲》中有“长街打瓦,踢毽罚毛”的句子。这种游戏古已有之。

打瓦。《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他将自己创作的唱本配以当时流传的俗曲时调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学体裁。
「挑棍儿」也在地上玩,挑的是冰糕棍儿。一人一把冰糕棍儿,洒在地上,用一只棍往外挑,一次只能挑出一根,碰到其他棍儿的就算失败,轮到对方。「挑棍儿」需要耐心,手上用巧劲儿。

用冰糕棍玩挑棍的孩子。
冰糕棍儿赢的多了,就用来做手工,编扇子,编图形,甚至有人能编出鸟兽模样,匝匝实实,像模像样。

只要功夫深,冰糕棍儿也能玩出乐高的感觉。
每天揣着装着一把冰糕棍儿溜达,看上去傻,但却大有历史渊源。古人算数时手指脚趾不够用,就研究出了用小棍儿计算的方法。那时候的会计,每天用布袋装着几百多根大小一样的小木棍儿——也有可能是兽骨或象牙,需要算账的时候,就拿出来放在地上摆弄。这些小棍叫“算筹”。人们用算筹搞出了十进制,可以用二百多根棍儿算出任意大的自然数。

西安出土的西汉算筹。
与纸牌、琉璃蛋儿和杏仁、冰糕棍儿比起来,「摔哇呜」是一项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游戏。
听名字,便知道“哇呜”是一种声音。用粘土——我们叫“胶泥”——捏成或方或圆的凹形,薄底儿,最好像个小盆。托起小泥盆,朝盆地哈口气,念个咒语“哇呜,哇呜响不响!”,抡起胳膊将哇呜使劲盖在平地上,一声脆响——这就叫“哇呜”。摔不响的,那叫哑巴。

捏成的泥盆和泥盆被无情摔烂的情形。
挖胶泥、和胶泥、捏哇呜、摔哇呜,有一套相当成熟的工艺流程,哪一步搞不好就听不到那声脆响。
胶泥要在水边挖,不能太稀,也不宜太干。一铲子下去,松散稀疏的、颜色发黑的、或是混着沙子的,都是普通泥巴,和不成形;切面整齐,没有杂质,颜色发黄,摸上去发粘,像和好的面一样,很可能是胶泥。挖着挖着有臭味儿,看上去再像胶泥也别摸,那是屎。

摔哇呜摔疲惫了,有的小孩儿就会把泥巴捏成各种形状,打造自己的泥巴世界。
捏哇呜的胶泥不能和的太软,否则摔下去很可能会摊成一坨烂泥,最多捎带一声闷屁响,有碍视听。判断软硬是否合适,就看哇呜的边缘,若边缘能捏的齐齐整整,轻轻朝地上盖,泥不往下塌,就比较合适。一般来说,哇呜越大越响,但不能过大,超出手掌控制就很难摔。捏好形状后,要细心打磨边缘和底子。边缘要均匀整齐,保证盖下去不透风,底子用手指肚慢慢搓薄,力求厚度均匀。边缘和底子的交界要尽量捏成直角,能兜风。

认真捏哇呜的孩子们。
摔哇呜有个绝招:用自己的唾沫。和胶泥是用唾沫,捏好之后再用唾沫糊一层,这样的呜哇摔下去,声响尤其脆亮,钻进耳朵里,湿湿的,凉凉的。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唾沫?因为用别人的恶心。俩人对战哇呜的时候,除了比响声,还要用自己的泥去补对方崩开的口子。
最骄傲的胜利,就是底儿烂声脆,混着自己唾沫的烂泥还溅别人一脸。
87版《红楼梦》我小时候没看过,每晚一到播放时间,我会被赶出房间,因为“这是大人看的电视,小孩不能看”。这件事困惑了我很多年,弄不明白“不能看”的原因何在。后来读《红楼梦》明白了:小孩不能看红楼,和黛玉不准看西厢,原因是一样的。

87版红楼梦剧照,小孩不能看。
禁忌之所以成为禁忌,是因为被认为会引发危险的结果。亲密关系,和暴力冲突,都是最须提防的危险。
除了「老虎抓仙女」,小学生还有几种易引发危险联想的身体接触游戏。如「骑马作战」和「斗拐」,都是小男孩爱玩的格斗型游戏。
顾名思义,「骑马作战」得有人有马,一人背着另一人就是一组骑兵,作战方式有两种,一是两队骑兵作战如楚汉之争,二是多组骑兵混战像三国演义。每到大课间,大小战场散布在操场各处,喊杀冲天,夹杂着人仰马翻的嚎啕惨叫和骂娘。

“骑马作战”今天的小学生也玩,图片来自《中国日报》。
若有人组织班级联赛,游戏可以快速发展成群殴,即便是平日不怎么闹腾的小男孩,也会为想象中的共同体奔赴前线。
为加强战斗力,还会出现三层人的大吨位战马。这种情形在老师看来,着实可怕,就安排班干部抓捕战马。于是,课间活动时间便会出现黑帮片的场景:两队人马聚在酒吧,两边的扛把子吹胡子瞪眼,眼看脸贴脸要亲上,一支便衣警队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亮明身份。死对头一秒变好兄弟,两队人马相互点头哈腰,搂肩抚背,敬酒点烟。

「骑马作战」确有聚众闹事之嫌,但「斗拐」真不该被列入黑名单,因为它是国际认可的体育竞技赛事——英文里有个专有名字,Judose,翻译过来叫「脚斗」。

脚斗运动员以腿搏斗中。
单膝相抵的搏杀,看起来和骑马作战一样暴力,但其实高级多了。有学者认为,斗拐是从秦汉间的“角抵戏”——又称“蚩尤戏”发展而来。
南朝任昉《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中国戏曲、武术和很多民间运动,都认为自己起源于“蚩尤戏”,因此斗拐应该也是。我觉得这种推论太过取巧,意思不大。

古代插画中的蚩尤戏。
若真的要找“蚩尤戏”在当代民间留下的踪迹,我觉得更可能是小孩“抵头”的游戏,除了没戴牛角面具,跟秦汉玩法一样。在中国南方,把这游戏叫「斗鸡」。

斗拐的小孩。
另有研究认为斗拐是种满族游戏,满语叫“单人库布”,还可以人背人分组对战,叫“双人布库”。

乾隆时期清宫画,满族摔跤手演练布库。
不管渊源如何,斗拐算是我小时候玩过的最有文化和体育精神的游戏,被斥责为“瞎胡闹”实在荒谬。
骑马作战和斗拐,是小男孩的游戏。但也有小女孩玩,力气大的能将小男孩摔在地上,但很可能引来更严厉的惩罚。如果男女混合玩「坐花轿」的游戏,更是犯大忌,不但会被认为不知廉耻,还会被好事者起哄,引出一段流言蜚语和莫须有的故事。

台湾一间小学的小孩玩坐花轿游戏。为这两个抬花轿的小哥感到担忧。
玩「坐花轿」很简单,两个小孩面对面,两手交叉,相互握紧,四条手臂形成横躺的8字,坐轿的小孩把两腿放进去,就算坐上了花轿。这种游戏多在学前班或一二年级的小孩里流行,大点的孩子玩这个,就会发展成另一种骑马作战,把花轿改装成战车,战事一旦激烈,众人叠成一坨,堪比一九九九年的先锋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1999年,48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现代摄影作品,内容为10名裸体男女叠罗汉。创作者为10位来自北京“东村”艺术区的自由艺术家:王世华、苍鑫、高炀、左小祖咒、马宗垠、张洹、马六明、张彬彬、朱冥、段英梅、吕楠。
还有一种群体游戏,隐约记得名字叫「钻山洞」。两个小孩手拉手面对面站好,扬起手臂,形成山洞的形状。另一些小孩纵队排列,前后牵着手臂,假装自己是火车。当火车从山洞里快速穿过,扮山洞的小孩突然将手臂放下,锁住谁是谁。这种玩法粗野无序,常常被搞成针对某个小孩的集体恶作剧,生出是非。

山东民间有类似游戏,寓意很明显。玩家分成两组,游戏开始前,两队为首者要一句对一句快速问答——
扯皮条,扯皮条。你的皮条几丈高?三丈高,骑大马,带洋刀。洋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红袄。红袄红,切紫绫。紫绫紫,切麻子。麻子麻,切板搭,板搭板,切黑碗。黑碗黑,打起骡子上正北。正北您有啥亲戚?大哥二哥丈人家。姓啥?姓潘。潘家闺女多大啦?十七八。梳头油,带金花。多得儿娶?今儿黑价(今天晚上)。嘀嘀嗒嗒娶了吧!
问答完毕,一组扮演隧道,另一组排成纵队,钻进隧道快速穿过去。
套词和钻山洞的形式,和旧时迎亲娶亲的仪式直接有关,很可能原本就是成年人在婚礼上的风俗游戏。这游戏的名字叫什么呢?扯皮条。
何等危险。
马克·吐温曾吐槽图书审查制度说:审查制度就是告诉一个成年人他不能吃牛排,因为婴儿嚼不动。老师和家长对待游戏的态度就是:这游戏小孩不能玩,因为它让成年人想了色情和暴力。
按照这个逻辑,我玩过最犯忌的东西是避孕套。
夏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把避孕套当气球吹,被众多影迷奉为经典场景。我和他们一样,从中感到了莫大的共鸣。
九十年代青岛乳胶厂避孕套,包装比较简陋。
吹气球是避孕套神秘禁忌的解构。大人看见你这么玩,自己羞得不得了,然后骂你不要脸,但就是不告诉到底哪里不要脸。
毫无解释的神秘禁忌引发更大的诱惑和反叛。我多次在小卖部买避孕套,五毛钱一只,透明小袋子包装。撕开包装,先拿出来捋一捋,越长越松,越吹得大。
但不止于此。我最喜欢的玩法是用避孕套自制水枪。
制造这种水枪,需要较长的一段气门芯胶管、圆珠笔芯、避孕套各一只。抠掉圆珠笔笔尖的圆珠,把笔尖拔下来,接在气门芯胶管上。胶管的另一头,扎在灌满自来水的避孕套上。
轻轻一捏水袋,笔尖就滋出一道水线。
网上的简易版气门芯水枪制作示意,这款没有避孕套加持。
一手拎着圆鼓鼓的水袋,一手捏着枪头,趾高气扬地走在胡同里,随时准备打一场遭遇战。
有不要命的,使劲往避孕套里灌水,作战时需要一个助手专门抱着大水袋,负责发射。圆圆翘翘的一大坨抱在怀里,摇摇欲坠,一不留神便跳脱出去。斗得酣畅,还有人敢怀抱炸药包冲向对手,同归于尽。
这游戏令人怀念,甚至有几分感伤。现在回想起来,眼前还总浮现饱满的水袋在阳光里跳动的美好。这种美好竟有人视而不见,反看作洪水猛兽,实在费解。可能他们也被禁锢在某套复杂精密的枷锁中,只看得见正负黑白,却不知危险里有欢乐,避孕套能折射七彩光晕。
这些被禁忌的游戏,这些早已忘记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