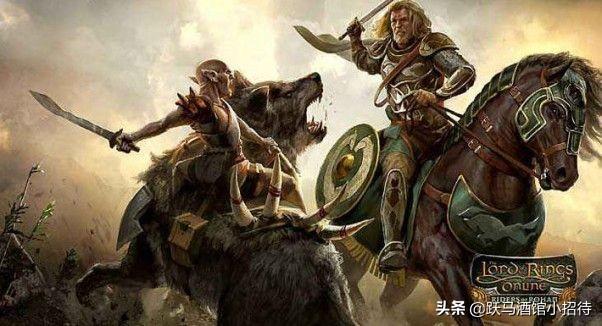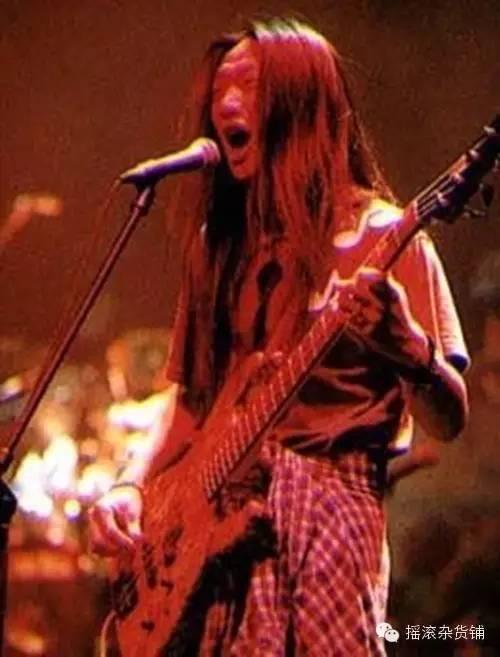大家是不是都听到过一句话,证明清朝时期对蒙古的绝对统治,那就是:“清朝皇帝是身兼蒙古大汗的”。
根据一些史料的解读,我们今天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没有研究过,而黄台吉的确有“博格达彻臣汗”的称号,再经过许多自媒体的宣传后,形成了现在大家的共识。
其实有学者很早就指出,清朝皇帝有蒙古大汗尊号或兼任蒙古大汗之说,是海外一些学者按照欧洲史上君合国的理念而加于清史上的产物。其实这类学说刚开始是为了证明当时中国是属于联邦制国家,而非单一制国家而创造的,结果被国内学者反驳后,现在反而冒出一些辨识度不高的人(低水平)拿出来用来反向证明,我是真有些无语。
钟焓的《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权”理论商榷》中有部分说明,我引用一下:
在最近数十年来美国清史学界陆续发展起来的多种新兴学说中,所谓的“共时性君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应该是其中最为流行的理论或命题之一。虽然它的某些要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由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初步提出,但无疑只是经过了柯娇燕(P. K. Crossley)等美国新一代清史学者的“概念提炼”(concepualization)之后,才达到了目前的全新深度从而广为人知。 这种理论最为通俗化的表述就是,清朝君主同时具备了下列多种身份,即对于汉人(国外学者一般用Chinese表示)来说,他是恪守儒家道德观念的天子-皇帝;对于满洲旗人来说,他则是汗王(han)或者族长(clan leader);相对蒙古王公而言,他身为遵循成吉思汗统治传统的可汗(qaγan);最后在广义上的藏传佛教信徒看来,他又成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上述诸种身份反映了清朝君主平等地采取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与文化手段以联络怀柔帝国治理下的多个族群。 这种统治机理最为突出的本质性表征就是所谓的多语种文献的“合璧”形式,以致该理论的阐述者柯娇燕教授直接将“合璧”(满语kamcime)换译为英语表述中的“共时的”(simultaneous),用来揭示其概括的清朝君权的实质。与之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冈田英弘的有关主张。
我引用上面是为了说明,国内很多人对“大汗”这个说法是有异议的。实际现实情况也是这样,上面图片中众多的称号只有黄台吉的“博格达彻臣汗”经过草原的认可,其余汗号都是其年号的蒙古意译而已,根本不是汗号。
从溥仪都有汗号大家也能看出来不对劲了,换句话说,清朝皇帝是没有“汗号”的,图片中的一切都是欺负我们不懂蒙语而已。
额耶尔札萨克汗(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即顺治帝)
恩赫阿木古朗汗(Энх Амгалан хаан,即康熙帝)
纳伊拉尔图托布汗(Найралт Төв хаан,即雍正帝)
腾格里特古格奇汗(Тэнгэрийг Тэтгэгч хаан,即乾隆帝)
萨伊什雅尔图伊鲁格尔图汗(Сайшаалт ерөөлт хаан,即嘉庆帝)
托尔格勒特汗(Төр Гэрэлт хаан,即道光帝)
图格莫尔额尔伯特汗(Түгээмэл Элбэгт хаан,即咸丰帝)
布伦札萨克汗(Бүрэн засагч хаан,即同治帝)
巴达古尔特托尔汗(Бадаргуулт төр хаан,即光绪帝)
哈瓦图猷斯汗(Хэвт Ёс хаан,即逊帝溥仪)
如:【顺治帝】顺治为汉语年号,蒙语为【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Эеэр Засагч】蒙为“平顺统治”,【хаан】就是“可汗”的“汗”,蒙语中没有皇帝这个词,对应的就是“汗”,全称就是【顺治汗】
所以顺治的【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再音译回汉语,就是“额耶尔札萨克汗”了。
蒙语中帝字会翻译成汗,是因为少数民族语中没有皇帝这个称号,他们的叫法我们统一翻译成为“汗”。
而康熙自己给蒙古的信中,也是没称自己是qayan(可汗)的,而是称为quwangdi-qin (大清皇帝),满文比蒙文要晚许多,其中借鉴汉语的地方也更多一些,大家在上面的大概发音中也可以感觉出来。
而且,蒙古其实是只要是部落就有大汗,可以同一时间多个大汗共存,我刚才说的论文中也论证了,大汗的等级其实并没有多么的高,清朝时还存在许多大汗,比如: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杜尔伯特汗、旧土尔扈特汗(卓里克图汗)。
那么黄台吉的“蒙古大汗”身份又是从何而来呢?
是因为林丹汗的儿子投降了后金,虽然当时他们的势力已经基本没有了,但从名义上来讲,后金是全盘接手了他的一切,包括汗位。
这里又有一个信息,就是林丹汗死后,其子额哲给黄台吉奉上了一枚“玉玺”。
黄台吉当时咬定这尊玉玺是“历代传国玉玺”,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于是钤用此宝称帝,改国号“后金”为“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以天子自居。
但这枚玉玺在整个清朝却不见什么记载,传到乾隆时期更是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呢,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传国玉玺,实为汉篆“制诰之宝”而已。
下面在简单说一下黄台吉的汗号,所有皇帝的汗号中只有黄台吉的是最受认可的,但其实这个也一半是“蒙古意译”,翻译倒腾而出的产物,他的【博格达彻辰汗】算是“一半汗号”。
黄台吉时给自己起了个【尊号】,叫【宽温仁圣皇帝】,蒙文诏书中就有“宽温仁圣世祖皇帝”之类的称呼,这个【宽温仁圣皇帝】,意译为蒙语为【Богд хаан】,【Богд】有“圣”的含义,【хаан】前面说了就是“汗”,满语将【宽温仁圣皇帝】意译为【Enduringge Han】,【Enduringge】也是“圣”的意思。【Han】同样为“汗”。
皇太极的所谓“蒙古汗号”,明显也是个音译,蒙文即【Богд сэцэн хаан】,眼熟吧!不就是【宽温仁圣xx皇帝】。
中间的【сэцэн】,意为“聪慧”,音为“彻辰”,其实就皇太极的【天聪】,可以理解为年号或尊号。也就是说,所谓【博格达彻辰汗】,依然是“来回翻译倒腾”产物,只不过多了一层意思而已。

蒙语对明朝皇帝怎么称呼呢,也差不多,在《黄金史》《蒙古源流》里,就有“朱洪武可汗”“永乐可汗”“景泰汗”翻译过来的这类的音译。
中国君主称为朱四汗。先是中国皇帝死,其长子与四子各分一地。后来四子击败长子夺取国家,其国治国有法,国中不得随意纵马践踏。
正统帝朱祁镇
初,阿速特之 阿里玛丞相,配额森所获之大明正统合罕以名摩罗之妻,摩罗之妻唤之曰:察罕小厮。而役使于家中,时其国中天灾疾疫繁衍焉。一夜,当察罕小厮之睡卧中,阿 里玛丞相之一- 婢,(早)起挤牛乳,见自察罕小厮之碗内现出明黄色之光芒,向右盘旋。乃言于其夫人阿噶答赉矣。由此相传,众皆观之,共相惊异曰:“此必大福之人也。自收此人以来,凡事不利,今尤示不凡之兆,当送还之也。”遂送还大明正统合罕,以故自大都之帑藏中,出彼乌齐叶特不胜负荷之黄白物矣。彼正统合罕在蒙古所娶之妻摩罗所生之子朱太子,即阿速特之塔勒拜塔布囊云,盖是矣。
《蒙古源流》北元萨勒车臣
天顺帝朱祁镇
正统合罕回到大都,其弟景泰合罕说“按照次序,你应该做皇帝”。正统合罕说“你平定祸乱,天意已定,不可更改,皇位你做”。于是景泰即位,直到七年后景泰死,正统合罕这才即位,他自称天顺合罕,意思是“天赐的运气”。
《蒙古源流》萨勒车臣
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用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姚大力对成吉思汗的称呼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也指出:“蒙古政治体系采纳‘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呼,乃始于蒙哥时期。”
还有实际上,也有很多史料证明蒙古并没将他们视作全蒙古的大汗。就拿哲布尊丹巴一世和噶尔丹这两个死对头来说,前者称清朝皇帝为“南方黑契丹可汗”(《哲布尊丹巴传》),后者称之为“中国皇帝”(《平定朔漠方略》)。土尔扈特的渥巴锡东归,首先献给清廷的物件中就有明朝永乐八年敕封玉印,可知在他眼中清朝是继承明朝的政权,而非蒙古大汗,如果他认同清朝皇帝有蒙古大汗身份的话,就不会上缴明朝玉印了。
综上所述,清王朝皇帝兼任“蒙古大汗”只是个误传而已。
清时把蒙古分为外扎萨克和内扎萨克,对于外扎萨克清一直也是以外藩来称呼,所谓设置的乌里雅苏台将军“镇守外蒙”更多的也就是象征意义,乌里雅苏台将军手里那点儿兵力也根本无法镇守。
乌里雅苏台将军属员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员,满人、蒙古人各一员。
章京四员,掌管四部衙门,见办事衙门。
绿营换防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三员,外委一员。
唐努乌梁海总管五员(每旗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五员(每旗五员)。
清朝统治蒙古实行的是“盟旗”制度,这种制度类似八旗的形式,又是在蒙古原有的封建世袭领地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它基本保留着原蒙古封建主政治、经济统治权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分化实力。
为了限制旗的发展,除了宗教以外,还使各个封建主的势力相互牵制,在旗上设盟,盟也是沿袭了蒙古大小封建主原有的集会形式,比如当年发动土木堡之变前,也先就预先与蒙古各部进行了会盟。
关于外藩蒙古上面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了,其实在乾隆的概念立,西藏也同属于外藩。
金川善后事宜。经军机大臣遵旨定议。归入西藏管辖。但西藏终属外藩。以塞内土司。归其管束。形势实有未便。莫若以治藏之法治之。《清高宗实录?卷305》
结束语差不多同样的治理方式,对于明清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双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