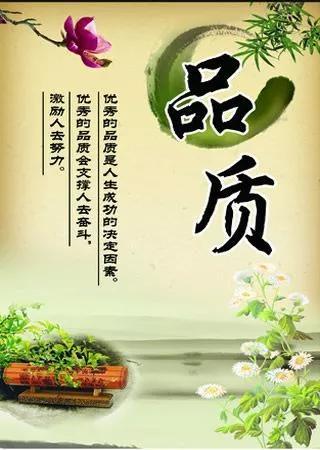“只要看到牦牛的尾巴飞起,羊群在湖旁眯着眼,那我就回到了故乡。”
---松巴益西白觉(སུམ་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1704-1788)
牛羊:静候着神灵和游子
喜马拉雅地区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创造了这个地方独一无二的文明。这种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纯粹的“游牧文明“或者”农耕文明”;在这个文明下,人民崇尚稳定的地域性,但又热衷于流动式的迁徙。
牛羊们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担当工具,在游牧生产中更是最基本的资本单位。
我们一般将青藏高原的地域分为:藏北高原,藏东高山河谷和藏南谷地。藏北地区虽然占据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这里被山林所割裂,雨水长期被阻挡在群山之外。
但是这其中广袤无垠的羌塘草原为放牧和游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而藏南的谷地虽然被称为“一种被山岭而不是沙漠包围的绿洲”(拉铁摩尔),但是这里拥有极佳的农耕条件;且群山的环绕给予了藏南谷地天然的屏障(具有较强的联络性)。
虽然藏北的诸政权都臣服于核心王朝—象雄,但是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使其离散心一直较强(大小象雄下的诸邦国联盟)。
藏南谷地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加之一次又一次的“农业革命”(从渔猎农耕到定居农耕)使谷地政权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占据优势;最终来自藏南谷地的吐蕃王朝统一了青藏高原(通过占领农牧业生产的交叉区域:拉萨河谷),并将农耕与游牧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
换句话说,谁先完成生产革命,谁先占据了中间区域,谁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茹列杰改革
传统文献中将第九代吐蕃君主布德贡杰(སྤུ་དེ་གུང་རྒྱལ་)时期的大臣茹列杰(རུ་ལས་སྐྱེས་)称为“七贤臣”(མཛངས་མི་བདུན་)之首。
如果我们分析茹列杰和他团队的改革措施会发现这些措施的核心几乎都与农业有关。
1.烧木为炭,并利用炭的高温燃烧来融化矿石,随后在融化的矿石中提炼金、银、铜、铁等原材料。这一创举不仅发展了矿业,更重要的是方便了对于生产工具的改良与创新。
2.在双牛上架起“聂心”(གཉའ་ཤིང་;牛轭,双牛枷档,架在双牛肩上曳引犁辕的横杠。)与“通雪”(ཐོང་གཤོལ་;犁)来耕地,加快了种植的速度,提高了生产的质量。
3.茹列杰住持修建了许多的桥梁并发展水利,提高了农业的灌溉力与抗灾能力。这一切“逆天而行”的改革在整体上提升了藏南河谷地区农业发展的潜力,属于“农业革命”中的“工具革命”。

拉普国噶改革
而茹列杰同样为列“七贤人”之一的儿子大臣拉普国噶(ལྷ་བུ་མགོ་དཀར་)则继承父亲的改革,开始了“农业革命”中的“制度革命”。
拉普国噶主持将国土给予农民(规定的持有农田的数量和测量方式),牲畜给予牧民(规定牧场的数量和资产计算方式),而农民与牧民需要向官方交税。拉普国嘎所定的税共分两大类:农税妥孜与牧税堆孜。
农税妥孜(དོར་རྩིས་):双牛一日所耕土地产出的粮食收多少藏升(བྲེ་;藏升,一种容量单位)为收税的标准单位。牧税堆孜(ཐུལ་རྩིས་):根据母牦牛的数量而定的酥油数为标准单位。
农民与牧民可将剩余的归自己所有。这种规范化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敦煌文献《大事年表》【དོན་ཆེན་གནད་བསྡུས་ཆེན་པོ་】有具体的表现:集会收税),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生产中的分配问题,并为国家经济提供了结构化的制度。
藏语中将牛类分为黄牛,犏牛和牦牛。黄牛统称为བ་གླང་(ba glang),其中ba指母黄牛,而glang(原始藏缅语: *glaŋ )指公黄牛。而犏牛(མཛོ་)指的是由公牦牛和母黄牛或公黄牛与母牦牛生出的物种,是藏区农业中最常见的生产工具。在敦煌的《西藏东北民间故事》中这样说道:当时一般在草原放养牛群,在森领放养山羊,在沼泽地放养马匹,在田野放养犏牛,而在岩洞里放养猪。

《西番译语》:牛词条

《西蕃译语》:犏牛词条
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一直被作为早期喜马拉雅先民的核心符号,人们常常使用表示财富的词汇ནོར་(nor)和ཟོག་(zog)来指称牦牛。牦牛分为家养牦牛和野牦牛,其中野牦牛被称为འབྲོང་(’brong;与汉语中的“犛”同源);而家养牦牛因公母被分为公牦牛(གཡག་;gyag)和母牦牛(འབྲི་;‘bri)。

牦牛

涂红的野牦牛,岩画,早期历史时期
在敦煌《小邦与赞普世袭》【རྒྱལ་ཕྲན་དང་རྒྱལ་རབས་རིམ་བྱུང་གི་མིང་】中就称雅砻地区先民称为“六牦牛部”(བོད་ཀ་གཡག་དྲུག་),牦牛成为吐蕃帝国祖源的重要标志。
在本土宗教中,牦牛和其他三个动物(狮子,龙,老虎)被称为“代表生命的四种神兽”(སྲིད་ལྡན་ཅན་གྱི་སྲོག་ཆགས་བཞི་),他们是雪域高原的本土守护者。
从吐蕃时期开始,牦牛和牦牛尾(གཡག་རྔ་)就被认为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其中牦牛尾常被用来制作佛教法器:拂尘(རྔ་ཕྱགས་མཛེས་ལྡན་)。

《苯教生命之树》,19世纪,藏于Rubin Museum of Art

生命之树旁的牦牛守护者

《拂尘》,18世纪,藏于Shelley and Donald Rubin
在南亚的系统中,牛尤其是奶牛是作为主神毗湿奴的化身和湿婆的坐骑而出现,它们象征了生育和繁殖。按照南亚的传统:人们不应该扰乱牛群的安静,因为这种安静是为了迎接毗湿奴的化身奎师那(Krishna)和牧羊女们(Gopi girl)来玩耍与讨论事理。

《奎师那与牧羊女们》,18世纪,藏于Smithsonian Free and Sackler Gallery
而在佛教传统中佛陀的《本生经》(Jataka,སྐྱེས་རབས་)里就有一个关于牛的故事(故事33号)。

《本生经:宽忍的公牛》,19世纪,藏于Zanabazar Museum of Fine Arts
《本生经》
尽管前生拥有无数的善行,但是因为业力还未成熟,菩萨降生为一只大水牛。这只水牛即使处在愚昧无知的畜生状态,但是对于有情众生它都保持着十足的善意与同情。
这头水牛外表狰狞,身上总是粘满了泥块,令人生畏。然而,有一群恶趣味的猴子,知道水牛的本性善良,知道水牛会原谅它。所以对它并不害怕,反而一直戏弄它。猴子时而爬上水牛的后背,一直摇晃它的牛角;时而站在水牛的脚边,阻止它在饿的时候吃草;猴子有时甚至会用尖利的棍子戳水牛的耳朵。然而水牛却没有任何怨言。
有一天,一位天神看到猴子们所做的种种恶行,不禁对水牛所受到的侮辱感到震惊。他想知道为什么水牛不帮助自己免受这种折磨。天神出现在水牛面前并告诉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那群猴子”。随后天神又问道:“为什么不阻止猴子?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吗?你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害怕那只猴子?”。
只见水牛拖着疲惫的身躯回答道:“并不是因为你说的种种原因,而是猴子天性狡猾和狂躁,它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我想帮助猴子让它们的内心平静下来”。过了一会,水牛继续说道:“对那些更强大的人保持耐心是很容易的,但当遭受到来自弱小力量的伤害时,我们真正的耐心与宽容才会表现出来,不是吗?”。
这样的回答让天神顿生虔诚之心。随后他将猴子们从水牛的后背上赶了下来,并给水牛传授了一种保护咒后消失了。或许真正的宽容从来都不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而是与所有的生命体产生了共鸣,同喜同悲罢了。
许多本土的护法神都选择使用愤怒的牦牛作为自己的坐骑,这里将重点介绍拉萨河谷众多山林的守护者大咒师(སྔགས་པ་ཆེན་པོ་)和西藏东部(尤其是嘉绒地区)的山神白聂妃(གཉན་ལྕམ་དཀར་མོ་)。

《大咒师》,18世纪,藏于John and Karina Stewart
大咒师原先是在拉萨山谷附近的苯教咒师,长期有偿地帮助附近的村民消灾降福。后来阿底峡大师与他相见并教其修行佛法。随后他的形象就从一位本土的宗教人士成为了密宗瑜伽士,发誓要守护圣土拉萨的群山。甘丹颇章政权(1642-1959)时期常常会将一些重要的山神进行合祭,其中就有这位大咒师。

《白聂妃》,19世纪,寺院壁画
“聂”在本土宗教中是一种需要人们常常酬供的“中间神怪”(功利性对象)。而在嘉绒地区的苯教宗教人士常常认为这位聂神不同于其他的“聂”;她是嘉绒本地山林的保护者,维系着山林万物的兴旺。人们相信白聂妃的坐骑牦牛会帮助路人在山雾弥漫之地走出来并安全回到家中。
除了牦牛这一本土动物,其他牛羊也常常被作为神灵的坐骑。这些牛羊张着嘴吼叫着,一边感受来自神灵的威仪,一边又向世人宣告着神灵的到来。

《黑威罗瓦金刚》,16世纪,私人藏品

《红威罗瓦金刚》,17世纪,藏于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威罗瓦金刚(Yamari,གཤིན་རྗེ་གཤེད་)被认为是文殊菩萨教法的护法神,并在藏区的各个教派得到供奉与实践。
一般将威罗瓦金刚分为红色(Rakta Yamari)与黑色(Krishna Yamari),也会因藏区的宗教史阶段而分为旧密形式和新密形式。从文本来源来看,黑威罗瓦金刚来源于南亚,而红威罗瓦金刚则是本土化诠释的结果。这两个神灵都骑着一头嘶喊的水牛,水牛的颜色和主神的颜色相对应。
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些神灵拥有牛头,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大威德金刚(Vajrabhairava;འཇིགས་བྱེད་)和阎罗主(Yama Dharmaraja;གཤིན་རྗེ་)。

《大威德金刚头部》,15世纪,藏于Rubin Museum of Art
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联想同样是文殊菩萨教法中骑着牛的威罗瓦金刚),他和下文的阎罗主同属于一个教法系统。
一般认为这个传统是由阿底峡大师,热译师(རྭ་ལོ་རྡོ་རྗེ་གྲགས་པ་;1016-1198【文献中岁数就是那么大】)和曼译师(མལ་གྱོ་བློ་གྲོས་གྲགས་པ་;十一世纪)传入西藏。在萨迦派中大威德金刚是四大主要密教护法神(རྒྱུད་སྲུང་བཞི་)之一。而在格鲁派中大威德金刚被作为最主要的核心护法神而被供奉,其教法实践方式非常复杂。

《大威德金刚》,19世纪,藏于Shelley and Donald Rubin

《阎罗主》,19世纪,藏于Rubin Museum of Art
而阎罗主的教法源流和大威德金刚相似;需要注意不要把地狱中的阎罗王和密教的阎罗主做过多联系。阎罗主和大威德金刚都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主要保护者。在一般的塑造中,阎罗主手上都持有骷髅棒和套索,旁边有与他形象相似的明妃相伴。

《阎罗主》,19世纪,私人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