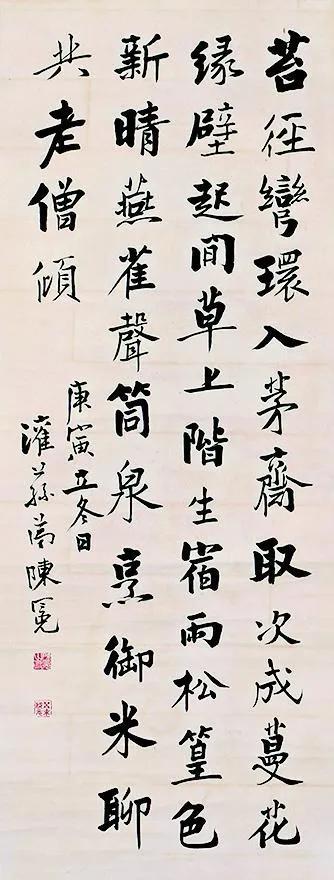江冀县人吴同,与其弟吴昊,载一船好货由水路到达新山,登岸货卖,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古代身上带的球形香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古代身上带的球形香炉
江冀县人吴同,与其弟吴昊,载一船好货由水路到达新山,登岸货卖。
这日无事,便去市场中闲逛。见人卖一匹白练马,只见那马在耀日下甩动鬃须,昂首向上奋力打一个响鼻,有穿云度日之功。
吴同无限喜欢,前去讨价还价,马主渐不耐烦:“八十两银,不能再少。”
吴同见差不多了:“随我来,同去取银。”二人交易妥了,马主自去。
不久,掉转船头返回。先在船上搭了个围栏,将那马圈在当中,一路行船。
途中,行船至茗山地界,此处弯多浪急,船到此一向摇晃犹剧。那马从未经船,吃不消水上颠簸,遂哀鸣不断。打动得吴同怜悯,急叫人将船靠岸,独个牵马下船去溜达。
因日头正盛,见前方不远,一片浓密树荫,便一人一马走进林子。
哪知遇一阔少,带帮人在此打猎,正赶着一头野猪穷追。见树密处,枝叶晃晃悠悠,不甚明了,阔少只顾张弓搭箭,“嗖嗖嗖”连发数箭。
那马被吴同牵着,悠闲处正扇得好尾巴,蓦地数箭流星赶月飞来,一箭射中马头,矢贯而入,一下穿透了。只见那马跪倒在地,立时而毙。忽地天降横祸,吴同一下愣住。
那边齐发喊:“着了,着了。”约十来人刷刷地赶将过来。阔少兴高采烈走在头前,见射死别人的马,情知不妙,只“咦”一声抹头就走。
吴同见他领头,手里拿张弓,哪里肯放他走了,追上去,一面叫“哪里走,还赔来。”一把抓住阔少衣带。
阔少走不脱,“哇哇”大叫。众奴见了,齐上来拉扯吴同。吴同强扭不放,众奴乱哄哄人堆里使劲朝他踢打,吴同痛得怪叫,撕下阔少一大块衣襟。
那阔少也因此得了自由,窜向另一边,吴同紧追弹射而起,从后伸手臂就搂住了阔少头颈,任由雨点般拳脚打来,只是不撒手。
可怜阔少便觉气紧,由不得鼻歪口斜,金星飞舞,一口浊气卡在喉头上下不得,一时间,竟吐白沬死了过去,吴同这才发慌松开手。
众奴按倒吴同,拿条绳捆住,押着他,一面抬阔少,哄乱回庄报与庄主。
庄主名高钟,见儿子活蹦乱跳出去,现被人横着抬回来,吊大白眼不知死活。他只这独子,抢天扑地大叫:“儿啊。”
嘶喊雷动,他儿子忽地一口黏浓,吐出浊气,活了过来。生怕他再嗝儿过去,百般叫人寻大夫救治。
问过众人,不由分说就叫人将吴同往死里打,未了说道:“先丢在地窖,明天继续打,倒要看看谁敢来取人,连同都绑了。”
这高钟拥有好大的庄院,腰肥势大,当地人都惹他不起。如今他儿子遭罪,一来心痛,又觉老脸没处搁,因此有心要在人前耍威风。
那边船上,紧等吴同不回,初并不太在意,又过许多时,还不见回,仍以为才买了马,兴致太高,遛得远了,因此耽搁。
然而,看看天色将晚,仍不见人,兄弟吴昊就觉有些不对劲儿了。
这吴昊十五、六岁,正是青涩年纪,首次随哥出门学做买卖。
因见他哥久也不回,急急下船,一路寻去,直走到附近人家,终于打听出事来。这还了得,立即心急火燎地找到那个庄院。
远远望见四面高墙,房檐重叠。自认孤身力薄,不敢贸然进去,急得周围转来绕去。
天色更加昏暗,他转到了庄的西侧外面,忽听见车轴“嘎吱”响,只见一辆牛车过来,车上尽拉草垛。
庄侧有一小门,牛车来到门前,车上跳下一人,“咚咚咚”敲门,随即门开。牛车停门外,不久就有几人进进出出,卸下一梱梱草垛往庄内搬。
机不可失,吴昊一猫腰,绕到牛车后。那几人只顾搬运,草垛高耸遮住了头。吴昊打门角溜之进去,不远就是柴房,墙根满是杂物,吴昊迅速闪将过去,就蹲在了杂物堆里。
待牛车去后,门重又关上,偌大的庄院变得人声稀少,仍时不时有人来柴房取用,只在咫尺之间。吴昊屏住呼吸,尽力缩成一坨,恨不得变成纸人钻进窄缝。头嗡嗡作响,心也呼之欲出,才稍缓,又见人来,搞得他六神离位,分崩离析。但转念想到他哥,一下子又振作起来。
夜已漆黑,再无甚动静。才慢慢移身子出来,伸头转颈,穷尽目力,来回地切望,比那夜叉探路还胜几分。一番辨识过后,渐弄清周围大致景象。
好大庄院,该往哪里寻人呢?随东往西的胡乱走,随来到一处大屋,甚是华丽,屋内暗点灯火,似有响动,忙躲在窗下,贴耳倾听,听得沙沙声。
“什么声音?”正疑间,黑暗中冷不防,忽地窗被推开。吴昊一下惊魂,急将身子一缩,就地滚出,趴在了花台之下,伸头望。
屋内灯光已灭,窗台上现出鬼影般轮廓,只见鬼影中伸出人头,往四下观瞧。吴昊已然看清,分明是人。
只见那人跳出窗外,手里还拎个包,转身将窗轻轻合上,溜烟就走。吴昊随其后,隔老远吊着。
一路尾随来到后院的小树林,只见那人蹭蹭就上了树,树叶“稀里哗啦”摇晃,那人很快下来,手里已没了包。“好个贼人,藏脏与此。”吴昊暗道。
只见人影从树上“滋溜”滑到地面,又来到一排连屋,轻手轻脚推开一扇门进去,随即关上,也不点灯,再无动静。
“哦,原来内贼,究竟藏的何物?”吴昊暗道。重又回到那棵树下,但他身子瘦弱,又找不到可搭手之处。就要一探究竟,忽想起他哥来,连忙丢下,继续寻找。
庄阔屋多,百般搜寻,直至大半夜。隐约闻听得人声嘀咕,忙止住脚步,伸头缩脖地听好一阵,不甚明了。于是匍匐向前,靠得近了,见两庄丁坐躺在一块青石板上说话,一面猛打哈欠。
一人说道:“大半夜还紧守这里,露冷僵人,着实叫人受不了。地窖里那小子倒好百倍,暖暖地正睡的好。”
另一个说道:“他打伤少爷,老爷怎会轻饶了他,明日不打死才怪。”
吴昊看见,青石板盖住地窖口,窖口略高出地面。
只见一人起身伸懒腰,说道:“不如我先回屋睡片刻,再来换你。”
“好哩。”
商量妥贴了,两人当中便去了一个。不去的那人仍斜躺在青石板上,因无人说话,精神萎靡,头渐渐搭拉一边。
“原来哥被囚在这里。”吴昊料定他哥就在下面地窖里。
向假山中扳下一块片石,勉强举过头顶,蹑手蹑脚走到那人近前。见那人正打好瞌睡,猛的一砸,竟带动风声。
那人忽醒,睁眼惊见,猜不着发生了哪门子怪事,惊得神魂出窍,急歪头缩脖子,想躲已然不及。那石掼将下来,削肩连脑壳都挨上,只来得及“嗝儿”一声就人兮鬼兮。
将那人横过一边,伸手搬窖口上的那块青石,然而力量不足,只略微抬起一道缝,连试几次,皆是枉然。渐觉身乏力软,找来根粗棍,再抬那青石,仍如前番抬起少许,咬牙将一只脚伸进缝中搭住了,力道稍歇了歇。
石板重量压在足背之上,钻心大痛。再次用力抬起,较上次稍高,又将另一只脚伸进去垫住了,痛彻肺腑。
腾出一只手,才将棍塞进缝中,死命拽出双脚,双手齐撬动那棍,牙缝中喊了声“嗨”,不敢高声。
青石移动,下边露出个缺口。俯身向里喊:“哥,哥哥啊。”连着叫了几声,才听得下面有人颤颤弱弱地回应:“是弟么?”见是哥的声音,鼻头酸楚,心头一紧,止不住泪水奔涌。
急将棍又撬了几撬,约莫差不多够了,吴昊将半个身子钻进窖口,伸手下去拉人,说道:“快、快,拉住上来。”
吴同终出地窖,吴昊见他浑身是血,不由心碎,继而怒火攻心,忍不住就要使性子。被他哥一把拉住,点指地上那个已在阴阳路上徘徊多时的庄丁,说道:“还是快闪。”
方才醒悟,兄弟拉手,急急寻回原路,已到柴房,见高高草堆,到了门前,拉门栓急出,跑出不远,得一隐蔽处,吴昊说道:“哥哥在此等会儿,我去去就来。”
吴同诧异,忙问:“还有甚事?” 吴昊转瞬已去,再次进到庄院。
不大一会儿,只见庄内火起,火从草垛冒起,烧至柴房,蔓延开来,火光中“啪啪”作响。
吴昊飞也似跑出,兄弟二人不再耽搁,施展逃命大法,撒丫子狂奔。吴同遍体鳞伤,吴昊的脚也肿得恰似小山丘,此刻全忘了痛。一口气跑向停船,一溜烟就上去。船上众伙计正盼得急,不由分说,即刻命驾船逃走。
再回头说那内贼,姓樊,因会识字、算数,都叫他樊九九,高钟就让他做了个管事的头目。谁知他暗地里划拉上庄主的小妾,名如意,无人时常黏成一块。
这如意生得比花儿还好看,恨庄主垂暮老矣,爱慕樊九九风流倜傥,人群中算个人物,常将腥眼偷看,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激情燃烧过后,情亦愈坚,两人就想着哪天远走高飞。
然而,谋划既定,唯独缺那银子花,樊九九便着了歪道,终于为贼。入夜,便趁无人四处踅摸,施展手段。却总在人前一本正经,板起个腔调,俨然道德模范,好不鸡贼。
庄主高钟见莫名其妙地丟失财物,遂发雷霆之怒,但万没想到这个樊九九,反令他各处留心细查贼人。樊九九既受令,自然要寻人顶缸。
一天晚上,下人丁二外面醉酒回来,倒在花台下酣睡。大半夜,樊九九就叫人当贼拿了,先打个半死,逼他招认做贼,丁二死活不肯招,指天发誓称自己为人清白。丁二遂命往死里打,打得浑身稀烂,体无完肤。
樊九九心里跟明镜似的,不过装样子,贼喊捉贼,做给人看而已。后来把丁二给放了,骂道:“醉成那样,活该挨罚,再有下次,还打。”
丁二睚眦必报,何况遭此大难,终日寻机要杀死那樊九九。
一天晚上,瞧见樊九九外出,便揣尖刀摸进到他房中。见床下好藏人,就爬在床下专等他回来。
正等不耐烦,樊九九忽打外回来,丁二爬在床底,只看得见他鞋脚,丁二心想:“待他熟睡再动手才好喃。”
谁知,其后又跟进来一人,见纤纤弱弱的穿一双花鞋,声音是个女子,像极老爷的小妾如意。
“我嘞个去,逮住好大的奸情。”丁二心中骂道。樊九九和那如意腻腻歪歪打情够了,才熄灯共床缠绵。
黑暗中,丁二竖起双耳,但靡靡之声,不堪入耳,丁二就这样在香梦中轮回,几乎要将他冲天恨意直泻得一干二净。
待到云飞过后,房内重新点灯。樊九九忽提起吴同一事:“不知他来路,差点勒死少爷,关他在地窖,谁知那小子怎的又跑掉了,又放一把火,又烧着许多屋,所幸扑灭了,往后几日必乱得很。”
二人缠绵入港,丁二不爱听,床下不敢少动。
终于花鞋离开房间,单剩樊九九在床上睡了。
熬过许久,丁二床下偷偷露半个头来瞧,见樊九九鼻翼起伏,双目似闭不闭,露半截眼白。唯恐惊了他,轻轻拽出尖刀。那刀一尺来长,巴掌宽,精铁打造,刀把上缠块老牛皮,寒光闪闪,阴风惨惨。那樊九九浑然不知,睡得比死人还沉,不知已然死期。
月光洒向纸窗,隔窗见一条黑影蓦然伸长,恰似一柄收割的大镰刀。丁二发疯乱砍,可怜樊九九就在梦里归西。
丁二杀人后,料必被人猜到他,此地已不能再留,遂遁走远方,再无下落。
那吴氏兄弟的船终行至家乡江冀县,其家不远。吴同并未伤筋动骨,无甚大碍,不久便恢复。
这番经历,自是忐忑难安,少不了担惊受怕,生怕什么人半夜闯家来踢门,整日惶恐,只在家闭门度日,祈神护佑,唯愿无事。
时光飞快,转眼过去三年,一切风平浪静,居然太平无事,空自心惊一场。
那吴同在家就渐渐坐不住了,又寻思要跑趟水路。
一日,对吴昊说道:“这年月白闲得慌,咱家船怕也成摆设,空养着许多人,每日用度花销繁多,白花花的恁往外流,总不见进来一个子儿,毕竟坐吃山空。现打听到行情极好,且未错失良机,我估摸着再去做趟买卖吧。回来后,也该为你寻门好亲事。”
吴昊又成长几岁,已大为老成持重,听如此一说,前事惊险仍记忆犹新,无不担心地说道:“只怕不妥,上次虽侥幸逃脱,恐余波未了,此番再出去,倘若又撞上了,恐脱身无计。我们一介平民,吃罪不起人命祸事,不如弃了这买卖,把船也卖了,另寻一门生计才好嘞。”
吴同哪里肯听,只说:“祖业便操此行,岂可到我手里就弃了,我早已详细计议过了,定能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管行船,不再登岸做耍,直抵新山便是,一旦卖完货,回来也是如此不耽搁,保证一路无事。”吴昊见哥态度坚决,不好再言语了,唯听安排。
不几日,准备停当,载满满一船丝绸锦缎,沿水路,往新山出发。
好不巧,行船又至茗山地界。忽地狂风骤雨,天地呐喊,一时惊涛骇浪。此本弯急,那船架不住左摇右晃,势难驾驭。
本应停船靠岸,待风雨过去。但唯恐多事,不敢多做停留,因此只管催行,恨不得飞过这段是非之地。
谁料事与愿违,乱风狂卷,那船忽地打横,猛水灌入,绷断绳索,货物抛向一侧,船体打旋儿倾斜,如何定得住,竟底朝天倒扣下去,人同货尽扣在水中,所幸都是经过风浪会水之人,纷纷都游上岸,但满船的货物尽坠。
兄弟俩爬上岸,跌倒在泥滩里,欲哭无泪。终于雨停风止,但见水面布练漂浮,五彩颜色格外显眼。事不迟疑,兄弟俩强打起精神,组织众人极力打捞上来。
好不容易将船拖在旱地,亟待修理。不想雪上加霜,所带盘缠落水,沉在淤泥沙中,轮番下水去寻,确也失之大半。
兄弟俩无限悲伤,看向湿漉漉的成堆布料以及破船,真个鸡飞蛋打,不由百爪挠心,巴不得是场恶梦。吴同半天说道:“快去凉干了,只会渥霉发臭的”难再言语。
又道:“先清点一下剩下的,寻个买主来,随出多少价都卖与他。待凑足钱,再设法修好船,我们就回家吧。”其苦一言难尽。
吴昊环顾四周,无不担心说道:“又到是非之地,千万保佑无事。”
一面叫人到附近打听有无修船工匠,又放出消息,愿折价出售货物。
几天过后,一片愁云惨雾中,忽见远远一群人走来,前后簇拥一顶轿子。轿子来到跟前,扶下一人,巧不巧,正是高钟。因他听说沉船,有人愿折卖货物,因此领人来看,意图捞便宜捡大漏。
吴同看见他,忙向吴昊低声说道:“冤家路窄,今又撞见那个老庄贼。”忙溜过一边躲了。
吴昊虽在他庄院闹过一夜,自认无人能识,因此留在原地应对。
高钟下轿,伸脖伸头望一阵,见眼前那些人狼狈不堪,旁边堆着乱七八糟的货物,一艘横拖倒拽的船,于是拿着腔调问道:“哪里的人?为何到得这里?”
吴昊见他说话时吹动胡须,就觉恶心,又不得不搭理他,拱手说道:“本是行船路过宝地,遇不测风雨,不想翻了船,损了一船的货物。”
高钟皮笑肉不笑:“嘿嘿,非是不测,该是命中有此劫数,能怪谁去。”
又道:“如何处置这些货物?”
吴昊说道:“找个好买主,折卖与他就是。”
高钟早打算敲一笔赚钱买卖,望那堆货出神,又叫人在货堆里乱翻给他看,才问道:“什么货,值钱不值钱?”
吴昊直率回答:“都是上乘的丝绸细绢,若诚心,便折价与你。”
高钟睁睁眼水,问道:“该着多少价银?”
吴昊说道:“原本价值一千五百两,如今泡过水,但也无甚大碍,索性就多折与你咋个?一口价,五百两吧。”
高钟将头甩来甩去,说道“既水泡过,还什么上乘不上乘,一概降为劣等。不如痛快点,这个数。”伸一根手指,望空比划。袖口直往下坠,露出整条手臂。
吴昊大声问道:“多少?”
“一百。”
“岂不白送与你?分明落井下石。”
“已是不错,除了我,谁愿这个价。”
“修船还要用钱呢,坚决不成。”
争论不休,高钟坚决不多给一个子儿。
最后高钟将眼突突瞪着,说道:“小娃娃,就一百两,分文不多给。就再送十根木料与你,修船能用上的。限你明日回话,想通了就来找我,就在不远的那个庄上。”伸手一指方向,竟坐轿走了。
兄弟俩决计另寻买家,谁料高钟已各处招呼过了,无人敢惹他。因此寻来寻去,无一个敢来应的。
万般不得已,只好受此委屈。直到第二日晚晌时,吴昊来到庄院,见过高钟,将布料一车车送到。
高钟见做成这笔划算的买卖,自然心花怒放,将吴昊带到后院,指一片小树林给他看。
吴昊见了,忽想起三年前那晚遭遇,记得贼人就上这片树,抬眼看去,已辨不出当初那棵树了。吴昊嘴上不说,心里直吊着鬼。
高钟一会指这儿,一会又指那儿,嘴里不断地念叨:“这棵,还有那棵,都是甚好的料,你的船也正合用哩,也不要太挑,我马上叫人来伐与你。”
吴昊嫌天色已晚,说道:“我们明日再来伐吧。”
高钟心里想着胡乱砍几棵便了事,忙说:“能费多少时,你们先回去等着,不稍片刻,即可伐了,与你们抬了来。”赶着吴昊人等先回。
高钟催促下人,尽拈歪脖子难成材的树伐倒,不论多粗劣,乱哄哄抬去岸边,交与吴昊,一哄而散。
兄弟俩见送来的皆不成形,骂道:“老贼欺人太甚,天理容他不得。”却也无可奈何,坐在木上长吁短叹。吴昊不由自主抠弄树皮,触到一块硬泥,被他抠下一坨,远远扔出,随即又抠下一坨扔出。吴昊带着怨气,又抠又扔。
忽抠到一块布料,向外拽了拽,卡住了,使劲再往外拽,扯出一块断布头拿在手里。
心头猛一震,忙俯身瞧那破处,满是烂木屑。随叫哥拿来长锹,刨弄出一洞,从里掏出一破布包,打开布包看时,却大为失望。原以为是一包金银,不料却是一只香炉,式样普通,表面黑泥,拿在手里滑不溜秋。
树心腐败,流淌酸液,浸在香炉之上,随意将香炉在身上擦了擦。好家伙,但见擦处金光一现。连着擦了又擦,汇成金色光芒,竟是纯金做成的一只香炉,好沉好沉,上面雕刻文字,细若米粒,更显高深莫测。
原来樊九九来不及取走,死后,便无人知晓,随日晒雨淋,被虫洞裹住,越陷越深,渐渐尘封。
兄弟俩喜从天降,内心狂野,表面处子。每日人前仍是一副愁容惨淡模样。
一面找人修好船,匆忙忙行船归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