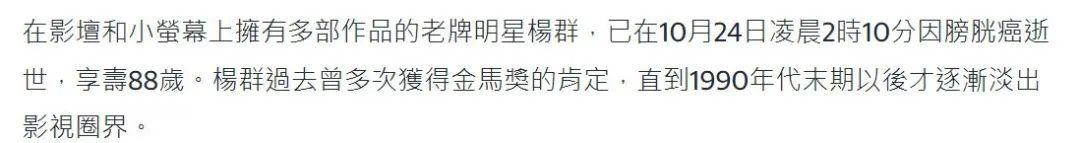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一个很经典的观点: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
这个观点尤其适用于《在路上》,如果不了解凯鲁亚克在什么时代背景下讲述了这个故事,那几乎没可能读懂他。

《在路上》是凯鲁亚克29岁时完成的作品。1951年4月,凯鲁亚克花三个星期,使用他独特的“率真文体”(本书译者李继宏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写作时不推敲,写的越快越好,写完后不审查不修改,最大限度呈现真实的自我”),写完了这部12万单词的作品。作品主题则是关于1947年到1951年间,凯鲁亚克和朋友们三次横穿美国和一次南下墨西哥的真实经历。
凯鲁亚克完成《在路上》之后,最初因为不愿修改而拒绝出版。但最后他不再固执,打算修改之后继续出版,但连续遭到11家出版商的拒绝,出版商方面给出的理由是“难以理解感情充沛但情节松散的率真文体”(李继宏语)。
直到五年之后,1957年9月,《在路上》终于出版,距离小说中首次横穿美国的经历已经过去十年了。
《在路上》出版之初,《纽约时报》就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就像海明威的《太阳依旧升起》,定义了迷惘世代一样,凯鲁亚克这部作品定义了颓废的一代”。
“颓废的一代”是1948年,凯鲁亚克参照海明威对“迷惘世代”的建构,给自己那一代人贴上的标签。随后在1952年,作家约翰·克勒兰·霍姆斯借文章《这就是颓废的一代》,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这个概念。
具体来说,“颓废的一代”指的是出生于1920年到1930年间的青年,亦即在二战前后成年的那一批人。他们身上烙有深刻的二战痕迹,李继宏形容说“命如蝼蚁的惊惶和末日降临的恐惧。”这一点在《在路上》的情节中有强烈的显露。
但李继宏还强调,“颓废的一代”最鲜明的特征不单单是“消极悲观”,还有“及时行乐”,这一点来源于二战之后美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在路上》始终笼罩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中。
上述就是凯鲁亚克创作《在路上》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李继宏译本在本书的开头详细介绍了这些内容。
但即便知道了这些内容,我们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真正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李继宏语)。
《在路上》发表之后,虽然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盛赞,但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抨击,他们不理解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像《在路上》引入我们国内之后,许多读者同样不理解一样。
甚至,《在路上》故事中的人物,也显露出这种不理解。
故事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加拉提雅对主人公萨尔及其朋友狄恩说,“你从来没想过生活是严肃的,没想过人们想要好好过日子,而不是像你这样整天瞎搞。”加拉提雅不理解狄恩他们那种“在路上”的生活。
甚至主人公萨尔也不理解,他在故事里说,“我没有东西可以送给任何人,只能送出我自己的困惑。”
那到底《在路上》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以至于让人如此难以理解?

其实故事情节本身并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难度,真正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情节和行为背后传递出来的意义。
正如上面所说,《在路上》讲述的是凯鲁亚克和朋友们四次真实的旅行经历,他们“在路上”的旅行中,充斥的是酗酒、飙车、滥交、吸毒、嫖妓……
这下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理解这个故事。这样荒谬的故事真的有意义,有价值吗?
意义。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当我们拼命想从《在路上》这个故事本身寻求某种意义的时候,故事中的主人公萨尔也在寻求某种意义,他始终在路上,也始终在寻找,因此他才会一次次地向不同的人问出那个相同的问题:“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萨尔和他的朋友们,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也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凯鲁亚克7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70年后的我们,或许这可以视为是《在路上》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
说回故事本身,只看情节,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故事的意义在哪。因为在我们看来,小说中萨尔和狄恩这群人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乃至于荒谬无耻的事。
但是读到这里,我们还需要继续拷问一下,为什么萨尔和狄恩们要干这些无意义的事?
事实上,萨尔本人对于这种“无意义”是心中有数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在浪费生活。小说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日子其实困苦、疯狂又暴戾,我们走的其实是一条毫无意义的噩梦之路,这一切全在无始无终的虚无之中。”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萨尔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噩梦”有所察觉,那他为什么不改变呢?他为什么不去试着爱上生活呢?而不单单是及时行乐,浪费生活?
问题的答案在上面已经提到了,恰如李继宏所形容的,以凯鲁亚克,或者说以萨尔和狄恩为代表的“颓废的一代”陷入了一种命如蝼蚁的惊惶和末日降临的恐惧之中。
这种惊惶和恐惧彻底摧毁了他们热爱生活的能力,他们不是不热爱生活,而是“爱无能”,“生活无能”,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而摧毁他们这种能力的,是战争,是原子弹,是“生命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死去,而且死得毫无尊严”这种残酷的真相。
小说中多次暗示了这一点,比如小说中老牛说“那些狗杂种现在只对怎样炸毁世界感兴趣”。
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萨尔哀叹道,“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现代文明其实很可悲,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早已破碎的幻想。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一种炸弹能摧毁所有的桥梁和道路,将它们变成乱石堆。”
凯鲁亚克的这些文字毫无疑问是对刚刚结束的二战的控诉,二战中首次出现的原子弹摧毁了一代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在原子弹面前,世界末日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时刻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人们可能在无知无觉中就会走向毫无意义的死亡。
生命的意义被消解了,正常生活的能力同样也被消解了。于是消极悲观和及时行乐就成了逃避生活,逃避现实的唯一良药。

但事实上,《在路上》真正想要传递的并非是这种逃避的思想。无论是现实中的凯鲁亚克,还是故事中的萨尔,毫无疑问都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这一点在小说中也都有暗示。
萨尔说,“因为我觉得只有疯狂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们疯狂活着,疯狂说话,疯狂想要得救”,萨尔梦想着“得救”,梦想着重新获得这种“疯狂”和“热情”。
但最终他求而不得,于是他又说,“你无法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卡洛。没人能得到最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够活下去,靠的就是有朝一日得到它的希望。”
为了得到这种希望,他们一直在路上,在路上就是生活。
到小说结尾,他们一直在路上,但路上已经没有了希望。
萨尔发出最后的,可怜的哀叹,“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会怎样,只知道那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正在慢慢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