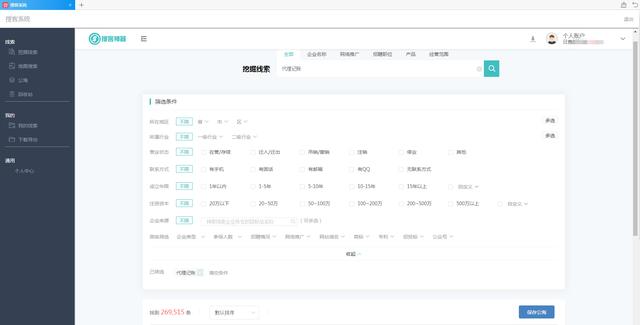凌晨1点多,连续工作15个小时后,61岁的夏开明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工地返回城中村的出租屋。街道上没有人头攒动的喧嚣,只剩两旁昏暗的灯光。通往出租屋的路并不好找,逼仄的街道是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两侧的“握手楼”彼此紧贴,头顶仅剩“一线天”。和那些想要挤进这座大城市的“广漂”一样,这里低廉的房租让他得以安身。

夏开明所在的番禺区大石新桥坊前街
在老家没有很多事干,种地也捞不着很多钱
2000年初,39岁的夏开明离开重庆涪陵区南沱镇老家来到广州。
彼时,夏开明6个孩子当中,2个儿子还未成家,2个女儿还在读书。母亲身患高血压,长期服药治疗。家乡红白喜事办酒席的,还要送人情礼……对他而言,这些都是负担。“在老家没有很多事干,种地也捞不着很多钱。”眼看压力越来越大,夏开明决心南下广州打拼。
2009年7月23日,经人介绍,夏开明入职广州某民营建筑公司土建维修部,“刚开始一直做水电维修,慢慢就什么都接触,粘砖、抹灰、油漆,啥都能上手。”
收入虽然提高不少,但夏开明却感觉身上的担子原来越重,家里的老三和老四相继结婚,为此还欠了不少外债。他必须节衣缩食,努力把自己的生活消费压缩到最低。出租屋不足30平方米,墙面斑驳,白漆脱落,屋子里堆放得满满当。没有信号的电视、旧衣物、四处堆放的纸箱和电工工具占据了他屋子的绝大部分空间。对夏开明来说,屋子里日常积攒的废品,都是他舍不得扔掉的宝贝,“卖了可以凑个烟钱”夏开明笑着说。

夏开明出租屋一角
夏开明回忆,广州夏天的工地酷热难当,很多工友经常脱水中暑。为了节省开支,每次上工地自己都会随身携带烧水壶和水杯。他盘算了一番,一瓶矿泉水2-3块钱,一个月都要一百多块钱。夏开明苦笑,“我们都是在街上不买水喝的人”。
“我们的弱点就是年龄”
2021年10月份,由于所在的建筑公司规定60岁必须退休,夏开明被辞退了。这让他很是发愁,家里的两个大学生还有90多岁的老母亲,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
生活的重负,让夏开明不敢有丝毫懈怠。
夏开明很快就在番禺区市桥工地上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因为是私人包工头,所以很快就上岗了,夏开明又重新干起了老本行。“水电、泥水工、墙砖、地板砖都可以做,只要能赚到钱。”夏开明说。
每天清晨五点的闹钟一响,夏开明就开始起床做饭,将煮好的青菜和大米打包,带到市桥的工地吃。工地规定每天准时7点开工,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工时,他却经常干到凌晨,不过这样的工作节奏对61岁的夏开明来说,已经显得稀松平常。一个月下来,拿到的只有5500元的收入,相比之前就职的建筑公司还降了500块。
“岁数大了,你不做就得走人。”夏开明叹气道,“我们的弱点就是年龄”。
夏开明不是没有考虑过返乡,他曾经计算过,老家总共有2亩丘陵地,一年下来能产1800斤稻谷,收入最多不过3000元。相比家中的开销而言,每月105元的养老金实在是杯水车薪,而家乡的工作又少得可怜。长年在外漂泊的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人脉关系,“干这个活儿有关系的话就方便”夏开明说。
与夏开明早早就来穗不同,64岁的龚日清从2021年4月10日才离开河南信阳踏上去往广州的列车。
龚日清的两个儿子早早成家,他曾经盘算过,靠着家中十亩田,一年也能有1万块钱的收入,对花销不大的两口子来说,这足够养老。
他没想到,妻子会成为他计划里的一大变数。2019年开始,龚日清的妻子相继患上乳腺癌、子宫癌,逐渐变成了“药罐子”,加上每月的复查,一年大概花费六七千块。眼看家里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一直在家务农的龚日清再也坐不住了,硬着头皮赶到广州的工地。

龚日清所在工地的宿舍
不过,能派给他的都是一些杂活。清扫工区内的垃圾、装卸建筑货料……得闲时,龚日清还偷师其他室内装饰师傅,学会了给地砖勾缝,每月还能多赚500块钱。
龚日清向记者透露,之前工地因为雇用一些超龄建筑工,公司还被处以罚款。眼下,工地上熟练的年轻建筑工人并不好找,自己的工作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临时充当的“一块砖”。在龚日清看来,自己的处境并非绝对安全,如果建筑行业“清退令”严格执行,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
“万不得已,就只能跟着私人包工的做。”龚日清说。
“受苦的营生,还得年轻时做”
与年龄增长相伴生的,还有逐渐增加的工伤风险。
从20多岁开始做瓦工,老家山西的廖忠平一做就是40多年,大到古建筑、小至马路牙子、地砖、墙砖,从里到外,他拿起什么活都能做,工友们称他为“全手匠”。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廖忠平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比往日。2019年4月份,廖忠平在一处建筑工地上砌墙,一脚踩空后,体重150多斤的他从一米多高的脚手架上跌落,膝盖、脚后跟多处骨折。“脚手架还不算高嘞,就摔成这样啦。”廖忠平颇感奇怪。
廖忠平回忆,手术总共做了8个多小时。脚后跟、膝盖各被打了2根钢钉,总共缝了11针。膝盖处留下一指长的疤痕,印子还清晰可见。
“受苦的营生,还得年轻时做。”廖忠平清楚地记得,自己28岁那年,从工地2.7米高的房檐上出溜下来,“当时只是两腿发软,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岁月不饶人,曾经铁骨铮铮的廖忠平也开始尝试服用维生素D及钙片,“不知道怎么,感觉现在骨头越来越酥。
眼下,廖忠平又开始承接一些农村建房的私活。“盖低层的房子,年龄大点也没关系。”廖忠平坦言,自己膝下的两个儿子尚未成家,妻子长期患有糖尿病,每月150元的养老金甚至抵不上每月注射胰岛素的费用,仅仅靠种地难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生活的压力让廖忠平不敢停下来,只能重新干回老本行。
警惕建筑业用工,一刀切
此前,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多地出台政策规范用工年龄,55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正在被逐渐清退出建筑工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均作出此项要求,超龄农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工地。
中国中铁某中层管理人员、调度主任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示,建筑工一旦到了50岁左右,精力、反应、身体机能都会下降。建筑行业普遍加班较多,休息的时间就相对较少,人的年龄一大,精力肯定不及年轻人。该调度主任表示,以前工地上隔三岔五就会有脑出血、脑梗这类突发疾病发生。“太劳累就很容易诱发这些疾病。”该调度主任说。
不过,该调度主任认为,目前建筑行业劳工确实紧缺,大一点的单位倒不会因为用工紧缺而放宽年龄限制,反倒好多包工头、一些私人企业因为招不到人而放宽标准。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相比2015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在达到6188万人的峰值,到2020年萎缩到5226万人,五年时间降幅15.5%。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接受南方农村报采访时指出,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就是为了完成财富积累,放弃了进城的希望。而二代、三代农民工不单单为了赚钱,也要参与城市生活,进行生活的城市化。因此才出现大量年轻人宁愿送外卖而不愿意进组装工厂和建筑工地的现象。
吕德文介绍,建筑用工跟其他企事业单位的用工制度有本质的差别。建筑工地多采用的是包工制,且用工方式多是临时性的,所以需要灵活就业人员。“临时用工符合建筑用工市场的规律,有其客观需要。”吕德文表示。
吕德文认为,各地出台的建筑业“清退令”从制度规定上来看,有一定的政策依据。但从实践过程来讲,该规定并不合理。吕德文指出,超龄农民建筑工是用工市场供需双方长期磨合匹配的一个结果,所以有非常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此外,吕德文在调研时发现,年龄是建筑用工市场出现安全事故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安全规范,操作规范这些流程有没有做到位。”换言之,就是建筑企业在劳动管理和企业管理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足够。对于企业来讲,每一个环节做到位都属于企业经营的一部分成本。
“泥工、瓦工这些熟练的农民工多为五六十岁,在建筑经验、技术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吕德文提醒,“以安全为由清退超龄建筑工的做法值得商榷,要警惕建筑用工市场‘一刀切’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