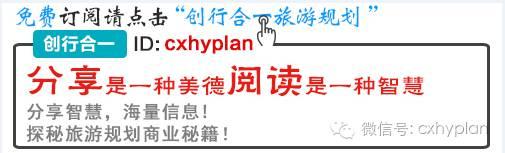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曾多次提到县域经济这个词,但囿于文章主题,一直没有深入地谈这个话题。所以这两篇,三土就打算来和大家聊聊县域经济的前世今身。今天这篇是前传,主要聊历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郡县治,天下安”。县作为一个行政单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当时楚国吞并了许多小国,按惯例,这些土地应该分封出去。但楚王比较小气,不愿意分给别人,而是先将其“悬”置起来,并派出官员直接进行管理。在篆书中,“悬”字就写成“县”。但因为时间久了,从悬那里假借来的县,成了一个代表行政区划的专字,作为本义的“悬”只好另造新字,在县的下面加个“心”,来指代悬挂、悬念的意思。
当然,那时候,县这种行政单位还没有在全国普及。而完成这个工作的,则是那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从秦朝开始,除了西汉初年等少数时期有过反复外,郡县制一直是中国最根本的地方行政制度,直到现在。只不过随着中国疆域版图的不断扩大,在郡县与中央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级。它最初被叫做州,后来也被叫过道或路,最后定名为省。但无论是三级行政单位,还是四级行政单位,县都是最基础的那一级,所以才会有那句“郡县治,天下安”。
当然,县不只是中国的专属,外国也有,比如日本。而英文里的county,在英国被翻译成“郡”,在美国则被翻译成“县”,比如加州著名的Orange County(橙县)。所不同的是,日本也好,美国也罢,都是县下面辖市。在美国,是联邦——州——县——市;而在日本,县与都府道一起,同为中央政府以下最高地方行政单位。比如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名古屋都市圈,其中心城市名古屋就属于爱知县管辖。

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市在县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并非西方意义上的 town,而是披着 " 市 " 外衣的府的转世。如果强行要进行东西比较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府也是县,换言之,中国的郡县制其实就是一个大县套小县的 " 二重县 " 体制。所以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的许多城市,比如嘉兴、苏州,虽然后面都冠之以 " 市 ",其实它们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地区,里面包含了数个县,以及数量众多的 town(它们分别被叫做市区、县城、乡镇)。而每个县底下,又有数个甚至数十个的 town(县城、乡镇)。
而要想改变这种 " 二重县 " 的体制,办法只有两种,要么撤掉上头的那个大县(府),实现省对于小县的直管,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 省管县 "。这种做法在民国初年就曾经一度实行过。而且为了更好地管理县域内的 town,国人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名词:市,并且在广州、上海、哈尔滨等地进行过实践。这些市普遍面积都非常小,其中最有趣的要数哈尔滨。在现在的哈尔滨市范围内,曾经一度并存过两个哈尔滨市,分别为哈尔滨特别市,及东省特别区治下的哈尔滨市。

但后来慢慢的,这些市周边的区域,甚至整县整县地并入市,市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结果,市成了府的翻版,两者除去名称叫法不同,实质上已经没有区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掀起撤地设市风潮,这一换名过程算是最终完成,市也由此取代府,成了县的上级行政单位。目前,全国除了海南省外,其他地方基本都恢复到了传统时代中央——省——市(府)——县的四级行政单位模式。
改变 " 二重县 " 体制的另一种办法,是打破小县的边界,全部融入大县(市)。目前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撤县设区,不过说实话,除了深圳,哪怕是北上广这三座超级大城市,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座城市。因为除了中心城区,其市域范围内普遍还存在数个副中心或卫星城,所以它们更像是西方意义上的都市区。
当然,不管是县市体制,还是市县体制,适合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才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下一篇,我将来谈谈 " 省管县 " 体制的优劣势,以及为什么今天 " 省管县 " 体制必须向 " 市管县 " 体制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