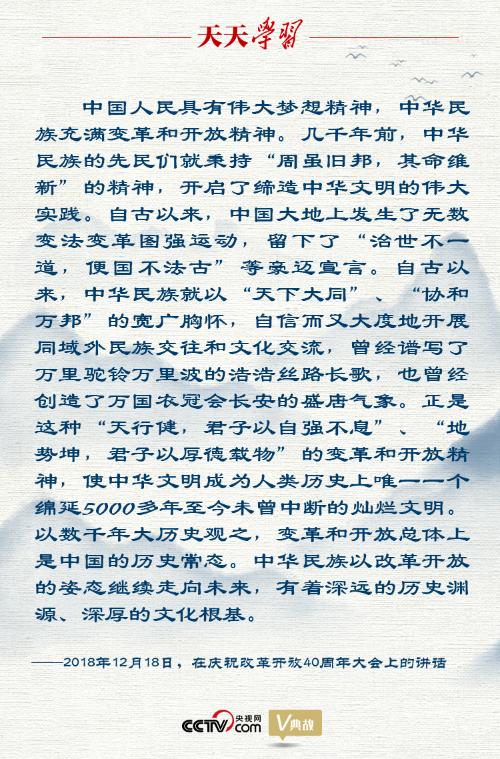中央之国的形成<先秦篇> [第59节]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关于大禹治水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在〈黄河与大禹治水〉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了。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诸多地区都有所流传,但结合当时的地缘结构来看,大禹所治之水应该是在黄淮流域无疑。
而这其中,淮河那些由北向南流,在地理上与黄河接近的支流是将这两大河流连接起来的纽带,也是治水的关键点。如果结合黄河在后世频繁南北改道的情况,有可能的结论是大禹切断了黄河与淮河的某条北方支流之间的联系,并将黄河之水与河北平原的某条河流连接起来,使得黄河干流的水流在山东丘陵的北部注入渤海,进而减弱了淮河流域的水患。


如果从工程量上来看,龙门1的位置位于晋陕大陕谷的南端出口,宽约百米,似乎上古之人集中力量,应该有可能在九年之内疏通这段不宽的河道。问题在于,黄河在到达龙门1之前的这段南北向的河道,是在山西、陕北两大高原之间行进的(也就是所谓“晋陕大峡谷”)。
这就是说,如果龙门1是人工开凿而成的,那么之前未能通过龙门1南流的黄河水又流向哪里,为祸哪里了呢?如果观察龙门1北部的河道是穿行在华北平原之上的就很好理解了,平坦的地形以及黄河的水量很容易冲刷出不同的水道。而在晋陕大峡谷中,两侧的山地高原阻止这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更何况如果龙门1在通行之前,真的高到象三峡大坝大样阻止了大部分的河水,那么黄河之水也最多是在晋陕大峡谷中形成一个大的水库,或者说淹没龙门1以北靠近河岸的耕地。只是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土地即使在现在,也并不具备多少耕种的价值。上古之人很容易在龙门1的南部发现渭河平原和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这样大面积的种植平原,并不需要费力保护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山地。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三大平原成为了西部族群的兴盛之地。
之所以否定龙门1为大禹治水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禹治水的地缘影响是在淮河流域。也就是说大禹通过治水,让淮河流域属于东部族群系统的部族臣服于他。如果将黄河定为治水目标的话,那么真正能够危害到淮河流域的黄河只是下游一段。
从这个角度看“龙门2”将有可能具备这个潜力。唯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龙门2并非黄河之上,而是在伊河之上。正如前面有朋友问到的那样,难道是黄河之水过大,通过伊河水倒灌,进而通过淮河的支流注入淮河 影响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
如果伊河不是西南——东北向最终注入黄河的河流,而是反方向与淮河,或其某条南向的支流相沟通的河流,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正如之后在古典时期,黄河的每次南向侵夺淮河河道,都是通过那些北——南向的河流完成的。
即使黄河之水大到能够逼迫伊水倒流,那么又会出现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那就是大禹所做的应该是在伊水之上筑坝,以阻止黄河之水流入淮河,而并非是用人力扩大缺口,让黄河之水能够更顺畅的进入淮河。
现在看来,让龙门2成为大禹功成名就的地点也遇到了困难。不过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会让一切都符合逻辑。事实上除非有时光穿梭机,否则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被“史料”所证明。特别是在某一个著名景观可以成为聚财之地的情况下,让其他选项就此放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所以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地缘结构的逻辑推测,或者说分析出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逻辑。鉴于以后的内容中还将涉及到类似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声明一下,以上及以下内容,仅为推断,并不被授权引用在具体争议之中。
1:〈大禹治水示意图〉 2:〈龙门位置示意图〉


在推断龙门2是否为大禹治水这地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关键点在于转换一下思路,即为害淮河流域的洪水的确是来自黄河,但这里所说的“黄河水”并非是来自黄河干流的水,而是一条本该注入黄河支流的水。这里所说的支流,就是“伊水”。
如果观察现在伊水的走向,这条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著名水流,在通过龙门2那条狭窄的水道之后,越过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区,与另一条同方向的河流洛河汇集之后注入黄河。这段位于洛阳东北部的河流也因此被称之为“伊洛河”。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明也因为伊水、洛水的存在也被称之为“伊洛文明”。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伊洛文明”的开创者就是大禹。因为在它开凿龙门2之前,伊河的大部分水流并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也没有注入黄河。既然洛阳盆地没有伊河,那么“伊洛文明”也就名不符实了。
不过相比于“伊洛”之名,“河洛”的用法要广泛的多。如果从水量及重要性来说,伊水与洛水对洛阳盆地的贡献并没有质的差别。而河洛(黄河、洛水)之称成为了主流的用法,本身就是在暗示在这片土地开始拥有文明的时候,伊河还没有在洛阳盆地存在,或者说它的流量还不足以提升到与洛水齐名的地步。
那么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之前,伊水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伊水在山上的上游河道,存在的时间绝对不止5000年。只不过由于洛阳盆地南侧的几道山脉连成了一片,伊水在流到了现在龙门2的位置时受阻未能进入洛阳盆地罢了。
既然伊水不能按照水流的方向顺利流入黄河,那么它势必会在山谷中蓄积起来,并寻找适当的出路向其他地区漫流。而这就造成了很多朋友所不熟悉的“汝海”的出现。而伊河之水最终的流向地,正是那个等待以久的“受害者”——淮河。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地形图,会发现伊川盆地如果蓄满水的话,会依水势向东北及东南两个方向漫流。不过在东北方向伊水突围的机会不大,有嵩山、箕山两座山脉阻挡,河水至多会淹没两山之间的山谷,并成为“汝海”的一部分。即使不看地理结构,仅从郑国能够安全的在嵩、箕两山东面享国数百年,我们也能判断出,伊川盆地的水患不会影响到此。
既然东北方向无法突围,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东南方向有没有合适的路径。还不错,这里为伊川盆地留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而伊水之南的“汝水”正是沿着这条通道向南注入淮河的。也就是说伊河之水在注满伊川盆地后向东南方向突围,并与汝水汇合,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湖泊。
由于这个湖泊的水流最终是通过汝水下游的河道注入淮河的,因此也就被命名为“汝海”了。至于汝海的南界应该在哪,或者说有哪一段的汝水扩张为“汝海”。如果考察地形的话,在发现现在的“北汝河”(也就是古汝水的北段)在郏县(春秋时的郏邑,郑国部分有过描述)南部有一条顶角朝东南方向的“V”状丘陵,而北汝河也在此沿着这个角向北拐了个弯后再继续南流。这条“V”状丘陵起到了天然大坝的作用,使得漫流至此的大部分洪水得以蓄积起来,成为汝海的一部分。

在确定了汝海的大致范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古时期,淮河的水患主要来自何方了。也就是说伊、汝之水对淮河流域所造成的水患才是大禹的治理对象。在伊、汝两河的水流还不算太大时,依托山势,这些水流汇集成了汝海,然后再沿着汝水的下游河道向南注入淮河。但到了雨季,伊、汝两河的水量暴涨的话,那么汝海之水就会向南奔涌而下,进而造成淮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汝河之水也是流入淮河的。那是不是说造成上古时期淮河水患的罪魁祸首就是“伊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其实在大禹治水之后,淮河的治理工作依旧是历代王朝的治理重点,并且作为历史上淮河流域最大的支流——汝水两岸的洪灾也还是一直不断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朝的官员甚至将汝水一截为二,将北汝之水入淮河的另一大支流“颖河”(颖水),再注入淮河;而南半部的汝水(南汝河)则与其他河流汇集成另一条独立的河流——“洪河”流入淮河。这种分流的作法固然是能够让古“汝水”的下游地区减少洪灾的危险,但同时也让颖水一跃而成为了淮河的第一大支流,并增加了洪涝的风险。
鉴于淮河的水患一直未断,因此大禹的治理将伊河之水北向引入黄河,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掉问题的方法。大禹之所以为后人所传颂,在于他开创性的用人工治理的方法,疏导了河道,减轻了淮河流域的水患(特别是和之前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大禹为当时淮河两岸的部族所敬仰,并由此开启了中央之国的概念和扩张之路。
至于仅仅是一条伊水的去留,能否造成淮河水量产生质的变化,相信许多朋友都存有疑问。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河流的水患并不是存在于一年四季的。我们所考量一条河流是否存在水患的危险,是看它夏季(雨水多)的最大水量是否大到足以漫过河堤。而测量流量的方法是计算每秒流过多少立方米的水量。
仅仅这样描述,还不足以让大家感受到伊河水在上古时期的雨季,水量会有多少惊人。我们可以得到的数据是,近现代所测量的伊河上游的最大洪峰是发生在1954年8月,流量每秒1370立方米。而黄河在1958年7月17日,于黄河下游郑州北部的花园口所出现的22300立方米/秒水流,为建国以来最大洪峰量。历史上黄河的决堤改道,洪峰量也基本为这个数量级。
至于4000年前的伊水,水量究竟有多大,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幸运的是,中国最早的洪水记录就是在伊水进行的(公元223年),根据当时所留下的记录测算,当时的洪峰达到了20000立方米/秒。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上古时期它的水量有多大了。
换句话说也就是,一条上古伊水所造成的洪灾,足以抵得上后来的黄河水灾了。在这种情况下,大禹用人工开凿的方式,在洛阳盆地与伊川盆地之间的山脉上打开一个缺口,让伊河水,或者说是将汝海的水,分流至黄河,足以让淮河流域部族们的农业环境发生质的变化。
大禹的这次治水工程在地缘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黄河的地缘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而大禹本人实际上也凭借这次治理水患,树立了洛阳盆地在黄——淮之间的政治地位。
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禹及其所代表的部族既然可以通过疏通龙门而减轻淮河的水患,自然也存在人为堵塞龙门,让伊水复流入淮河的可能性。对于淮河流域的部族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地缘威慑力。
尽管伊水的水量在后世已经逐渐减小了,黄河对淮河的这种地缘控制力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春秋之后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能力通过人为的方式,在洛阳盆地——山东丘陵之间的任意一点,将黄河之水向南引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决堤)。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集权结构是源于“治水”文明,从黄淮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既然大禹已经通过治水显示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向分散于黄、淮流域的部落们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威了。由于淮河流域的诸多部落都在这次治水工程中出了力(当然也有坐享其成的),因此大禹需要找一个地方召集各部论功行赏。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行为,以观察自己在淮河流域的威信究竟如何。由于评定功过实际上是一个计算过程,所以这次会盟行为被称之为“会稽”,也就是现在“会计”的意思(学财务的朋友倒是应该去“会稽”圣地拜一拜)。这种做法倒是很象姜太公在“封神台”上所做的,只是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创意封神榜时是否受到了大禹“会稽诸侯”的启示。
关于“会稽”之地究竟在哪里,一直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主要的说法有二:一是绍兴后面的会稽山;二是蚌埠市西面的“涂山”(行政归属怀远县)。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前者的会稽之名明显有附会的意思。而后者的位于位于淮河的中游,如果大禹希望就此确立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威信,“涂山”倒是个合适的地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是在伊川会稽诸侯的,这个“伊川”指的就是伊川盆地(现大部归属伊川县)。如果说大禹希望在自己功能名就的地方会盟诸侯,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涂山和伊川都有可能是真正的“会稽”,只不过对于希望控制淮河流域的大禹来说,“涂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图:大禹会稽诸侯地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