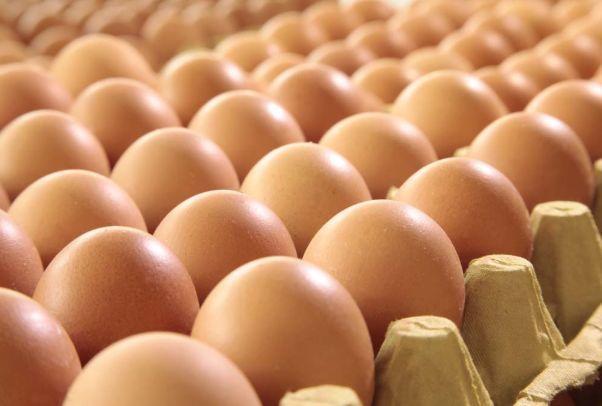文 | 宋扬
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德国哲学家谢林语),有如行云流水一般,偶“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又“一落百寻轻”(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那么与这种万千变化的“动”相对的就是静。因而,要探讨音乐中诸如旋律、节拍等“动”的因素,就不能回避与音乐也息息相关的“静”。
概言之,音乐中的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音乐在开始前和结束后的静,也可称作音乐外的静止;一类是音乐自身产生的静,如音乐本身“安静”的取向,乐段间的空隙、乐句中的休止等。
不难理解,音乐由静到动的过程,在“静”的所有可能中应居首位。比如音乐会,从指挥家或独奏家走上舞台到第一个音符奏响前,这段“无音”时间可被音乐家用来做自身调整,对观众则是即将开始的信号;乐章间、特别是两部作品的演出间隙也需要“静”的参与,如忽视了静的功效,在一首马勒交响作品后,马不停蹄地上演布鲁克纳的另一部交响曲,必会使艺术走向它的反面——过于致密的音乐导致听觉疲劳和反感,达不到传播美的目的。可见,开始前的静止是音乐表演的要素之一,具体停多久要视情况而定。钢琴大师布伦德尔曾说,音乐的先决就是静止。我们也有诸如“静为躁君”“密云不雨”或“意在笔先”等说法。
音乐结束后的静止也重要且微妙。经验丰富的演奏家一定清楚,在快速激扬的末乐章奏完,观众立刻爆以掌声,这是符合逻辑的欣赏习常;而一旦音乐是以慢速收尾,在一种趋于安宁的音响居统治地位时,听众会被感化,被带到与音乐“同起伏”之状态。这时有造诣的听众会在音乐声逐渐淡出许久后才渐渐松口气,而不是马上鼓掌或相顾而言。这无疑传达了一个信号:音乐与人已融为一体。静止在此刻扮演着人们对音乐反思和意犹未尽的角色,构成了音乐的一部分,即所谓“趣在法外”,其存在价值不比音符本身逊色。
人有时会被音乐完全征服,如在受难曲或歌剧中,会产生“休戚与共”的奇特效应——很大程度得益于音乐本身那种深邃幽静的氛围,此正是“静”的第二大类,即音乐中的静。
在欣赏某些经典的安静段落,特别是在现场观演,观众会受到强烈的感染,以致和台上的音乐、乐手以相同的步调呼吸,表现出一样的情绪。这时的大厅在座者已无人再做常见的抓痒、耳语、搜寻节目单等小动作,而是将全部意识投向舞台。听众显然被音乐彻底同化、征服了——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茶花女》中安详重情的倾诉,巴赫受难曲和弗雷《安魂曲》中静穆的宗教氛围,舒曼《童年情景》中平和舒缓、含蓄悠长的《入眠》《诗人的话》等都能使人产生这种共鸣,而这些音乐的特点就是静。一场生动的音乐会,舞台与听众从来都是双向和互动的,台下的这种感动和神往传回给表演者,音乐家也就明了下一步该怎样处理,以使听众获得持久的满足。
宁静的反衬作用在某些独立作品或某个乐章中也特别有效。比如在一个音响起伏较大的乐章,作曲家在汹涌澎湃的乐句中设置了间歇与安宁,好比在惊涛骇浪中行船,偶遇浪静风息,让人释然;或像沙漠中的一抹绿洲,是希望也是休息,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首乐章里,在命运的风暴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之际,突然由双簧管奏出凄凉单薄的乐句,它起到了多重作用:让所有参与音乐的人,包括乐团和听众都得到一丝喘息;同时其曲调又与前后内容相关,便于承启。真是精彩无比,展现了作曲家体法自然,并用于创作的杰出才能。再如贝多芬《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第一乐章,在经受风雨的彻底洗礼后,钢琴奏出几个凄楚的单音,既是对前面历程的回顾,又借着这个悲剧般的温语获得休整,开启下面的急遽内容——德彪西《印象集·水中倒影》以及莫扎特歌剧《魔笛》序曲等都有这样高明的考量与设计。
这些都体现宁静和休息在音乐中的特殊作用,即在紧张之后紧跟一安静段,“于无声处听惊雷”,效果往往更惊人。短暂的宁静通常会在听众心里产生信号:往下会发生什么?造成神秘感,取得转折的意义。总之,安静给人以反思和调整的时机,在休整之后,人们会更加注意下面的音乐,而不是由于听觉疲劳产生腻烦。
静止的另种形式是休止。人靠呼吸来延续生命,音乐是人的活动,因而也有呼吸——其一动一静大体与呼吸相同。人们会因休止而领会乐句的用意,明白音乐是如何进行,又怎样呼吸。休止大到可被称作“暂停”的段落,小可存身乐谱的一小节之中。
例如舒伯特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作品D 795)的第12首即名“暂停”(Pause),第11首叫“属于我”(Mein)。11段的歌词有“那可爱的磨房姑娘,她已属于我”,可表现这位“好逑”的磨坊小工本来自信无比,然而紧跟着12段“暂停”到来,这个“休止”有莫可言状、大转折的微妙用意——之后的一切发生了戏剧变化。磨坊女爱上另一猎手,单相思的小工起初还在狐疑,最后他的结局不免惨淡。休止在这儿竟起到如此不可替代的作用。
休止分隔乐章、乐段,也分割乐句,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分句。可以说,杰出的音乐作品及演绎无论进行到哪儿、有音没音,都暗含着规律,既善于动,也善于收,其“动静之理”也就最能表现艺术家的气质与灵魂。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与诗词规律相通的音乐未尝不是如此,入乎其内,好比音符,出乎其外,可称休止。《道德经》也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个无声的、看似无关痛痒的休止却能把我们带到正确的欣赏位置,这是休止的卓越意义。
然而,能引来上述奇妙效果的休止符,其本身有内容或意思吗?显然都没有。故此休止不能单独存在,它与前后内容结合时才起作用。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曾用“休止”谱成一曲,即钢琴曲《4分33秒》。在这首“乐曲”中,除4分33秒的“静止”外,没任何别的东西——钢琴前坐定一人,在那里静默四分半钟。假使不按古典传统,哪怕用20世纪的作曲法演奏些“另类”的东西或让乐器发声也好,但这种眼观鼻、鼻指口、口问心的沉默式表演也太过超前,太不合常理了。对这种极端“休止”的意义我深表怀疑,毕竟如上所述,休止不能独存。
此外,休止也会因处理不当,产生凝滞、松散等反面效应。而一旦原创者和表演者将休止的真谛付诸实践,将赋予音乐莫大的益处。
贝多芬讲过:“死亡可用休止来表达。”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第三幕“特里斯坦之死”音乐,即按上述意思处理。
【争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栏目欢迎读者投稿参与讨论:
yyzb1979@163.com
- THE END -
“星标”音乐周报微信公众号
不错过每条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