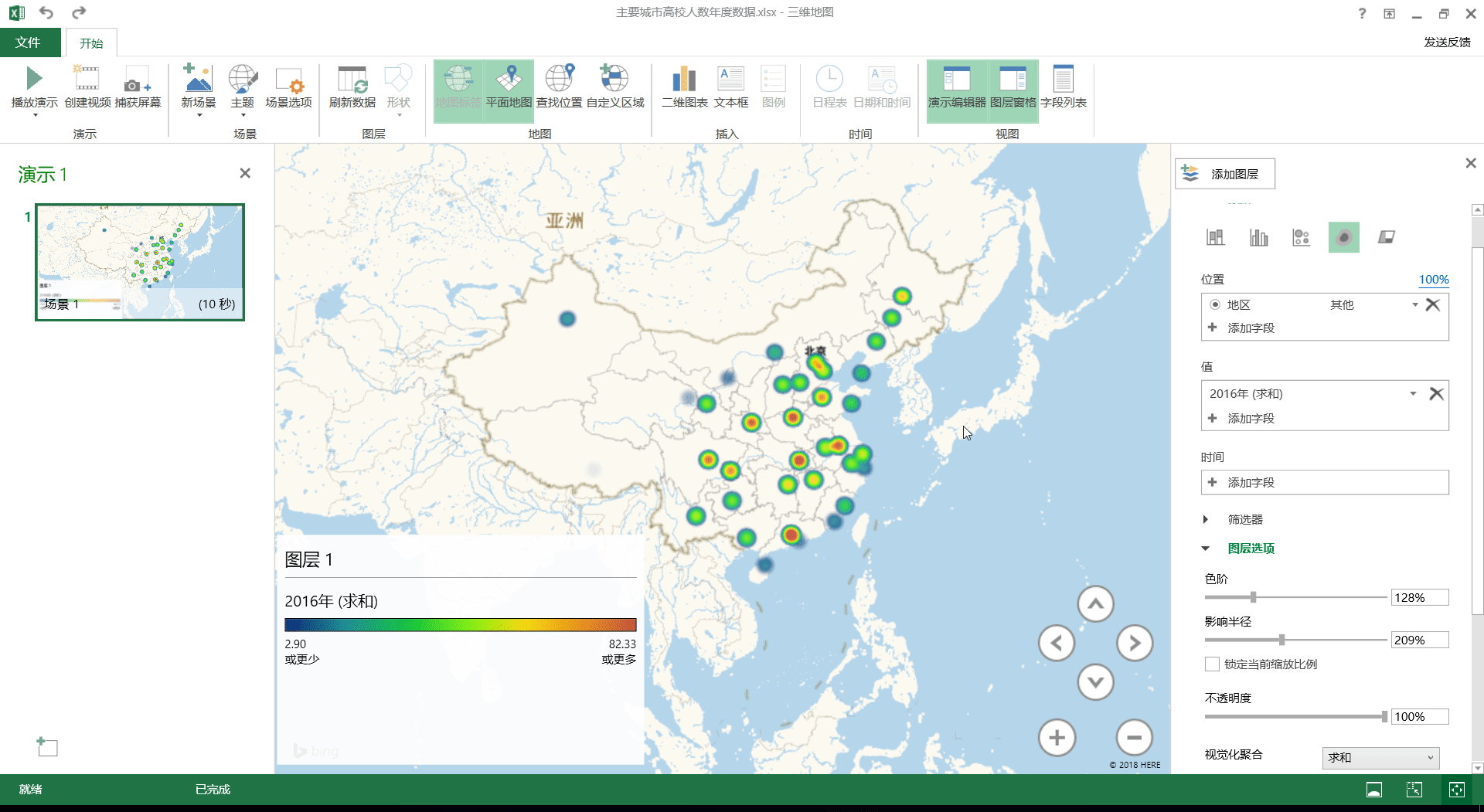文/刘斯奋 林岗
▶ 大道至简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万物的体悟
刘斯奋:文风,即如何运用文字进行思想和审美表达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个问题历来都受到重视。而简易明了的方式,则尤其受到推崇和提倡。
其原因,正如孔子在《易·系传》里指出的:“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孔子之所以这样提出来,是因为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一门唯物务实的学说。它“不语怪力乱神”,主张人生的目标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经世致用”就成了儒家对学问的根本态度和要求。而要“用世”,就必须使自己的主张做到简单明白,以便世人“易知”“易从”。

这样一个大原则,对中国文风的影响可谓直接而深远。孔子本人“述而不作”的《论语》固然是“大道至简”的范本,而后世一切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文章,都无不遵从这个传统。
一旦偏离这个传统,滑向繁琐和故作高深,就或迟或早都会受到严厉指斥和纠正。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到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莫不如此。
应当指出,这里的所提倡的“简”,绝非简单浅薄,而是基于对事物本质的精准把握。远的不说,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出现许多具有很强概括力和号召力的至理名言,无不是准确抓住事物的本质,将精深的道理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林岗:文字表达思想和事物应当尚简,这既是中国固有表达方式的要求,亦渗透着古人对自然社会万千事物的体悟。古人正是从大道至简中领悟到用文字表达这个至简的大道亦需要采取尚简的原则,以简为原则规范其文风。
失去了尚简的文风,亦同时远离了至简的大道。繁文缛节、滔滔不绝的文字洪水一定淹没了至简的大道,淹没了事物的真相。
古人大道至简的认知,是从自然万象中,从人类社会万物流变终极至理的反复体悟中形成的。岁月迁流无非四季,周而复始;农耕无非谨守节气,不背四时。至于人间万事万物,将之视为一个过程,小到人生,大到朝代,其始必简,其末必繁。造作无端,不知节制,繁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离失败不远了。
盖简先于繁,物先简而后繁。如果没有高度自觉的尚简意识和觉悟加以节制,保持事物原初生气勃勃的状态,必然失去初心,加速滑向繁琐、臃肿而衰朽。
文明史上有无数案例,始简终繁,因繁而衍生出无以救治的衰朽。这些惨痛的教训迫使古人领会如何保持事物原初状态的有效原则和方法,而尚简就是这样经验归纳的结晶。包括我们已经谈论过的中庸,也包含有相同的含义。
如何使人间事物能长久,这是古人念兹在兹的老问题。论中庸,期望事物达到合理的平衡的状态,平衡则能长久。简与繁也是如此,需要平衡,但这个平衡并非绝对50%对50%,它需要因应具体时代和需要去变化。因为尚简是针对过繁走入了死胡同而言的,并非抽象的简、越简越好的意思。

古代文论的文和质一语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质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于简,而文对应于繁。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虽讲做人,但也可用于论文。孔子不否定文,但显然认为质更重要。缺少了质,再怎么文也实现不了其功用。
均衡状态当然是最好的状态,但历史上却很难做到完美。
西汉初年刘邦的《大风歌》就简洁有力,直抒胸臆,表达粗旷,只是略嫌过简。待承平了一段时间的武帝时期,文风逐渐变繁杂起来。大赋的铺陈形容,连篇累牍,是出了名的。董仲舒《春秋繁露》里面讲天人感应那套经学意识形态,也是非常繁琐庞杂。文风由简变繁反映了从生气勃勃走向固化的社会变迁。
▶ 要“文以载道”就必须先改变文风
刘斯奋:是否可以说:文风的变化其实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变化紧密相关,与社会面临的矛盾变化相关?当国家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必须集中全力处理解决时,简单明白、易知易从的文风就会被大力提倡,受到推崇。
而且在危机摆脱后,国家和社会进入目标明确、思想认识总体一致的上升发展阶段,这种文风还会继续得到保持。但越过这个阶段之后,社会慢慢失去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变得停滞不前。文章的功能也从用经世致用,更大程度转向标榜才情学问,文风也转向浮华和繁复。
这种状态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成果也不能一概抹杀和否定。不过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重难返,日趋尖锐。统治集团于束手无策之余,也变得更加因循保守。
结果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之下,弄出一套严格的标准化文体——八股文,规定题目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以此扼杀一切可能动摇现存统治格局的离“经”叛“道”思想。
这就不止是浮华和繁复,而根本就是提倡确立一种僵尸式文风了。至于清朝统治者,除了全盘继承八股文取士之外,还大兴文字狱,搞得知识阶层心惊胆颤,人人自危,纷纷转向故纸堆讨生活,埋头于对儒家经典进行一句一字的寻根究底,结果催生出一个以繁琐考据为能事的亁嘉学派。
士大夫们纷纷趋之若鹜,陷溺其中不思自拔。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爆发,以救亡图存为当务之急的经世致用文风,才得以重新抬头。
林岗:历史上繁琐文风的形成,往往同统治凝固化有很大关系。古代社会不需要科技创新。新秩序建立一段时间之后,封官受爵,盘根错节,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出路不多,只能越来越内卷化,靠的是维持安抚士人。
刘斯奋:就是要把他们“圈养”起来。
林岗:没错,就是“圈养”。用什么来“圈养”呢?当然是科举功名。一方面是禄爵有限,另一面求之者众。僧多粥少,士林内卷就不可避免,而繁就是内卷化的结果。比拼的不是见解、领悟,而是格式、文采,文风哪得不繁?
刘斯奋:这是为了让这些儒生整天为眼前的利益疲于奔命,以免他们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无事生非。
林岗:为了秩序的稳固,功名利禄是有正面意义的。应当承认,承平的年代问题不大。一旦到了四方多事的年代,问题就显露出来。因为功名利禄造就的多是苟且庸碌之辈,而社会危机需要有眼光的能人。如果有眼光的贤能人物不能带领社会,那社会就会慢慢失去活力。
东汉败于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情形,终至于让社会陷入群雄并起的局面。曹操是汉末并起的群雄之一,他面临四方多事,故要开创能人登进的局面。要举贤才,就要去除花里胡哨的招数,就要大刀阔斧破除门阀制度。曹操回归大道至简,他提倡简洁明了的文风,并且身体力行。汉魏之际,社会动乱,时势艰难,但“汉魏风骨”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尚简确实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但凡政治上有生气,文化上有创新的时期,大都去繁尚简。一时的附庸风雅是有的,但却不影响大局。吴晗《朱元璋传》提到朱元璋嫌弃儒生士大夫写的奏章过于繁琐,讲不到点子上,三番四次要求文风要简洁不要废话。

刘斯奋:朱元璋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当然更加厌烦这种繁文缛节,一句话能讲清楚的问题偏偏要讲十句。
林岗:初唐宫体诗风盛行。唐太宗君臣写诗继承了齐梁宫体诗风,辞藻华丽,堆砌浮词。但陈子昂登高振臂,呼吁去除陈言,直抒胸臆,回复“建安风骨”的刚健诗风。
诗风尚简的变化及至中唐伸延到古文。又有韩愈、柳宗元站出来倡导古文运动,使先代古文重新焕发生机。韩愈更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唐代涌现不少经学家,经学家们比拼注释,如孔颖达《五经正义》,经中一字,注释千言万言。学问是有了,但又如何?关键是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
刘斯奋:也就是它不能做到经世致用,所以古文运动要“文以载道”就必须要先改变文风。
▶ 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把繁简两者兼顾
林岗:韩柳古文运动的确有很强针对性。当时臣下奏章和公文沿用初唐以来的骈文格式,堆砌虚言,文不及义。韩柳举起古文这面旗帜就是为了改变朝廷和士林的文章风气。
繁的文风之所以自唐代开国以来一直持续,当然得益于太平盛世,社会不见危机。但经安史之乱,暴露出问题。像韩愈这样的儒学之士,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而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体认深刻,力倡古文,翻转士林文风,由繁归简,并将文章之道提升至新境界。
刘斯奋:按你的说法,文风的繁简是和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当文的目的是为了载道,是为了经世致用,那么它的文风必定是简的。
林岗:是的,生气勃勃的时候必定是简的。
刘斯奋:但到了社会停滞,没有什么进步的需求也没有什么危机的阶段,文就变成一个用来打发时光,博取浮名的工具,它自然就变繁了。因为只有变繁,它才能显摆学问,卖弄花巧。
林岗:繁琐文风的历史新高,我觉得是清朝。
刘斯奋:典型的就是乾嘉考据学派。
林岗:讲到乾嘉考据学派,当下不乏认同,肯定的声音也很强烈,你怎么看?
刘斯奋:我觉得是否可以这样来看:传统文化的崇尚“大道至简”,其实是中国人基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用整体的、综合的方法来认识把握事物,属于宏观思维。
这种思维方法有利于运用全局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去谋划事功,有利于在面对纷繁复杂局面时,分清全局和局部,主流和支流,从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作为中国重要文化传统的这种思想方法,至今仍旧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没有失去其光芒与价值。
西方文化侧重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用的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是一种微观思维。这两种方法其实各有长短。

不过,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微观思维因为更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故而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显示出它的优势。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无疑是思想方法一大突破。而亁嘉学派的治学目的虽然全不在此,但运用的方法却与此有暗合之处。或者算是一种歪打正着吧!它今天重新受到学界一些人的推崇,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全是单一的类型也是不够的,宏观把握之余,依然需要有人去把一些发现发明、一些真知灼见去细分和细化。这种梳理也属于一种文化的积累,其价值必须充分肯定。
所以,繁与简其实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功能,问题在于它们应用的时机和地方。文化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把两者兼顾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引进西方的微观思维方法之后,我们传统的以简驭繁、整体把握事物的思想方法,在多大程度受到挤压、排斥甚至遮蔽?特别是迄今对学术界的文风形成,其影响又如何?
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打破禁锢,引入了西方各种新潮的研究方法、各种高深莫测的理论。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是“饥不择食”,迫不及待地对这些舶来品顶礼膜拜。
但是不少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潮理论,其实是出于应付学术立项的资金考核而刻意炮制出来的“成果”。我见过某个曾经暴得大名的所谓理论家,阐述问题的时候,无边无际地漫天撒网、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但其结论只不过是“人必须吃饭”这类ABC的道理。这种“学问”固然绝对不是大道至简,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的逻辑实证方法,而是典型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 被近现代历史所塑造的“学生”心态、解构心态
林岗:赶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时髦的确是个严重问题。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是中国的先生,中国是西方的学生”的定见越来越获得普遍的认同。
一百多年失败和衰落的历史让国人烙下深刻的观念印痕:现代化是单向度的,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只要按照“老师”走过的路,“学生”再走一遍,必定能达到“老师”的国强民富。中国现代革命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所感召。这两者和从前说的西方虽不是同一回事,它们也是欧洲的产物。
总之“学生”的角色和“学生”的心态被近现代的历史实践所塑造、所加强。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作为后起现代化国家因而处于“学生”地位的历史合理性,问题是这种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副作用,这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如果我们无法摆正西方的位置,也同样无法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西潮的时髦、教条的时髦,相当长时期通行无阻,首先是我们无法摆正西方的位置,自己也因此无所措手足,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就是典型的症候。
二战之后,欧洲的人文学者反思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的原因,灾难之后有人想问题,这很正常。就像“文革”过后我们也反思一样。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搞错了。反思启蒙、批判启蒙成为欧洲战后主要的思潮。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左倾激进思潮应运而生。
断症对不对姑且不谈,只说这些后现代思潮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有破无立,有批评无建设。好像把启蒙大厦解构了,问题就自然没有了。这和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很不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纸上学问。只会告诉你启蒙错了,启蒙除了导致禁锢,毫无意义。当你问它正面论述是什么的时候,哑口无言。后现代的思想任务其实在解构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学问到此为止。
这种围绕自身打转的纸上学问,恰逢思想解放、国门打开的时候一窝蜂传进来,凭着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师生幻觉”,便以为这些是西方最为时新的文化理论,趋之者若鹜,导致如今学问界充斥着过多空论。
事实说明,当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热情,被“师生幻觉”所遮蔽,借用欧美后现代思潮的观念、新词、思路来研究学问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生存在它们的阴影之下。
后现代解构启蒙,我们解构什么呢?解构古代传统,解构新文化,解构近现代史,等等。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一问,它们是否值得解构呢?解构游戏真这么好玩?
解构思潮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当代作家,不少作家以解构为使命,以解构心态面对历史题材,凡事以解构为先,解构近现代历史事件。例如土改本是中国现代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打破宗法制度,解放农民所必经的一步。但文学的呈现只剩下惨酷、灾难和无理性的呈现,令人遗憾。
刘斯奋:它是从物质上摧毁宗法制度的基础。
林岗:作家本来应该站在自身认同的立场看历史,然而赶了解构的时髦就不这么做了。丢掉了自身的立场,其文学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极其有限。
刘斯奋:只是盯着一些具体的例子,孤立的细节。
林岗:将土改戏剧化来呈现,突出其不尊重人性一面。历史主义没有了,一切都戏化。解构主义奉行相对主义,为否定而否定。我认为是比较糊涂的。
刘斯奋:它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以无目的为目的。
林岗:没错。文学上为写而写,学术上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共同认可的就是绕圈圈的纸上逻辑。
▶ 发表即弃的洋八股和土八股相结合的杂交物
刘斯奋:谈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学问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一种是乾嘉考据式的学问,我们的文化所流传下来的大概也就是这两种路数。而且可以看出,简是适用于经世致用的,大道至简主要指的的就是这个方面。
同时,我们的文化历史上也存在着如经学、考据、梳理细节这条路数的学问。这两条路数的学问各有其功能和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一句大道至简就否定另一方。这样,我们对大道至简的理解就会更为清晰。
而近代以来,像你说的由于被西方所遮蔽,事实上我们连乾嘉学派的这种实证作风都抛弃了,也就是把认真考据再得出结论的作风给抛弃了,造成如今内涵异常空泛的现象。这类对文风的不良影响在近代有其历史渊源,但近几十年来尤为严重。它们对文风造成的弊病,我与几位有同感的朋友曾经总结了以下几条:
第一条,以艰深文饰浅陋。一个浅显的问题,它刻意弄得隐晦曲折;没有真知灼见,却满篇生搬硬套的外来名词术语;加上颠三倒四的语法,让读者头晕目眩如堕五里雾中。这种下决心让人看不懂的文风影响尤其恶劣,为害极其巨大。
第二条,以抄袭冒充研究。它不下苦功去深入钻研,利用现成的数据或别人的文章成果,东摘一段西抄一节,改头换面、颠倒次序地拼凑起来,便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科研成果。一旦蒙混过关、名利到手便窃幸得计、乐此不疲。为学如此,实在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
第三条,以繁琐支撑空洞。将一个常识性的论题放大又放大,分隔又分隔,叠床架屋、堆砌引文,美其名曰追根溯源,一网打尽。实际上是以杂碎的材料来掩盖他判断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空洞,打肿脸充胖子,藉以吓人。
第四条,以模式扼杀创造。把国外自然科学论文中的若干规矩变本加利生搬硬套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形成固定格式。其可笑者,例如规定引用文献的数量,又规定洋文献和本土文献必需各半。这种模式实在莫名其妙。只要将现成的结论加上一堆废话,好像机械制造一样填充到这个模具里面,就成为了学术成果。在这种模式的统制下,独创之见遭到扼杀、论述简明受到排斥。其荒谬背理,较之科举八股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条,以矫情代替真情,以低俗排斥高尚。明明对生活麻木不仁,远离老百姓的痛痒,了无真情实感,却偏偏要故作深沉、大发感慨。不以真善美导夫先路,反以假恶丑颠倒众生,为了吸引眼球不惜肢解文法、灭裂文字,词语尘下、意识卑鄙。
所以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我们自身有八股的传统,另外加上西方那套思想的引入,于是造成当下部分学界的文风如此恶劣。如今做学问的人也清楚,他们的成果除了自己所在的小圈子以外,越来越难以引起更多的关注。
如果这种状态再不改变,那么它对中国文风的影响真的让人堪忧。因为它比乾嘉学派还等而下之。目前的状况是否有所好转不得而知,这些是我由以往的经验得出的看法。
林岗:更有甚者,发表即弃。可能心知肚明,眼不见为净。
刘斯奋:他们只要发表了文章,拿到了科研基金,钱到了手就阿弥陀佛,完事大吉。
林岗:这些文章就像古人说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就可以扔掉。刚才你说的那几点十分中肯,那是一种洋八股和土八股相结合的杂交物。
▶ 民族复兴的时代如何继承“大道至简”
刘斯奋: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废除土八股的任务尤未竞,现在还加上了洋八股,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状态。按理说,我们国家早已走出鸦片战争的深渊,步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十分需要真正经世致用的学问。
而在重新认识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大道至简”——这个蕴含古人智慧的把握世界和真理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再三深思的。
林岗:可以总结为两条原则:一个是坚持大道至简的原理,另一个是辅之以经世致用之心。
刘斯奋: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
林岗:希望能借此扫清鸦片战争以来的阴霾。
刘斯奋:希望广大学界人士能够认识到,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只在乎物质利益,这不单单是文风的问题,而是士风的问题。
林岗:要扫除阴霾,首先要求知识人自身有所觉悟,要看到这个时代在思想创见方面比上一世纪能够提供的空间更为广阔。长期笼罩我们眼前的西方神秘的面纱由于民族复兴和国运盛隆正在一层一层褪去,固有文化传统的应有形象也逐渐显露在我们的面前。站在今日的时代节点,文化创造的前景更加光明。
刘斯奋:是的,以前想象所触及不到的,现在已有条件。
林岗:以往西方有如庞然大物堆立面前,一度遮挡了我们的视线。到了今天,这个庞然大物正在塌缩。不管是它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原因,总之这个变化使我们有可能看清从前看不清的风景。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是生活在任意时代的人都能逢遇到的。
刘斯奋:作为个人,最幸运是生逢其时,否则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既然命运正在发出殷切的召唤,我们如果还不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施展抱负和才智,去开创一套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学术新天地。那岂不是白白来人间走了这一遭!

林岗:当然,这个问题也有悖论的一面。美景只会出现在能够洞察美的眼睛里,并非人所共见。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的“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有些东西取决于个体自身,需要洞察到诸如文风繁琐的弊端等问题,这样才会主动扫除阴霾,看清眼前风景。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孙 磊 朱绍杰
制图 | 蔡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