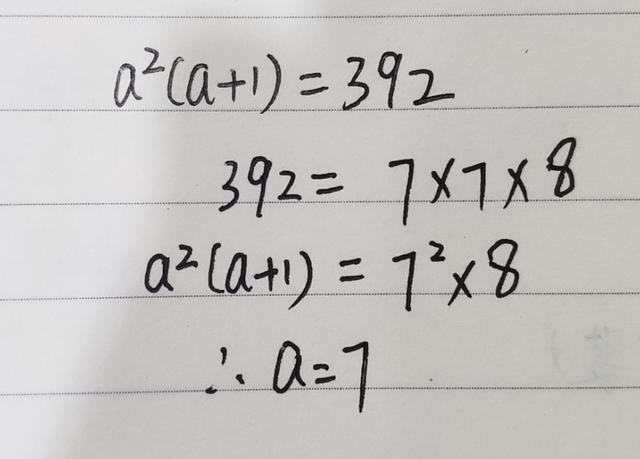“需要最近本社区业主的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吗?让人怵目惊心的是,他们所提供的电话号码、住户地址甚至身份证号码都十分准确,连户主的户籍私密信息都暴露无遗。
最隐秘的家庭信息被全部暴露!来自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一

2015年,山东省淄博市。
“铃铃铃……铃铃铃……”
王女士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陌生号码,崩溃地想把手机丢出去。这已经是她今天收到的第8个陌生电话了,无一例外地都是家装方面的推销。自从她和老公在淄博某小区买了房子后,他们就被各式各样的推销电话“轰炸”。如果说个人信息泄露是平时自己留信息时不注意造成的。那么,来电者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购房信息以及需求的呢?
买卖小区业主信息?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故事开头的王女士刚买完房子就不停地被各类有针对性地推销电话骚扰,她的信息早已被“业内共享”了。不仅如此,被“共享”的信息还会被进行详细分析,并被分成“三六九等”,进而要价。
检察官 王烁:
它最主要的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楼盘的新旧和档次。比如这个小区是新楼盘,那它要价肯定最高,掌握的人也少,随着楼盘越旧,价格就越低,同理,一些高端小区业主信息的要价也会略高于普通小区;再一个是看资料的完整程度。有的资料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资料信息非常全面,除了姓名、电话等基本信息外,还有你购房的平方数、什么方式付的款、首付多少贷款多少、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都非常全。
如此隐私的内容被放在网上公然售卖,业主的家庭状况公布于众目睽睽之下,被用于推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信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掌握,特别是很多时候,白天家中只剩老人或孩子,那不法分子是不是就有机可乘,而一度嚣张的“精准诈骗”是否也和此有关呢?
看到这儿,让人实感愤怒。可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属于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郑建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开展“业务”的呢?
检察官 王烁:
郑建是这样供述的,他说:他买来资料后,就从互联网上搜了淄博装饰群等QQ群申请加入,加入之后就在上面发帖卖这些业主信息。有时候也通过淄博旮旯网、天涯社区论坛、淄博信息网等网站论坛发布信息卖业主资料。
有人购买后,郑建就把事先拷贝在优盘里的资料,通过qq、微信、发短信等方式传给买家。这些购买的人群多是房产相关行业的销售人员,业绩在身,想出了这种“歪门邪道”来拓展业务。这些资料大多以小区为单位进行买卖,一个小区的业主信息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视情况而定。
信息发布后,郑建就坐等客户上门了。此时,本案中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晶出现了。
2014年7月的一天,纱窗店老板王晶打通了郑建在网上留的电话,表露出自己想要购买一些用户信息的意愿。
检察官 王烁:
王晶是这个案子中唯一一个不是做家装销售的人,但他也是这起案件中买卖个人信息数最多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纱窗店的老板,店铺也具备一定规模了,自己并不缺钱。
当天下午,郑建便拿着拷有数十个小区业主信息的U盘来到了王晶的厂子。
检察官 王烁:
当时他俩谈完之后,郑建让王晶把他U盘里10来个小区业主的信息都拷贝去,而后王晶给了他500块钱。根据郑建的供述,他知道王晶肯定和装饰公司也有联系,能弄到小区业主的资料,所以在后来郑建也主动问王晶要过别的小区业主的信息。
王晶的经济条件不差,店铺也能够正常运转,那他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经营呢?
检察官 王烁:
王晶在网上看到郑建发布的相关信息,就觉得好像买了这些信息就能多拉拢一些客户,多挣些钱。虽然知道买卖信息这个事不好,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
显然,王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被捕之后,他痛哭流涕,反复说着自己所为的“理由”,希望能被从宽处理。
那么,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王晶买来的“客户”信息,给他的生意带来帮助了吗?
检察官 王烁:
在讯问他的时候他就表现的特别后悔。他说“打过电话去,别人一听是推销的立马就挂断了,有的还骂他,效果特别不好”。他正准备把这些人都拉进一个微信群里进行业务推广,还没实施就案发了。
截至案发,犯罪嫌疑人郑建共存储公民个人信息23160条,利用电子邮箱共发送、接收公民个人信息4296条。犯罪嫌疑人王晶存储公民个人信息37867条。五名犯罪嫌疑人共涉及储存、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多达106873条,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造成极大的社会隐患。
三
本案系淄博市公安机关查办的第一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由于没有先例,案件的审查起诉遇到了重重阻碍。
摆在公诉人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对“个人信息”范围认定。在本案中,被告人获取的小区业主信息中,有一部分信息仅有电话号码,那这样的信息可以算作公民的个人信息吗?刑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予以认定又有着哪些标准呢?
检察官 王烁:
公民个人信息是和公民个人直接相关的,能够反映公民局部或者整体的特点,具有法律保护价值。包括公民的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住房情况等。
既然电话号码属于公民个人信息,那是不是可以依照这一点给他们定罪了呢?其实不然,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手段包括窃取和其他非法手段,而本案中各被告人都不存在窃取的行为。那么,这一法条中“其他非法手段”具体是指哪些手法?本案中,各被告人购买、互换、索要等手段是否可以算作本罪中的其他手段呢?这一点关系到本案5名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检察官十分谨慎。
检察官 王烁:
所谓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是指窃取之外的方法没有法律根据而获得,即排除了一些诸如为了国家安全或者侦查机关为了案件侦破等合法事项而采取的技术手段调取、获得信息行为的非法性。其他方法必须违背了信息所有的意愿或真实意思表示、信息获取者无权了解、解除相关公民个人信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社会的公序良俗。其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互换、索要、从其他电脑中私自拷贝等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信息所有人的意愿。所以我们认定本案5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中的“其他非法手段”。
2009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将出售、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但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对本罪的具体认定予以规范。《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增加了“情形特别严重”情形下的法定刑档次,但针对涉及到审判实际中的焦点——“个人信息”和“情节严重”等的认定标准问题仍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的适用存在较多的争议。
那么在本案中,各被告人的情节是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构罪标准呢?
检察官 王烁:
因为在本地区没有已判决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结合了全国各省市该类型案件的已判决案例、查找国内外法学专家对该罪名的理论学说、通过科室讨论,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是获取信息数量较大,或者获取信息数量次数较多;二是利用所获取的信息从中获利,数额较大;三是获取信息后用于非法犯罪活动;四是给其他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五是其他一些与他人互换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大量传播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以此作为标准,我们认定本案的被告人属于情节严重。
最终,郑建、王晶二人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其余3人也均被判刑。
案情之内的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案件之外暴露出的问题却远没有结束。此时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关键词,仍会发现有类似现象存在。如今,需要我们登记个人资料的情况越来越多,涉及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但如果每个人都不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此案因为网友的举报而曝光,但还有一部分不法分子仍潜藏在暗处,偷窥着公民的个人隐私并利用它谋取利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提高警惕,在自己不购买、不传播他人个人信息的同时,对类似不法行为进行及时地举报和揭发。
与此同时,如何从根源上斩断畸形的供求利益链,整顿市场纪律,杜绝类似行为的发生,也是监管部门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并且,办案人员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及对类似案件的判决也将为法律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供方向。
(注:本案中除办案人员外,其余皆为化名,图片部分源自网络)

播音、制作|刘璠
撰稿|王蓉蓉 刘璠
监制|徐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