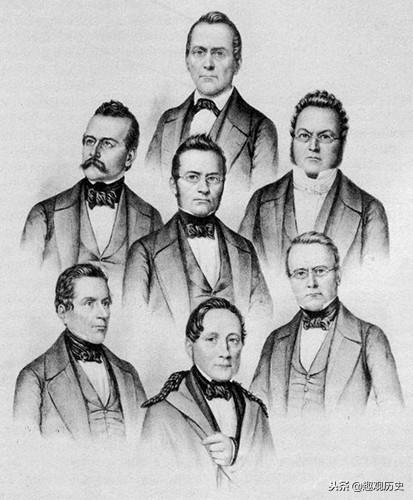当今许多人都知晓一项文艺领域的常识:「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但是,在大量叙事的灌输下,很多人也不清楚究竟接受到的文艺作品,是否为本来面貌。试想:倘若有朝一日,竟然发现课本上印的、传媒上播放的、博物馆展示的著名画作《蒙娜莉萨的微笑》,根本不是达芬奇的原始手笔,而原作与记忆印象又相差甚远,那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冲击呢?又或是无伤大雅、一笑置之,弃真相于不顾,继续沉浸于脑海中建构许久的「美」呢?
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中,就有这样一项特殊案例,那便是《黄河大合唱》。
由光未然(本名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诞生在一九三九年的《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著名音乐作品,体裁庞大、政治性质强烈,又以「黄河」为叙事焦点,凸显出鲜明的剧情推进效果,的确是一部出色鸿篇。它有包含混声合唱、女声合唱、独唱、对唱等不同形式的八个乐章,相较于同年问世、亦是冼星海作曲的《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作词),更加集中表现音乐的听觉美感,也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于不同意识形态环境下被唱响。称《黄河》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的代表作品,应不为过。
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包含本人)长篇累牍地考证、介绍《黄河》的版本演进,但人们经常忽视(或未知)《黄河》的样貌如何改变,更不晓得今时大众所聆听、习惯、传唱的《黄河》,几乎脱离了冼星海原始意图。甚至,后人所创造出的关于《黄河》的诸般种种诠释,已掩没了当年被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其所希冀创造的某种艺术追求。
时间倒流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因武汉沦陷,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自陕西宜川壶口下游,东渡黄河,转进晋西南吕梁山游击根据地,过程中抗演三队成员见识到黄河渡船的船夫号子、沿途沦陷区的焦土、吕梁山游击队的战斗场景,除肩赴文艺宣传任务外,还须抵抗日军向游击队根据地攻击的炮火,在复杂险难的地型不断转移。据首演《黄河》的指挥邬析零回忆,抗演三队在陜北靠近延安不远时,光未然因坠马受伤,被送至路程七百华里的边区和平医院,再渡黄河,此时光未然萌生将这一段见闻转化为文学的想法,便蕴酿长诗《黄河吟》的写作。在《黄河吟》创作完成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冼星海《生产运动大合唱》完稿后的五天,因参加抗演三队决定在西北旅社举办歌词朗诵会,冼氏接触到光未然《黄河吟》诗作,有意为之谱曲,即后所谓之《黄河大合唱》。
据冼星海日记,《黄河大合唱》初次谱曲的时程很短,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始动笔,三月三十一日完成,仅费时六日;但期间冼星海健康不佳,自叙:「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身体不好,常睡午觉,他们还以为我是装做的不去开荒!」「身体不好、伤风头晕……」四月十三日晚间七时,陜北公学在延安召开第一次音乐大会,除吕骥、光未然先后发言,其余则是由抗演三队、鲁迅艺术学院及抗日军政大学联合组织的文艺表演,节目内容包含全体合唱《中华民国国歌》,鲁艺演出合唱曲目《船夫曲》《打到东北去》,抗大八人文艺工作团演出《新山歌》《延水谣》《在森林中》,鲁艺由冼星海指挥演出《生产运动大合唱》,抗大五大队演出《军民合作》及《太行山上》,最后才是抗演三队首演《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首次问世,其实是相当简陋的样态,由于延安缺少乐器,只好把能见到的乐器都用于伴奏,编制包括:竹笛、口琴、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主板、木鱼、铙钹、铃、鼓锣、堂鼓、钹,据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献记载,当时甚至使用汽油筒或大缸制作低音乐器,显见条件克难。又据冼星海日记所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的《黄河》首演,其实有些瑕疵,主要是《黄河怨》的独唱走音,所以「给观众不好印象」,而现场观众的对《黄河》的初步体验,是「觉得很雄伟」。四月十六日晚间,抗演三队又于「生产运动总结束晚会」中演出《黄河》,冼星海日记称:「除女声独唱不十分好外,其余都很进步。」随后的五月十一日,为纪念鲁迅艺术学院创办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百余人演出《黄河》,这才出现作曲家满意、认定为「相当成功」的表现,且由于演出结束后,在场观演的毛泽东、王明、康生等延安党政高层,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并「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才使得《黄河大合唱》后来的重要地位,奠下基础。
一九四零年,在《黄河》已于中国各地(包括陪都重庆)唱响之后,曾有两次座谈会讨论该作品的成就,参加者包含光未然、贺绿汀、刘雪庵、李凌等,指出除了演出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外,乐器音色的搭配亦不协调,且当时许多指挥并不知晓如何处理这部作品。二零零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在艺术总监朱振威的带领下,依照《冼星海全集》所刊印的乐谱,复刻了一版延安《黄河》的演出,模拟当时乐队、合唱的演出效果,据说不少观众在聆赏时,也是一头雾水、很不适应。也可以说,《黄河大合唱》的问世,一边受到大众欢迎,同时也引发专家抱疑,甚至冼星海自己也无法回避作品的简陋状态,于是他「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并认为这种方法更加「国际化」,有利将作品推广到全世界。

画作上的冼星海
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冼星海在苏联期间,于莫斯科完成《黄河》的交响版本配器,并将其称为「交响曲大合唱《黄河》」,编列为冼氏作品第七号。这也是人们所谓「莫斯科版《黄河》」。这个版本的配器十分「魔性」,有不少和声、织体的运用脱离作曲常识,且频繁转调、音域过高,使得演奏(唱)的难度大幅提升,且有些音响效果并没那么悦耳。早年间,学界多以冼星海在外困苦、病痛缠身,作为作品新版本效果「奇异」的推脱之辞,但又矛盾于「人民音乐家」的作品岂能有「错」?于是这份莫斯科版《黄河》稿件回到中国后,未能经常演出,尘封许久。一九五零年代,李焕之曾试图简化莫斯科版《黄河》的织体设计,编写出一版谱稿,并曾录制唱片、电影;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因《冼星海全集》的编纂需要,李焕之再度将莫斯科版《黄河》作有限度的调整,并交由上海乐团试演。据说,当时演出虽有安排正式录音,但录音母片被有关单位要求不能公开、唱片无法发行,所幸有一份风衣录音流出,人们才得以稍微认识冼星海作风。
幸好在一九五一年时,莫斯科版《黄河》的手稿被影印成辑,小量发行二百册左右,作为当时中苏文化交流所需的代表作品,而我也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了这份手稿复印件,方能开展莫斯科版《黄河》的校订研究,成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二零一五年五月,上海爱乐乐团在张亮指挥下,联同上海广电合唱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台湾新节庆合唱团,假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原版《黄河大合唱》,这是自一九四一年冼星海配器完稿以来,七十四年首度完整的呈现。虽然,部分观众在乐曲中出现的多处不谐和音响及花腔中,仍有些找不着北的体验,总觉得听到一个不熟悉的《黄河》,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最后十几把铜管、十几架小军鼓齐鸣的震撼效果,还是很能吸引观众掌声。
至于我们现在听到的《黄河大合唱》,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说到一九五零年代李焕之改编的版本,虽曾因唱片、电影的发行,流行一段时间,但很快地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缘故,《黄河》陷入了难以演出的境地。「文革」期间,革命文艺当道,「样板戏」成为主流,《黄河》等一系列抗战时期、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作品更是被冷落了。一九七零年前后,受江青的文艺思路、中央音乐学院大字报影响,以殷承宗(时名「殷诚忠」)为首的中央乐团创作小组,开展「留曲不留词」的创作方向,将《黄河大合唱》的部分旋律,改造成如今众人皆知的《黄河》钢琴协奏曲。这部组曲式的钢琴协奏曲,在当时被列入第二批「样板作品」中,除了乐师、独奏家、钢琴的倾情演奏以外,舞台上还须悬挂毛主席像,以及同时播映与乐曲内容相对应的字幕。
时届一九七五年,北京文化界为突破「文革」文化环境的诸般限制,便蕴酿一场关于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一些文献中提及,这或与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女士听从李焕之的建议,曾致信毛泽东表示对《黄河》等作品遭冷落表示不满,有所关联。几经波折,由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负责,中央乐团创作组施万春、田丰、陈兆勋等人执笔配器,重新为《黄河大合唱》编曲,并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首演于北京民族宫礼堂,名义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参演团体有中央乐团、中国歌剧团、新影乐团、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少年合唱团,由严良堃指挥。随后演出多场,获得广泛热烈反应,得到大众极高评价。中央乐团版本《黄河大合唱》,一改原作品复杂的配器织体,以「三化」思维(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将原作品的主旋律,配上颇具功能性质的伴奏和声,使乐队处于「伴」的地位,与冼星海原作品「交响曲大合唱」的思路略有不同,甚至部分配器思路明显源于《黄河》钢琴协奏曲的设计。关于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的产生历程,以及期间的政治情况,于一九七九年被改编成电影《怒吼吧!黄河》,公映于世。

电影《怒吼吧!黄河》海报
而一九七五年完成的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其实欠缺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直至一九八七年为当时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方由施万春补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演出亮相。但施氏补写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除去开头琵琶独奏几个音形以外,其实整章的旋律、和声、织体,已跟原作没太大关系,这标准的「施万春作品」,多年来夹杂在其它同被改写的乐章中,被视为「冼星海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虽然包括严良堃在内的诸位乐界前辈,均认为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是基于延安首演版本编写,很能体现「原貌」,但若与一九四一年冼星海亲编的莫斯科交响合唱版本对照,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单纯。从冼星海的原始谱稿中,可看出其深受法国浪漫派风格影响,后又吸收苏联大编制交响乐的创作思维,试图打造一个印象式的演出效果。例如:在《黄水遥》中,「自从鬼子来」一句仅由女声部弱声唱出(中央乐团版是混声四部强音唱出);《保卫黄河》原本是四部渐入轮唱、层层迭加,成为在前后乐章过渡的曲目,仅作为转场式的片段(中央乐团版改为三部轮唱,经一段主题旋律间奏后,转调为混声合唱,成为完整独立的「战歌」)。又如上文提及,《黄河之水天上来》几乎扬弃原作不用,改以另人新配,强力凸显旋律而失去原本复杂的织体设计,亦鲜见演出艺团如实将真正作者的姓名署于明显之处。
除去前列所提及的《黄河》版本,还有几个有意思的小版本也应留意。
一九四九年,陈田鹤甫至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工作,由于福州解放不久,当时该校学生希望排演《黄河大合唱》,但苦无伴奏乐谱,又听说黄自四大弟子之一在校任教,便有学生将一份《黄河》的声乐简谱交给陈氏,希望能由老师编配成钢琴伴奏的稿本,为福州军民演出;而一九五零年代陈氏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又编配了《黄河颂》的伴奏。由陈田鹤编配的《黄河大合唱》钢琴伴奏谱稿,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延安首演版本加工编配、符合原貌的版本,编曲家加油添醋的地方极少,但其亦有省略《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章、《保卫黄河》仅演唱到三部轮唱止之情况,只能猜测《黄河》在一九四零年代广泛流行时,就已经成为那样面貌了。该版本目前尚未正式出版,原始手稿一直由陈氏后代细心保存。
又「文革」之前,瞿维亦曾将《黄河》编为钢琴伴奏谱稿,并在「文革」后修订出版,虽然这个版本被严良堃评价为「演出效果不顺畅」,但很长一段时间,这份谱稿却是在香港、台湾地区唯一能见到的《黄河》乐谱出版品,港、台有些小合唱团曾利用这份谱稿,一圆唱响《黄河》之愿。
那么,既然《黄河》有那么多种版本,各有千秋,有没有人想到来烹一锅乱炖,搞个大杂烩呢?如果把所有版本的优点集中在一起,岂不无敌了?二零零五年,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在官美如主任的主导下,真的召集了一批作曲研究生着手这项工程,试图集各家之长,达完美之成就,这就是所谓「室乐伴奏合唱版本」。该版本的伴奏以双钢琴为基础,搭配打击乐、少数独奏乐器,神似室内乐版《布兰诗歌》。但若仔细观察,这个版本其实就是中央乐团版、瞿维版的杂交产物,据工作小组当事人的记述,合唱团早已使用瞿维编配的谱稿排练,于是声乐部分只能依瞿维版照抄,而伴奏方面主要参考中央乐团版的设计,于是原本企图以学术考据权威诠释的雄心壮志,也成为一滩泡影了。除了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以外,我还未曾看到有其他艺团演出该版本《黄河》。
二零一九年是《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周年,与二零一五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样,海内外都有不少演出《黄河》的音乐会,有些演员阵容坚强、演出质量确实挺高,但几乎选择了一九七五年出现、改变原作风貌的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作为演出曲目。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试着思考:我们纪念一出作品、一位作曲家,到底是要纪念些什么?是纪念一个人的创作伟大吗?是纪念作品的历史意义重要吗?那为何不拿那个人本来写的,而是找一个「代笔」来偷天换日呢?
但我还听说,近期有艺团为纪念作曲家施光南冥诞,托人写了一部「歌剧《施光南》」热闹上演,希望让观众透过该剧了解作曲家的伟大之处,但却不是让观众直接欣赏该作曲家的作品。(更何况施光南也写过两部歌剧呢!)这样想来,虽然现在能聆听到的《黄河大合唱》不完全是冼星海原作,但好歹留了点本来旋律下来,冼星海的命运还是好上一点了。且听且珍惜吧!
仅以此文,纪念《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周年。
本文刊登于《三联爱乐》总第236期(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