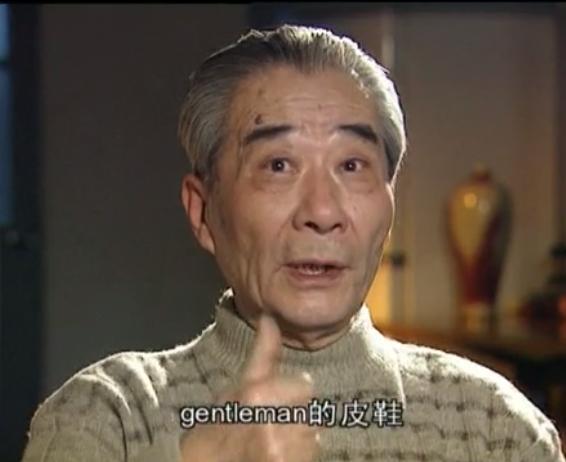鲁迅的《孔乙己》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其实,鲁迅写出这么一段,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周作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窃书的故事》刊在《新民报晚刊》上,其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鲁迅先生和当时一位文人之间。
京师图书馆里藏着一部宋板书,但是,却规定“此书一概不外借”。大师因为在校书上颇有建树,于是,图书馆就特意腾出了一间清净的房间供大师校阅。因为图书馆方需要一人与大师交接书籍,于是,这一任务就交付给了时任科长的鲁迅。不几天,大师又放话,要来馆中校书,通知让人去交接宋板书,于是,此事依然是鲁迅亲理。
不过,这一次这位大师却彻底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坐实了“窃书”的罪名。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鲁迅到的时候,只见大师已经收拾妥当,只等鲁迅来收书。鲁迅一到,大师就带着佣人起身要走。鲁迅这时突然留心打开楠木盒子检视,谁知,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大师一眼看出了破绽,于是,便责骂随行的工友没有把书放好。工友随即伸手到网栏里去取宋板书。至此,鲁迅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收了书离开了。
周作人又在文中补充说:此后鲁迅每逢回想起过往种种险象,仍然对这件事心有余悸。倘若,他当时没有仔细检查一眼,恐怕他现今还在遭受失书的罪责。从那之后,鲁迅就最痛恨这位大师,因为险些上了大当,从此也笃定一个念头“藏书家即是偷书家”。鲁迅也在心中给这位藏书校书大师下了定论,藏书家爱书成癖情理之中,但是,为占为己有不择手段就略显卑劣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周作人杜撰的,而是从其兄长鲁迅那里听来的。

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卓彰,对他的文字世人耳熟能详,但是,少有人知道他还曾任职过教育部的科长。
当时,鲁迅下属于傅增湘——中国近代知名的藏书家,擅长校书,二人曾有一段过节。起因就是,鲁迅先生因为时遇饥荒,打算把藏书卖给傅增湘,谁知道傅增湘出了口白菜价,鲁迅一气之下不卖了,并且,还认为傅增湘行为不端,有“偷书”之嫌。
周作人在文中并没有给这位人物署名,只是根据实情给主人公贯了一个“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头衔。这么一来,对于读者而言,主人公究竟是谁也就不言自明了。甚至,连黄裳在《藏园佚事》中,也曾讲述过鲁迅与傅增湘间的故事。
痴醉藏书的傅增湘没有得到想要的古籍,反倒在鲁迅的口中、周作人的故事里、黄裳的文中以“窃书贼”的形象活泛,后世熟知或景仰于傅增湘藏书校书功业的人,听闻此事无不惊呆。不仅如此,鲁迅还曾撰文在另外一个故事中讥讽傅增湘“偷书”。

故事发生在他的工作之中,仍用他一贯辛辣讽刺的文风。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记载了一个群体欺盗案: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等,对清政府遗留的内档进行了清整。文中未出现任何实名,而是以单个英文字母代指。传言,这些英文代称并非随意选用,而是根据每个人姓氏拼音的缩写。
从史料来看,傅增湘曾在1917年之后的一两年里任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所以这个F先生不难猜测正是傅增湘。Y次长所指应是袁希涛,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在江苏组织了“义务教育期成会”,曾于1915年及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先后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曾先后多次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那么这个C参事指的就是蒋维乔。
鲁迅在文中这样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是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在鲁迅记载的这则群体盗书事件中,最另人咋舌的是:全部门人几乎都参加了,但是,惟他自己独善其身。这就恰如屈原在诗赋中歌哭,处在如此境况中的鲁迅,则现身以文字为武器,去披露讥讽故事中的人与事。
参考资料:
【《窃书的故事》、《藏园佚事》、《谈所谓“大内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