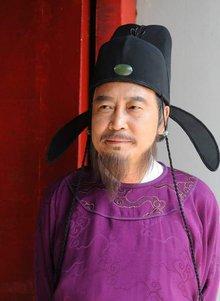在史学界流传着一句话,“二韩佐辽定天下”。
“二韩”不是指两个人,是指两个家族,其一是韩延徽家族,其二是韩知古家族。

韩延徽被视为辽太祖的“谋主”,相当于诸葛亮对刘备的意义。他辅佐了从太祖开始的四代皇帝,辽国的一切大政方针,战略指向,契丹建国初期的一切规章制度均出自其手。
韩知古曾经是家奴,因有才干统领汉军汉族事务,对于稳定前来归附汉人的情绪、安顿汉人的生活起过重大作用。他的儿子韩匡嗣最高职务达到了辽南京留守(今北京),但他对宋作战的时候吃了败仗。可是,耶律皇家都庇护他,原因是除了他和述律后情同母子的关系之外,他还是当时最高明的医生。再就是他有一个了不得的儿子韩德让。

宋太宗灭掉北汉后,挥师北上,准备乘胜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时,代替韩匡嗣守卫南京城抗击宋军的是儿子韩德让。韩德让安抚军民,调度有方,在高粱河一带和宋军决战,打垮了十几万宋军,宋太宗腿上还中了两箭,慌忙中,手下的将士拼命把他扶上了一辆驴车,才急匆匆地借道涿州逃回汴京。韩德让这些可以称得上是辉煌的政绩军功,还不重要。他入住宫帏肩负守卫皇宫,保护萧太后母子安全,登堂入室成为萧太后公开的情人才是他的主要功绩。
不要以为这是笑谈。辽景宗猝死,太后萧燕燕刚30出头,儿子辽圣宗才12岁,如果不是韩德让出面镇压反抗萧燕燕的势力,萧燕燕再有才能恐怕一时半会儿也稳定不了朝纲。后来,韩德让执掌军政大权,击败了宋朝的“雍熙北伐”,几年后,他和萧燕燕率军挥师南下,在澶州促成宋辽之间签署“澶渊之盟”,从而造成南北120年的和平局面,这是他的主要功劳。

韩知古家族的墓地,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尽管女真金朝在攻下辽上京时候,对韩知古家族墓地的地上建筑进行了破坏,但没动地下,所以,解放前后均有重要文物出土,韩知古一门基本情况通过出土文物已经搞清楚了。
韩延徽历事四朝,即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在当时一直担任辽的最高的行政长官“政事令”,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活到78岁去世,被追赠为“尚书令”。被埋葬在“幽州鲁郭”。可是一千多年来人们始终不知道幽州鲁郭确切在哪里,当然也就不知道他的家族墓葬怎样了,由于史籍缺载,韩延徽后世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韩延徽这“延辉”二字是他行于世的字号,他的字还为“藏明”,而他确切名字叫什么,辽金史专家们还争来辩去。
1981年6月6日,八宝山殡葬管理所在院里的东侧施工打地基,忽然,发现了一座气势雄伟漂亮的墓门,立即通知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发掘。

到了现场一看,墓道已经破损,在那个年代文物保护意识还不是很强,文物发掘主要配合单位施工的情况下,连墓道都没能完全清理出来,只清理出墓道门前2.9米一块地方,便打开了墓门。根据当时的探测,墓道总长为9.8米,未打开的地方有什么埋藏品就不知道了。
墓门的正面结构是仿木构的,瓦当不是单独镶配,而是在板瓦状的砖前端雕刻而成。
打开墓门,进入墓室,先是一段甬道,甬道东西两壁绘着满堂壁画,但还没高兴多久,待将电接过来开灯照看,才发觉因剥落太甚,只能隐约辨认出一些影像,所以,至今没有摹绘像样的作品出来,照相没有什么效果。
前行打开墓室门进入墓室,见墓室是用青灰色单面绳纹砖砌成,单室穹窿顶,平面呈圆形,直径3.18米。墓室上部的彩画还鲜艳夺目,洒脱精炼。
正中绘莲花,四周用八条红色弧形宽垂带将穹顶分成八格,每格内绘白色飞鹤一只,间以流云,穹顶下部四周分绘生肖象和人物十二个。

青瓷水注·韩佚墓出土
此时发现墓室大部被淤土填塞,用了许多人力将淤泥清除后,发现墓室后部有棺床,清理时,随葬遗物很丰沛,有的在棺床正前方,有的在棺床前西侧。根据墓室被淤土填塞情况看,失落在棺床前的一部分随葬物,原先都应放置棺床上的。棺床右侧前方置墓主人韩佚墓志一方,无盖。左侧南方置韩佚妻王氏墓志一合。
在棺床正中前沿部位上,砌小砖台一个,小砖台左侧发现有木盒与铁锈锈迹,并有少量骨灰,原来这里是存放有骨灰盒的。看来墓主人是火葬的。未见尸身和随身饰物,还是有些美中不足。
然而,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发现墓志就是最大的收获。
捶拓后展读墓志才知道,墓主人韩佚是韩延徽的孙子,曾经担任过营州(今辽宁朝阳)刺史、工部尚书、上京副留守加太保。爵位为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他的父亲为韩德邻,是韩延徽的二儿子。他祖父韩延徽的名叫韩颎。韩佚墓志里明确他葬于“先茔幽州鲁郭里”,可目前八宝山殡葬管理处东部韩佚墓一带并没有“鲁郭里”这个地名,但一路之隔的南面,曾有一村名称为“鲁谷”,郭与谷音相近,应该是鲁郭,在近千年的称呼中变为鲁谷,在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看来韩延徽家族墓地就在这里,有待进一步发现。
原文载于《知识就是力量》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