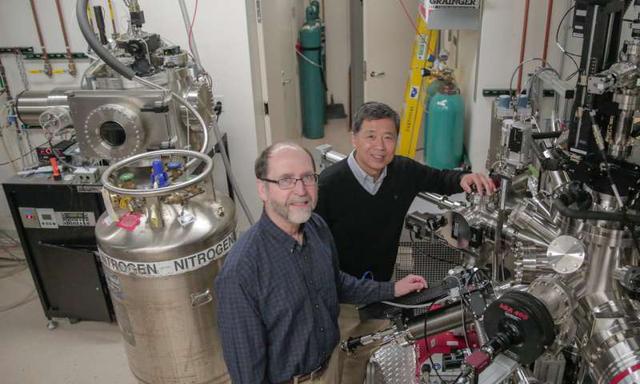我做天妃二百年了,成仙则有四千两百年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好看的替身梗古言小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好看的替身梗古言小说
我做天妃二百年了,成仙则有四千两百年了。
四千多年前,天帝白衣染血自蛮荒归来,身后跟了一位女子。
那女子是月华仙子,三界第一美人,名副其实的天界白月光。
只是她性子孤傲,目高于顶,唯一情之所系的,便是天地间至尊无双的天帝陛下。
四千多年前,老天帝隐退虚空界,新天帝为服众望,下凡历劫,战魔君于黑水沼海,于生死之际被魔族偷袭,是月华仙子舍身为盾,为他挡下致命一击,自己却神灵溃散。
天帝痛念于心,以半颗元神做皿,用心头血滋养了几千年,只盼有朝一日,月华仙子能复生归来。
所以月华仙子心悦天帝,是四海八荒皆称的佳话,而我爱慕帝主,则是三界六道俱知的笑话。
我只是一介凡女,出身卑微,命若草芥,不过机缘巧合之下,替元殊天君挡下一道天雷,才有幸得见天颜。
那日,元殊天君笑眯眯地问我:「你为本君挡下飞升上神的最大一道诛神天雷,免本君十万余年修行毁于一旦,本君心里感激,许你一诺,尽管开口。」
我说:「我想进天宫。」
他微微一怔,随即便又笑开,轻道:「简单。」
乘着祥云才至巍峨天宫门口,便见一袭白衣的天帝羽光而来,剑眉星目,华仪天成,却是脸色铁青,眸色锋凛:「元殊,你简直是胡闹!」
元殊天君唰地打开手中的鎏金玉骨扇,摇得不疾不徐,笑得浑不在意:「本君选在这个时候提前飞升,是怜你刚渡劫羽归,又损了半颗元神,怕魔界得了消息,勾结妖界攻来,你无人可用罢了。」
天帝却冷斥道:「孤早就叫你弃了这念头,修为不及,强行飞升,会元神俱散,不得超生,你简直是在找死!」
「本君现在不是好得很。」 元殊天君又露出惯常的吊儿郎当的表情, 「你非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魔界,本君劝阻不得,就只好陪你喽。」
天帝冷哼一声,似是并不领情,却也没再说什么,只抬掌将修复之术施来。
元殊天君挥手挡掉他的法术,一把将我拉到了身前:「本君此次成功飞升,修为无损,都是多亏了她,也没别的要求,只想让她在天宫做个小仙,你不会不同意吧,小老弟?」
天帝虽真的是他的小老弟,却最烦被他叫『小老弟』,惯常说的「滚」字都到了唇边,忽然记起自己已是天帝,三界楷模,又生生咽了回去,只一双金褐冷眸向我投来,隐隐泛着寒光,落在身上,冷漠疏离,如霜覆雪。
但他到底是答应了的。
答应我留在他身侧服侍,以仙奴的身份。
甚至亲自施法为我脱去凡骨,阔赠万年灵力,只因我的命格与月华仙子同出一辙,是他等了几千年,上好的塑魂之器。
元殊天君一听就变了脸色,抓起我的手就要离开。
但我是愿意的。
我看向天帝的目光笑色蕴然:「天帝允我飞升,予我长生,我为天帝赴汤蹈火,身死魂灭,不敢言悔。」
天界众仙都嘲笑我对天帝一见情深,痴心妄想,可我自己清楚,我不是痴心妄想,我只是……没有喝下那碗孟婆汤。
当年黑水沼海,魔君无良,少女献祭,于乌云压顶,暴雨滔天,波浪诡谲之中,一叶小舟如浮萍入海,漂泊无依,不过片刻,便被激荡滚涌的黑墨涛浪掀翻吞噬。
一浪接一浪的黑滚波涛如巨石频频撞击于身,我的骨头几乎都被砸断碾碎,心神俱裂,五脏皆损,可我不想死,可我太想活,可拼命挣扎,却终是黑海无涯,人难胜天。
命悬之际,是那双有着金褐瞳眸的人乘着祥云而至,拨开漫天漫地的黑浪,扫平滚滚翻涌的墨海,救我于危难,护我于心口,予我第二条性命,让我永世难忘。
缘于沼海初见,情定杏林微雨,更有梨亭品茗,莲池听荷,梅园赏雪,四时景致不及他万分之一温柔,点点滴滴刻心头,教我如何能忘,如何敢忘。
塑魂的时刻并不好掐算,早一分嫌早,晚一分不足,必须以万分的耐心去等待那十成十的精准。
这一等,就是一千多年。
长久以来,我都很清闲安逸,甚至没见过天帝几面,但他每一次来,我都用尽了心思迎候。
我知他喜茶,便早早去抚仙湖畔龙井泉旁等着,一定要在清明雨前就采到那珍贵茶树的头一茬嫩芽尖儿,用上神仙法启祝融真火微烘月余,再以长白山之巅天池水蓄养的那棵万年梅花树上千年积累的雪露冲泡,水至清至纯,叶至臻至翠,澄绿的芽叶在晶莹的雪水中翻腾舒展,剔透的似看得清浅碧脉络,如滴了青墨入水,缓缓氤氲出一盏人间四月天。
在这上百道程序中,最难的,当属泡茶的雪露,那甚至比元殊天君的祝融真火都稀缺几分,毕竟千年雪露易得,七万年梅花树却只此一株。
听闻那梅花上仙的脾气颇为古怪,仙位越高越得不到她的好脸色。
记得第一次去长白山,我在山巅足足等了六个月,霜雪严寒,呵气成冰,我不会御寒法术,虽是仙骨,也只是不会死而已,仍难抵寒气沁入心脉,伤及肺腑。
但好在还是感动了上仙,允了我半盏千年雪露,我自是千恩万谢,小心地将那溯光琉璃盏接过,仔仔细细地捧在怀中,贴在心口,婉拒了元殊天君的驱寒法术,生怕身上的寒气不在,雪露会融化,味道就变了。
却正欢喜期许之际,被等在天门的天帝一掌掀翻了杯盏,厉声诘问:「你去哪儿了?」
未及应声,他一双冷目从碎了满地的溯光琉璃盏扫过,眸光又如寒刀投来,入鬓的两道锋眉也似染了万年霜雪,若剑一般直透心底:「孤允你飞升,你便真当自己是正经的仙娥,长白山的绝顶雪露,你也配?」
「今日错过了千年难遇的塑魂良辰,你区区肉骨凡胎,如何担当得起?」
「不过一介凡夫俗子,有幸成为月华的塑魂之器,休要贪得无厌!」
他明明面无表情,语色淡漠,却一口一个仙君,一字一句凡人,无不充斥着仙凡有别,鄙弃的意味几乎是从骨子里透出来。
我讷讷无言,急急跪地认错,伏在冰凉的青玉砖石上,破碎的琉璃盏片几乎刺透掌心,鲜血汩汩而出,寒意却顺着脉络丝丝缕缕地蔓延上来,圈圈缠绕收紧,几乎将四肢百骸都凝滞成冰。
元殊天君急得拉我,愤然与天帝呛声:「是本君带她去的长白山,要怪就怪本君!」
天帝目色微怔:「你也去了长白山?」
「是,本君去了长白山。」元殊天君面上浮现显而易见的痛悔之色:「几万年来,我日日愧悔,却破镜难圆,再回不到当初。」
他闭了闭目,掩去眸中泪色,苦心规劝:「自从长白山成了天界禁地,你便再没有喝过一口满意的茶水,她是为了你,才巴巴去求那千年雪露,你不要像我一样,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天帝不耐地撇过脸去,眼风都不屑扫我一眼,便冷冽道:「孤不需要。」
话音未落,白光烁闪,衣袂纷飞,我只来得及抬眸捕见一抹青白广袖锦袍的角摆。
元殊天君气的七窍生烟,却也奈何不得,只连忙将我扶了起来。
我的膝盖已经跪得麻痹,加上残留的长白山冰雪寒气,更是刺麻得发疼,像是有千万只蚁兽在同时啃噬,几乎站立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长白山是若梅上仙的隐世之地,天界禁区,即便是贵为天帝也不得用仙法窥寻,更不得入内,所以元殊天君才在雪山外等我,所以天帝才找不见我。
恍然便想起在长白山上,若梅上仙一边神色傲洁地递来雪露,一边警声告诫:「天家寡情冷血,你为他做的再多,他也不会感激一分。」
我当时答了什么?
想必是眉目雀跃,笑色晏晏:「无妨,他只抿一口,我也满足。」
恍神间,元殊天君已一边为我疗愈,一边歉声道:「惜衡素来孤高寡言,卓尔不群,现下只是太忧心月华,才言语没了轻重,你别见怪,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
他以前眉目最是温柔,礼数更是周全,被我的指尖不经意地触到,都会受惊般弹开,红了整张脸跟我致歉,怪自己唐突。
我心不在焉地掏出帕子,慢慢擦拭掌心,长白山的雪太冷,让人如坠冰窟,长白山的雪露却太烫,像是身处无边炼狱,被烹烈炙涌的油翻滚着浇在心头,滋滋冒着血腥气。
天界众仙最近又有了谈资,口口相传得极为精彩,天帝罚我跪于天门几天几夜,还亲手施了天雷断脉的鞭刑,回去的时候血都浸透了衣衫,从天外一直蜿蜒到仙奴殿。
我听了只觉可笑,元殊天君却气得跳脚,最是替我不平,每每遇见嚼舌根子的,俱先隐忍不发,待他们讨论到兴头上,便突然用应龙真身怒吼而出,直吓得他们心神迸裂,听说有几个现在还在告病养伤。
元殊天君甚是得意地和我复述当时场景,一连讲了几遍,每次都不忘在最后加一句:「不必在意这些酸腐之言,你长得可比他们那副尖酸刻薄样好看太多了。」
这话不假,我确实蕙质娇容,美艳无双,美到人人都背后对我糟践鄙夷,却各个当面都不忍苛责半分,只因我那张和月华仙子一模一样的脸。
谁人都知,当年天帝下界历劫,九死一生,月华仙子痴情至深,执意追随,连轮回台也愿意跳,幸得元殊天君眼疾手快,才将她救下,但她还是被轮回台的煞气削去了一缕青丝。
我……就是那缕青丝,所以我当然是与月华仙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月老和我知,跳轮回台前,月华仙子私下找过月老,苦苦哀求他为她和天帝在人间界安排一段姻缘。
月老怜她钟情天帝万年却半分不得回应,终是点头答应,不想红绳已结,姻缘已定,投生的却只有片尾乌发。
所以,我和天帝是姻缘注定,合该琴瑟和鸣。
天帝不知是听见了风言风语,还是心里过意不去,第二日便来了仙奴殿,彼时我正半倚在藤架上,看着院前的曼陀罗花出神。
曼陀罗是魔界唯一的花,这唯一的花也是黑色,黑的像晕不开的墨,如今我将它种在天界,却是通体雪白,不知何时,它才能变回它本心的颜色。
或是,永远都变不回了。
天帝缓缓行至我身后,停驻了好一会儿我才发觉,急忙站起身来行礼告罪。
「无妨。」他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一声,半晌,才迟疑着开口:「你……还愿不愿意为孤沏一杯茶?」
我自然求之不得,可才要动身,又忽然想起雪露已经没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思绪,更加不自在起来,一向不假辞色的脸上竟浮现几丝惭愧与窘迫:「普通的天雨之露,也是能入口的。」
我立即雀跃地应声,疾速而稳妥地摆好一应壶具,用尽浑身解数烹了茶水,小心翼翼地呈到他的面前,仔细地觑着他的表情,生怕他有一丝的不悦。
他从未被如此近身的灼烈目光盯紧过,又露出了几分不自在的神色,却仍是耐着性子品了茶,微微熏红着耳尖称赞:「不错。」
我悬紧的心这才放下几许,漫漫柔绻在胸腔翻滚而上,砰砰地撞击着心口,连面颊都羞涩地染上绯红云霞,一时都有些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陛下喜欢,奴婢便再去讨些长白山的雪露回来。」
他眸光微闪,眼底浮现浅浅的动容之色:「你……很是用心。」
自到天宫以来,他从未以这样温柔的目光瞧过我,四目相对,视线相接,我像是被烫到了一般低下头去,嗫喏着开口:「奴婢本分。」
静默半晌,他长臂探来,将我的手拉过去,查看我的腕子,眉头便微微蹙了起来:「伤还没好?」
那日我心里难过,元殊天君也不是个细心的,所以手腕上的划口便留了下来。
天帝的手掌炙热,我忍不住微微地缩了缩手,他却紧握着不放,只一双桃瓣似的眉目静静凝来,我只好道:「只是小伤,陛下不必挂心。」
他不甚赞同地皱眉,蕴起仙法于修长若竹节的指尖,莹然生光,刚接近我的伤口,却又停了下来,手腕翻转,便有天青色的玉钵浮现掌上,他轻轻拿起盖子,浅浅的雅香泻了出来,他用赭石棒沾起些许莹白的玉色软膏,奇道:「这便是人间的药膏吗?」
我点了点头,有些猜不透他的心思,但听到他提人间,便忍不住心头一跳,只怕他又要羞辱于我。
他却神色温和道:「你会更习惯用凡间的法子疗伤吗?」
天潢贵胄,无上至尊,何时在意过他人喜好,如今竟能着意问我一句,当真稀奇。
我心头骤然暖过涓涓细流,轻道:「只要是陛下赏赐,奴婢都喜欢。」
他瞧了瞧那药钵,目中闪烁着新奇的璀璨光色,跃跃欲试地拉我坐下,小心地将软膏抹在我的伤口,还时不时抬眸查看我的神色:「疼吗?」
「不疼。」我轻摇了摇头,看着他认真的神情,又想起了曾经初遇。
献祭那日,波涛翻涌,跌来撞去,我虽被救得及时,却免不了处处都是严重的擦伤和淤痕,那时,也有一人,俊容墨衣,神色认真地为我上药,手脚笨拙地包扎固定,明朗清风的眉宇间尽是严肃谨慎,只渐渐凌乱的呼吸和红透了的耳根昭示着心里的紧张涩赧。
神思游转,天帝已经处理好伤口,我的目光落在手腕上,那里打着一个丑丑的结,看起来像极了想系个蝴蝶结却失败了的作品。
他大概猜到了我的想法,立即矢口否认:「不要误会,孤才没有尝试绑那劳什子的蝴蝶结!」
我忍着笑点一点头:「陛下打的千千结很不错。」
他有些挂不住面子,突地站起身来,我以为他被我惹恼了,急忙请罪,他却摇了摇头,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孤不是生你的气,只是有些话,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微微笑着瞧他,目色诚挚:「陛下尽管说。」
他面色迟疑,缄默半晌,终于还是缓缓说道:「半刻钟之后,是塑魂的又一黄道吉辰。」
我一怔,立即垂了眸,将目中的骤然涌上的痛色掩饰过去,只是喉间却像是酸极的梅子化成了汁,涩得发苦,忍不住攥紧指节,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才勉强挨过那陡然而起的心痛如绞,重重地点头:「自然……自然……」
自然是她魂归故里,自然是我神殒命消。
以我之血脉换月华仙重生,是我答应成为塑魂之器时,就早已知晓的结局。
所以我说的愿为天帝赴汤蹈火,身死魂灭,不言悔,都是真的。
况如今,我已享了千余年寿命,不能说是吃亏,而是占了天大的便宜,所以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他之所愿,吾之所求,足矣。
我在往生池醒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锥心刺骨的疼。
塑魂,便是被千千万万把魂刀游走遍四肢百骸,将每一根筋络都斩断,每一丝骨血都碾碎,让灵魂至身心都细细塑成月华仙子的躯壳,若未成,又要依样回转拼成我的灵肉,但凡整个过程中,有半分疏漏,有半分意志不坚定,我都会神灵溃散。
更别说,那撕魂裂魄的疼毫无消减之法,只能生生受过,所以每每结束,都如同在地狱里走过两遭。
所以,即便这是四千年来,我经历的第五次塑魂,早已熟知了每一个步骤,却仍是难以习惯这样滔天的苦痛。
只是一睁开眼,看见天帝那双清冷矜贵的金褐瞳眸朝我望来,素来疏冷倨傲的脸上也难得地浮现关切神色,我便觉得,似乎也没那么疼了。
「……月华。」他不确定地开口,目中满是希冀与忐忑。
我蓦地白了脸色,实在不忍让他失望,只默默地垂了眼,并未言声。
他却也一瞬就明白了,闪烁的眸光顷刻便晦暗下去,猛一拂袖,便旋身离开,只半句几乎散在风里的「好生休养」 漠然地消落,被往生殿氤氲的温泉水雾薄薄地裹了一层,传至耳边似乎也带了些微的暖意。
我已虚弱至极,无暇他顾,只能缓缓闭了目,任往生池里的和暖的温泉水覆过全身,丝丝渗进衣衫,透进骨骼,慢慢生起骨肉,一点一滴地疗愈万千的细碎伤口。
可惜这温泉水再灵,也只能生死人,肉白骨,却永远都愈合不了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恍然间又听脚步声响起,我心头一喜,立即抬眸望去,语气却不禁失落下来:「天君。」
「距上次塑魂才不过百年,他竟又用你试炼?」人未到声先至,他急火火地跨步进来,几乎是怒气勃发的神色,却在见到我时倏地住了口,满目皆是难以置信。
我知我现在必是唇无血色,面色煞白如鬼,便极力地弯了弯唇,希望别那么骇人:「这副模样,吓到天君了吧。」
「你还笑得出来!」他的眉头狠狠地绞缠一起,低下身子查看我的伤势:「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脸色,比若梅头顶上的万年积雪还要白上三分。」
我勉强地扯了扯唇角:「哪有三分那么夸张,最多两分罢了。」
「你……」他满腔怒火,却又劝我不得,只长叹一声:「你又何必如此?」
我自是有我的坚持:「鹊羽卑若微尘,一生美好,皆在黑水沼海的惊鸿初见,一眼万年。」
他怜悯地瞧我:「值得吗?」
「当然。」我已累极,半合了眼,语气轻却笃定:「我说过,只要他要,只要我有,无不舍得,无不倾囊相予。」
元殊天君将我抱回仙奴殿的时候,我身上已无半分伤痕,但魂魄却因摧磨碾毁太多次,早已孱弱不堪,直如枯叶残枝,不堪一折。
我奄奄一息地靠在他的胸膛,乌长的发丝散落他满怀,像极了我孤散无依的意识,我不禁轻动了动指尖,感受着漫天漫地惊涌而上的痛楚,艰难地开口:「快了……」
他心口震震,沉稳的嗓音落入耳根:「什么快了?」
「月华仙子回来的时机……快到了。」我苍白的唇角泛起一丝笑来,忍着四肢百骸流窜过的一浪又一浪的灼烈刺痛,轻道:「我能感觉到,就是下次。」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记挂她?」元殊天君几乎恨铁不成钢,「你可知她若生,你便死,灰飞烟灭,不入轮回!」
「无妨。」我浑不在意,语气里甚至透出一丝欢喜,「只要她回来,陛下因失去半颗元神而残缺的记忆,也会回来。」
他几乎一瞬间便怒意翻涌:「他恢复记忆又怎样?那个时候你早就已经死了!」
「不是的。」我微摇一摇头,执拗道,「那个时候……他会记起我,记起我们的曾经。」
元殊天君心口蓦地一堵,明明怒气冲天,却瞪圆了双目,只一声轻骂咬着牙落下:「真是傻子!」
他总是如此,热心沸血,打抱不平,像极了凡间行侠仗义的少年人,我不禁莞尔,温然开口:「傻子今天要去找若梅仙子讨要雪露,疯子要不要跟着?」
「那是自然!」他瞬间来了精神,目中阴霾都一扫而空,转身就带着我去向了长白山。
若梅仙子见我虚孱至极,并未多言,也没有多留我,只念了冰心诀点在我的眉间,凝寒的凉意霎时自额头蔓延至周身,熨帖过四肢百骸,将万千经脉里奔涌沸腾的灼热痛楚都温柔的抚平。
我道过谢,便出得门来,才至山脚,远远便见元殊天君正焦灼地来回踱步,一见我来,就立刻急急问道:「她吃饭了吗?修炼了吗?看起来心情如何?」
素来傲气凌人的元殊天君,也会在这寒冰彻骨的雪山脚下,急惶地活像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年,实在是引人莞尔,我忍着笑开口::「还不错。」
他目色灼灼,晶亮得像日光下盈透的霜雪,满怀期待地指一指自己,又指一指长白山之巅:「那我……」
我淡笑着瞧他,轻轻点头:「或可一试。」
他瞬间像得了特赦令,急急就往长白山的方向冲,到了若梅仙子划定的结界边际,又不大放心地瞅了瞅我,瞧我浅笑着看他,才蹑手蹑脚地越过了长白山脚下界限,见没有任何武器凌空飞来,立马回头冲我笑得灿烂:「真的没事!」
他直了直身子,整整衣袍便要大步流星往山上走,却只见七颗梅花剔魂针簌簌破空而来,毫不留情地地打在了他的脚下,接着便远远传来一句厉声娇喝:「滚!」
「好嘞!」元殊天君应得干脆,已经迈出去的脚步也急急转了个弯,紧着步子朝山下走来。
腾云之上,纱雾飘渺,元殊天君垂着头,神色难掩落寞。
我不禁问道:「你与若梅仙子,何故?」
他轻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当初年少纨绔,不懂真心可贵,随意践踏,如今得了报应罢了。」
报应……若这世上真有报应,才最好。
一路默默,快至天门的时候,我终是忍不住开口:「其实若梅仙子心里有你,你在不周山飞升上神那日,我能为你挡下天雷,皆是受她指引。她当时虽易了容貌,但身上那股千万年沁渗的梅花香气却隐藏不掉,是她告诉我,无辜凡人受劈天雷不会受伤,不会损寿,若我能为你挡下飞升前最后一道薨天厉雷,你就会实现我的愿望。」
他一怔,不敢置信道:「当真?」
我语色笃定:「当真。」
他霎时喜形于色,照着我的发顶就喜滋滋地吧唧了一口,尤嫌不够,索性一把将我抱了起来,激动地转圈。
我笑他无状,却也被他的雀跃欣喜感染,头回在这肃严压抑的天宫露出真切的笑容来。
却蓦然觉得一阵冷意袭来,遍体生寒,不由抬眼望去,竟见天帝正立于天门之后,眸色晦暗地如刀投来,似乎连空气中都结了万年的冰霜。
我的笑色僵冻在唇角,未及反应,他又冷冷凝了我一眼,拂袖而去。
回到仙奴殿,我便将雪露放进了柜子里,那里已尘封了七八盏,都是从前讨来的,却很久都不曾动过。
其实自第三次塑魂失败,天帝来我这里,就不再饮茶,而是爱酒了,我精心研酿的,也早就变成了桃花醉,入口涩极,回味却是绵长甘醇。
之所以还循着旧例去长白雪山,不过是给若梅仙子说一说元殊天君的近况罢了。
无论当年如何忍痛断情,她到底还是牵挂他的。
我自然明白她。
子夜的星辰已然游转,殿外却依然毫无声息,依照往常景况,天帝在塑魂失败的深夜,心思最是黯然,但是今日的酒酿都已凉透,却还没等来那一袭白衣。
我失落落地将酒倒进杯里,一仰头饮尽,满嘴的苦,苦得发涩,在口齿间盈荡肆虐,回徜的后味该是甘甜,却如何品不出那分蜜意,只有难以言喻的酸苦充斥满腔,仿佛一颗心都泡进了三月的梅子汁里,涩得发疼,酸也到了极致。
我捏紧酒杯的指尖几乎发白,却还是勉力平复心绪,强捺下一腔的不甘与烦躁,来日方长,没关系,没关系的。
「砰」地一声,汉白瓷玉酒杯已然碎于我的指间,尖锐的碎茬狠狠剜进手心,将细细的掌纹割地七零八落,汩汩淌出血来,红的刺眼。
我冷眼瞧着那狰狞的伤口,不言不语地发怔,心早已千疮百孔,痛的麻木不堪,皮肉之痕又算得了什么?
却觉一阵风猝然袭来,眼前白衣一晃,手腕便被天帝抢了去,他那双总像是藏了万年霜雪的褐眸难得染了急色,语气更是盛怒:「你……你这样自伤自贱,难道疯了不成?」
我愣愣地抬头瞧他:「……陛下?」
他两道入鬓的剑眉死死拧紧,带着怒气冷哼了一声,落在我面上的目光像是刀锋刮过,但手下却是启了疗愈诀,轻轻在我掌上扫过,肌肤瞬时光滑如初,再不见一丝伤痕。
「谢陛下。」我微微垂了眸,涩涩开口:「奴婢还以为……陛下不会来了。」
他淡淡嗤了一声,华袍轻掀,款款落座,举止间自有一派丰神高澈:「偌大天宫,莫非王土,孤自是想去何处便去何处。」
我默默无言,心中却是欢喜,为他斟了酒,见他一连饮了十余杯,面颊已微微泛红,忍不住劝道:「陛下惜身。」
他淡淡扫了我一眼,突地劈手夺过玉白酒壶,高举饮下,莹澈的酒液一股脑地倾洒下来,似银河落瀑,洋洋洒洒地进了嘴里,咽下满口清苦之余,又溅出了些许,自唇角簌簌溢出,沿着玉一般的脖颈滑落,明明是粗鲁的动作,任他做来,却自有一派潇逸风华。
一饮而尽后,他握着酒壶重重地掷在方清缠枝古木桌上,一双染着绯烟云霞的凤眼缓缓投来,似是有桃瓣徐徐竟绽:「若孤不来,你待如何?」
我思绪一滞,便道:「自是等下去。」
他轻一挑眉,清漠的嗓音中已带了些许的醉意:「若是等不来呢?」
我微微敛了眸:「那便一直等下去。」
他目中有波转的流光滑过,金褐的瞳眸里头一回映进了我的脸,默默地凝望我半晌,突地一笑,语气里便掺了几分无赖:「若一直都等不来呢?」
我静沉地回视他,目光不躲不避,语色笃然:「地老天荒,总会等到的。」
他闻言眸色一动,探手便朝我伸来,却因酒意失了准头,身形不稳地歪向了旁边。
我急忙扶住他,被他攀住手臂顺势而上,人便靠在了我的肩膀,头也倚进我的颈窝,略薄的唇快贴上我的耳畔,将带着染染酒气的吐息柔暖地喷在我发烫的耳根:「那你为什么要对着他笑?为什么要那么……那么好看地对着他笑?你从来没有对孤那么温柔地笑过……」
「陛下……」我轻唤了一声,他灼热的气息呵进耳朵里,像是掺着微小的雷电,酥麻麻地痒,让我忍不住缩了缩脖子,便想躲开。
他却不肯,一抬手便轻捏住我的下颌,脸凑得更近了些,带着非要有个说法的执拗,暗哑地呢喃:「为什么?嗯?」
我偏头看他,那双绝世无双的灿金眼眸里,流光缱绻,柔情款款,暗藏着几分明知故问的顽皮劲儿,恍然间,像极了曾经初遇的少年气。
我眼眶一热,目中便滢了雾气,不自觉地伸出手去,冰凉指尖在他眼侧缓缓摩挲,几乎在一瞬间,就难以自控地落下泪来。
「别哭……你别哭啊……」他立刻慌了神,搂着我的手臂连忙紧了紧,又急急为我擦去涟涟泪水,目中竟涌上几分疼惜之色。
我心头一刺,恍如刀绞,只死死攥紧了手,让指甲狠狠嵌入掌心而痛出几分清明,笃声道:「陛下误会了,鹊羽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人,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可撼动。」
他深深地凝视我,目光闪闪烁烁,仿若盛了漫天璀璨的星辰,薄染了些许明知故问的得色:「是孤吗?」
我望进他的烁金眼瞳:「是你,也不是你。」
他却霸道地一凛锋眉:「必须是孤!」
说完未待我言声,他喉头一动,便探颈吻来,炙热的绵软印在我的唇瓣上,我猛然一颤,身子就不自觉地绷紧,下意识地想躲,却被他死死禁锢在双臂之间,只觉他灼热的手掌覆上我的脊背,施力一揽,我便身不由已地扑进了他的怀里,心口紧紧相贴,骤然凌乱的心跳混在一起,再难分舍。
他半阖着眼俯下身,轻柔地舔弄我桃粉樱唇,先是缓缓勾吻,再是慢慢加深,接着便打开我齿关,那香软滑舌便长驱直入,唆吻深吸,几乎不给我喘息的余地。
他却胸口起起伏伏,喘息更重,不知足的吻渐渐蔓延至脖颈耳根,手也不安分起来,在我的背脊纤腰急切地摩挲,修长指节所过之处,俱是一片火热灼烧。
「陛下……」我软软嘤咛一声,却见他目色更暗,恍若大火燎原,一弯身就将我抱了起来,却是酒意上头,轻晃着走到床边将我放下,陷入重重纱缦里,红烛帐暖,春意盎然,他又倾身吻了下来,莹白如玉的龙尾亦因动情而熠熠生光,娓娓流转,温柔似水地缠裹上我的身子。
我心里骤然一慌,突然有些害怕起来,下意识便抵住了他压过来的胸膛,他却完全不容我拒绝,像是一只禁锢了许久的恶兽,猛地扣住我的膝头,将我紧紧合住的两腿用力掰开,不待我挣扎,便整个人重重地压下。
我惊慌失措地挣动,在惶急和恐惧之下,突然生出几分力气,狠狠推了他一把,他本就酒意甚浓,又一时不防,竟真被我推了开去。
我急急下床,抬步就跌撞着往外逃去,却还没跑两三步,一双手便从后迅速探来,将我拦腰一抱,又拖回了床上。
我奋力推拒,却觉他自身后覆来,火热的胸膛贴着我的后背,粼粼生光的龙尾缓缓缠紧我不足一握的腰肢,像是束缚了我如鸽子般扑棱棱狂跳的心脏,喃喃地叫了一声:「眷眷……」
我蓦然一愣,便僵滞在了那里,又见他的龙尾流连摩挲在我的敏感之处,带着几分讨好:「眷眷,我想你。」
世人皆知,眷眷,是月华仙子的闺名。
可我……也叫眷眷。
当年初遇,他问我名讳。
我说我叫眷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眷,取挂念之意。
而见得最后一面,他红着脸问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眷眷,与他同结眷属。
思及此处,我心戚戚,又听他哀鸣般呓语地叫着我的名字,一寸寸地软了身子,如春水般融在他的怀中,再无挣扎的力气,而他也再不给我挣脱的机会,又倾身将我的嘴给吻住,任我柔弱无力的「呜呜」地挣动,只一手扣住我的双腕压在头顶,一只手去撕扯我的衣服。
我在一片炙烈火热中,只觉头顶的重重纱幔,像是重重山峦一般接踵压下,让人半点喘息不得。
自上次天帝一早从仙奴殿离开后,天界的众仙口中道谈资又丰富起来,无一例外,都是嘲讽我不顾脸皮,谄媚勾引天帝。
元殊天君每每都恨不得跟他们干架,但我都只说罢了。
毕竟,就连天帝陛下自己,都是这么觉得的。
那晚之后的第二天,我浑身都是青紫的痕迹,他却不发一言便要离开,我被他漠然嫌恶的眼神刺痛,心里的不甘与怨怼像沸腾的油一般翻涌,极为失态地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陛下也曾下凡历劫,如何得知你心心念念的脑中残影,就不是我呢?」
他却一把捏住了我的脸颊,迫我仰起头看他,居高临下地冷声开口:「区区一介凡女,怎配与她相提并论。」
此话若当头一棒,让我心寒如冰,待他松了手,我便失去了所以有的支撑,如一片孤落的残叶跌落在榻上,泪明明在眼中打转,却倔强地如何不肯落下。
我是区区凡女。
可当初在沼海为你挡下蛟龙毒牙的,是我。
在毒王谷不眠不休照顾你,为你试遍所有毒草的,也是我。
让你修为不及,却不顾师门众人劝阻,拼了命诛灭魔君也要救的人,还是我!
明明都是我,却生生悔,步步错。
他见我悲痛难当,目色沉了沉,眼里细微地闪过不忍之色,却最终还是转身离开。
而元殊天君得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理论,却被我拦了下来,毕竟,我如今大小也是个天妃,有职责要维护天宫安宁。
天妃是天帝后来下旨封的,大抵是为了补偿我。
但自旨意下达以后,他就再也没白日来过我的寝殿,都是漏夜而来,摸黑上床,食髓知味一般,用尽了手段折腾我,但每每都强逼我背过身去,不准看他。
我知道,他是在我身上找着他心里的影子,仿佛这样,他的愧疚,他背叛月华仙子的亏心,就能少一些。
可是那一日,在我和月华之间抉择的那一日,还是来了。
或许也称不上抉择,毕竟天帝早就做出了选月华的决定,他沉默了许久,久到良时吉辰都快过去,久到我的内心深处升腾起几分希冀,却见他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便道:「去吧,孤……会助你往生。」
「陛下可曾爱过我?」我仍有一分不甘:「可曾对我有半分动心,可曾哪怕有一瞬间考虑过,或许我才是……」
他目色骤冷,不是怕自己心软还是如何,断声截了我的话:「痴心妄想!」
我不再多言,转身走向了法阵中央,听着熟悉的塑魂咒声响起,被熟悉的苦痛淹没,漫天漫的寒气像细碎的刀,刺进我每一寸肌肤,切割我每一根经络,让我的灵魂片片凋落。
我太不甘心,太过怨怼,以至于月华仙子已经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我无依的魂魄却凭着执念仍不肯溃散。
我亲眼瞧着天帝,瞧着他的半颗元神慢慢融入骨血,记忆一点一滴恢复,而他双目中翻涌沸腾的痛,滔天的悔,仿佛无休无止,无穷无尽。
他终于想了起来,我才是他心心念念背影的真身。
而这个认知,这几千年来的一切,都在他记忆中的残影清晰起来的那一刻,显得无比的残忍。
我看着他发了疯一样凝聚我的魂魄,将我虚浮缥缈的半缕残魂死死抱进怀中,仿佛风起浪卷,涛声轰鸣中,死死握紧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再也没有了曾经的仪态风华,只像失去了所有般崩溃恸哭,浑身颤颤,几乎语不成句:「不是……不是的……眷眷……不是这样的……」
我虚弱地抬起近乎透明手,想要为他擦去眼下泪水,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颗大颗的泪珠穿透我的掌心,簌簌下落,几乎在地上凝聚成一片小小的湖泊。
他目色通红,满面仓惶,急急念了诀便要将元神吐出为我定魂,我却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只是微小的气力,他却丝毫不敢再动,生怕自己一用力,我最后的片缕魂魄也会消散,甚至连呼吸都是屏息。
我看着他,轻轻开口:「别再白费修为了,塑魂引的结局,你是知道的。」
他连连摇头:「不……不会的……」
「只恨……以后再不能伴随陛下左右。」我费力地开口,目色脉脉地望着他,「但至少,能为陛下完成夙愿,死而无憾。」
「你才是我的夙愿!」他握着我的手,紧紧贴上他的脸颊, 惊慌至极,语不成句:「眷眷……你才是……你才是我真正爱的人。」
我蓄一蓄力气,又再开口:「那么,陛下会记得我吗?」
「我当然会!」他满面痛悔,悲戚得不能自己:「你是眷眷,你是我的眷眷啊……」
我又问:「会永远记得吗?」
他已然痛苦地说不出来话,只拼命狂乱地点头,喉间呜咽着声声悲鸣。
「这就好。」我心满意足,微不可查地瞥了一眼那株浮现墨黑斑点的白色曼陀罗,又情深款款地望着他,在完全消散之前,说出最后那句几乎在瞬间击穿他整颗心脏的话,「无论如何,我都愿为陛下生生死死,千千万万遍。」
只要你此后余生,囚于情之炼狱,日日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
当年黑水沼海,惊鸿初见,我曾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好的少年。
他生来悲悯,天性善良,为所有献祭少女披荆斩棘,谋得生机。
他救我于危亡,怜我于困顿,安置我于桃花源。
他坚定温柔,勇往直前,敢与世俗成见对抗。
他说他叫无疆,是魔族少主,会洗去魔族污名,带领魔族走一条向善的路。
可是我害了他。
我救下的那个修仙的凡人少年,他带人覆灭了桃花源,捣毁了万千珍姝。
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兵天将,不顾哀鸿遍野,不顾凄楚求饶,将无疆精心培育的桃花源杀成了一片尸山血海,那里的百里桃花,现在还染着殷红的血,永远都难以退去。
而那个修仙少年,就是当初下凡历劫的天帝,他叫惜衡,我们所有人,都是他功德簿上的一笔,都是他通向天界的垫脚阶梯。
所以,我用尽心心计将孟婆汤吐了出来,带着前生的记忆投胎,求仙问道几世,终于探听到了元殊天君于不周山渡上神天劫的机会。
所以,我成功地入了天宫,骗过了高贵的仙界众神,让他们都以为,我对天帝用情至深,甚至天帝自己都信了。
我说,天帝允我飞升,予我长生,我为天帝赴汤蹈火,身死魂灭,不敢言悔。
可我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所行所为,能加深他一分痛苦,即便生死无状,神灵俱散,我也心甘情愿。
我还说,我和天帝是姻缘天定,合该琴瑟和鸣。
所以,最应亡于他情浓缱绻之时,为他铸造最坚固难撼的牢笼。
我也说,他之所愿,吾之所求,足矣。
足以让他也体会一遭,最爱之人死在自己面前,是如何的撕心裂肺,摧肝断肠。
我又说,只要他要,只要我有,无不舍得,无不倾囊相予。
只求他每每思及,追悔不已,恨不能杀了自己,却求死无门。
所以,我真的愿为天君生生死死,千千万万遍。
只要他此后余生,囚于情之炼狱,日日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
但有一句话,有一句我望着他那双灿金瞳眸说的话,是发自肺腑,无半字虚言的,那就是鹊羽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人,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可撼动。
那个人叫无疆。
他有一双世上最美的灿金瞳眸,后来被所谓持身正道的天帝夺去。
而他却死于他的十七岁,死在三月四日的春暖花开。
死在,我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