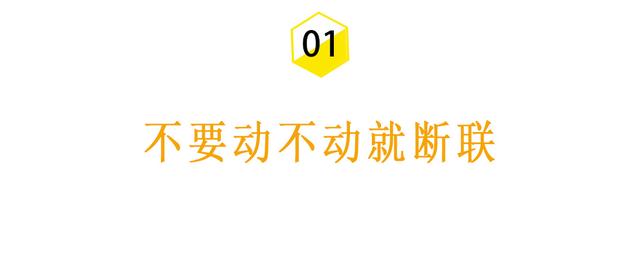冬心梅:清到十分寒满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冬心《墨梅》
冬心,冬日孤寂凄清的心情。
二百多年前,一介书生病痁江上,寒宵怀人,不寐申旦,遂取崔国辅“寂寥抱冬心”之语自号。初见此名时,我却想能谓之冬心者当是梅花,念及,脑际就会莫明其妙地浮现一个场景:山野有梅林,梅林有茅屋,一个素衣女子掀起竹帘把头探出窗外,嘴唇翕动却没有发出声来,好像是生怕惊着立雪赏梅的青衣书生。
冬心即清代画家金农,扬州八怪之一,五十而画。我十几岁时读汪曾祺小说《金冬心》,记得他对这位公认为扬州八怪里的一号人物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彝器上的铜绿,但末了却叹服: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当时,汪老的话反而勾起我无限想象他非常喜欢金冬心的另一面——“疏能走马,密不容针”的梅花,究竟是什么样子。
明朝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或许也算有癖之人,不懂也非常喜欢书画。后来,捧读《冬心画谱》,铭记冬心的梅——“吾家有耻春亭,因自称为耻春翁。亭左右前后种老梅三十本,每当天寒作雪,冻萼一枝,不待东风吹动而吐花也。”冬心因痴情于梅,视梅为手足,故又有“晨起用杜道士小龙精墨为梅兄写照”之雅记。如此爱梅,清极也奇极。
冬心《墨梅》
冬心一生画梅很多,涉笔即古,每画必题“一摅枨触之感”,书法上的“古朴”,造就了其梅花的“古拙”,书法上的“雅致”,造就了其梅花的“生趣”。大幅与小品、画轴与册页,大多是墨梅,很少敷色,即使敷色也不浓艳,且授书入画,借书以抒发情感,而使梅花“生意”。据说张大千最心仪的画家冬心是一个,说“金冬心的画画得极其蹩脚,但是又好得为得了”。又蹩脚又大好,学问甚大,不同一般。我注意到,人们评论冬心的梅花,大多会提《寄人篱下图》。这幅作品是冬心梅花三绝图册中的一幅,现藏南京博物馆。我曾寻来图片细细欣赏,画幅很小,构图很简单,两块方形的篱笆栅栏内,老梅一株,一枝枝梅花盛开,透过栅栏的门,还可以看到梅花点点落地,从而使这幅本应拘谨的画面产生了天地舒展、空灵透达的效果。左侧用渴笔八分题有“寄人篱下”四字,非常醒目,突出了此画的主题。关于这幅画,有人解作成表现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不满,高高的篱笆墙是封建制度的象征;有人说梅花再好却无赏花之人,当理解为寄人篱下的怀才不遇,才华横而不流;还有人认为这幅画别有寓意,它所强化的是一个关于“客”的主题,冬心实际上是杭州人客居扬州,生活窘迫,画是他生活的直接写照,他过的就是寄人篱下的生活,此画由寄人篱下的生活联系人类生命暂行暂寄的思想,高高的篱笆墙,其实是人生的种种束缚的象征,人面对这样的束缚,只有让心中的梅花永不凋零。
2016年夏,笔者第一次到扬州寻访冬心寄居室
人生如寄。冬心30岁时便到了扬州,浪漫、优雅、浮华,扬州仿佛是一个仙境,有一种纷沓杂乱的光彩使艺术家们在这里集聚。那时候,金家是钱塘大家族,冬心身材颀长,须髯满面,是一个热情而看起有些极端的游历者。他的足迹遍及四方,可以住在舟中,住在深山的古庙里,或简陋的旅店中,但很少住在家里。他可以远离妻、妾,但是对龟、鹤、小狗一类的动物却有着无比的喜爱,经常携行在他的身边。传说他的出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一个集团——永远有一群男仆跟随着他。男仆们各有不同的性格,也各有不同的技艺或专长,他们拥簇在冬心四周,善于裱褙的裱褙,善于制砚的制砚,善于理琴的、唱曲的,善于制作灯笼的……而冬心仔仔细细地鉴别着各种由没落府邸所流落出来的珍贵器物,讨价还价,争辩真伪,叙述一件古物的渊源,两只眼睛不时会闪烁出异样的光彩。更多时候,冬心是在扬州卖书鬻画,自嘲画梅乞米寻常事。《金冬心》小说中就写到冬心因为卖不出去字画,想方设法做了十张乌木方灯架子,四面书画,托南京袁枚代卖,而袁枚复信说:“金陵人只解吃鸭月肃,光天白日,尚无目识字画,安能于光烛影中别其媸妍耶?”时隔二百多年复读此信,仍旧读到一介画家踽踽走进耻春亭,默然凝眸老梅,失魂落魄。
2019年2月笔者第二次到扬州寻访冬心寄居室
冬心画室前的那株清梅尚未开花
那个时代,冬心也有妻有妾。哑妾孟娟是冬心人生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女人,她是扬州八大盐商纲总江鹤亭精心培养的“瘦马”,后天药哑,但长得非常漂亮,人也特别聪敏,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当时冬心是应邀帮助江鹤亭整理上万卷从京城购回来的古版书籍,江鹤亭派孟娟作为金农的助手。在冬心的细心调教下,孟娟很快成为整理古版书籍的好手,两人也在朝夕相处中有了恋情。据说,当时经常来扬州江府的袁枚也十分喜欢孟娟。最后江鹤亭只好在孟娟面前摊牌,一个是袁枚,一个是冬心,结果孟娟毫不犹豫选择了冬心。当时冬心60岁,孟娟20多岁。
冬心一生不得志,晚年也不富裕,“以布衣雄世”,过着“和葱和蒜卖街头”的落魄书画生涯。他带着孟娟居住在天宁寺附近的枝上村,与郑板桥夫妇、李方膺、李鱓、黄慎、高翔和汪士慎等人交往非常密切,他们当中有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卖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客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直把他乡当故乡,在扬州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是中国最早一批让艺术走进市场的画家。可以想象,小孟娟精通琴棋书画给这群穷困潦倒的文人墨客带来太多的快乐,抚琴斟酒,磨墨铺纸,是诗画知己,是添香红袖,更像一朵梅花盛开在冬心苍老孤寂的心境。
这样的日子仅过了七年。孟娟意外染上一场重病,被送回钱塘金家大院,像一季短暂的花期,很快就香消玉殒。
孟娟死后,冬心一下子老了许多,70岁后带着一只瘦鹤寄居扬州旧城的西方寺中,吃斋、礼佛,同时也手不停地挥画。冬心在西方寺居住的最后几年,是他人生绘画的爆发期,绘画题材从传统花卉走向山水、人物、马、自我写真,直至佛像,可谓无所不画,无所不见开创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大境界。这段时期,冬心也画了很多梅花,仅《冬心画谱》后面的书画年表就记载了近百幅传世墨梅作品,皆是有美感的梅花,皆是有风骨的梅花。“只有梅花真知己”,梅花的精魂化作了冬心的寒葩冷艳,穿过岁月的流光,至今在白净的书页上向尘世传送着缕缕幽香。
冬心《对梅饮酒图》
我特别喜欢冬心的一幅《对梅饮酒图》,“停琴举酒杯,笑对梅花饮”,观此画幅真让人生落英之思、坠红之叹、风尘之怨、感遇之想。这是冬心心中的冬心,浓髯、肥颈、长衫,独坐在梅树下,琴弹给自己听,酒倒给自己喝,笑笑给自己看。那一种情绪,打动人的,是因为他勾起了你某一根快要麻木的神经,忽地令你心里水润润地、怔怔地要流下泪来。画中横斜的一枝花并非冬心墨笔写梅,而是少见的红梅,一朵一点淡淡胭脂,如红颜。我想到了孟娟。“美是欲望的最高形式。”如果孟娟在冬心身边,该会给冬心斟酒两人对饮,还会给冬心抚琴一曲,冬心该会拾起一朵梅花与美人戴,还会给美人吟诗一首。艺术家更愿意在这种错觉,甚或是幻觉中,赢取心灵的安静。亦如冬心于穷愁潦倒、意兴阑珊之时,一沉思,一低吟,一怀想,一挥毫,一相思——
清到十分寒满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板桥竹: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板桥《兰竹图》
那一枝冷梢,拥着一个冬天的清醒,怀着一个春天的想望。
在《冬心画谱》上,我曾经读到一幅自画像题记:“十年前,卧疾江乡,吾友郑板桥进士宰潍县,闻予捐世,服缌麻,设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东莱,乃云冬心先生虽撄二竖,至今无恙也。板桥始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予感其生死不渝,赋诗报谢之。近板桥解组,予复出游,尝相见广陵僧庐。予仿昔人自为写真寄板桥。板桥擅墨竹,绝似文湖州,乞画一枝,洗我满面尘土可乎?”
金冬心年长郑板桥6岁,画竹却自称是学郑板桥的。我看过郑板桥的纸媒原画,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三楼展厅,右边T型角落悬挂着郑板桥的一幅墨竹,没有玻璃罩盖,纸已泛黄,画上几枝竹叶墨黑一团密得透不过气来,结果是我索然无味去认读画上题跋,而转身莫名喜欢上吴昌硕的一幅对联。几年过去,我已想不起吴昌硕那幅对联写得是什么内容,却一直忘记不了三百年前的那几枝墨竹,清风明月,偶尔萦绕一帘幽梦。
板桥雕像
郑板桥即郑燮,江苏兴化人,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郑板桥20岁左右即寓居扬州,像那个时代多数汉族读书人放弃科举一途,是避祸自保,而到扬州去卖字卖画。扬州,使人联想到运河,联想到盐,也联想到财富与繁华。然而,扬州以名园、胜景、文酒会的文艺活动背景,与大多数艺术家所居住的肃穆幽静的古寺,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森森的古木、和简朴洁净的僧舍,不仅适合于他们的创作,更适合他们拮据的境况。郑板桥寓居城外的于天宁寺,自始没有享受到扬州的繁华,自始就那样的困窘,那样的疲于奔命,受着命运的拨弄,所享有的,便仅是那些在饥饿、贫困中坚持理想的艺术家们“相濡以沫”的友谊,如冬心,如李鱓,互相激赏,互相扶持,但互不模仿,这就是他们之间长久不变的情谊。
《清代学者像传》记载,郑板桥一生的三分之二岁月都在为竹传神写影。郑板桥也曾有诗写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至于为什么画竹,郑板桥又有一番说明:“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其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声。于是一片竹影凌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我对竹不陌生,生活所居随处见竹。欣赏郑板桥的墨竹,慨叹竹移纸上是那么的脱尽时习,那么的秀劲绝伦,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幽静得永远像一个梦,梦境里青梅竹马的往事如夜半风声、竹声、水声让人一生无法忘怀。
板桥墨竹
梦醒过来,金冬心带哑妾居住扬州时,郑板桥的身边也是一个娇小女子饶氏,在丧父丧子之余,饶氏活泼、乐观而温顺,对郑板桥内心的创伤有着无比的平复作用,很能触发他创作的灵思。
郑板桥曾有三段姻缘,徐氏、郭氏与饶氏。雍正九年徐夫人死后,板桥娶了位继室郭夫人;乾隆二年,即徐夫人殁后六年,板桥又娶饶氏。当时郑板桥已45岁,饶氏仅19岁,但他们的这段姻缘十分美满,两人一直到老都十分融洽。郑板桥并且在《扬州杂记卷》中记述了他和饶氏的这一段传奇故事:雍正十三年,当时郑板桥正在扬州卖画,而且正处于穷困落迫之际。尽管如此,兴好交流的板桥对访古寻幽的兴趣丝毫未减,那日,他去寻访一个叫“玉勾斜”的地方,走到一家人门前,惊觉门前的对联是自己的诗作,就向户主饶夫人问个究竟,饶夫人说自己的女儿极爱郑板桥的作品,他忙道自己正是郑板桥,饶夫人马上把女儿五娘叫出来,两人情意相谐,当场定下终生。后来虽遭波折,但饶氏忠贞不二,又得义士程羽宸相助,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在郑板桥的诗文中,妻子似乎多与贫病愁苦联结在一起,给人一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意象。而,饶氏却永远是欢乐与青春的象征。如果说孟娟像一朵梅花,清绮美丽,一旦遭遇风雨就免不了花开花谢的凄婉零落。饶氏虽不识字,却像一枝晴竹历经风雨,陪伴郑板桥一年又一年。从郑板桥自己的诗词等资料中可以看出,郑板桥与饶氏两人互敬互爱,情投意合。尤其是在板桥中了进士,生活状况渐渐好转之后,他常常带着适意的心情描写他们的爱情生活。如他写第一次写饶氏:“小妇最怜消渴疾,玉盘红颗进冰桃。”又如“楼上佳人架上书,烛光微冷月来初。偷开绣帐看云鬓,擘短牙签拂蠹鱼。谢傅青山为院落,隋家芳草入园疏。思乡怀古兼伤暮,江雨江花尔自如。”(见《怀扬州旧居》)总之,饶氏虽然仅仅是一个妾的身份,但她在郑板桥的心目中却较之正妻还要重要。饶氏的聪明、娇怜、漂亮都使她拥有更多的资本获得板桥的宠爱,同样她也为郑板桥的私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这应该说是郑板桥落拓人生的一大慰藉。
巷陌百姓是喜欢郑板桥的,人生本已凄苦,谁又不祈盼像一枝青竹历经风雨仍旧劲秀呢?郑板桥书画上有一枚耐人寻味的闲章——“十年县令”。“十年县令”, 从案无留牍、爱民如子,到开仓赈济、罢官归去,即使过去了三百多年,人们说起这个县令仍旧会想到他的《衙斋听竹图》,三四竿墨竹清瘦苍劲,浓淡相宜,深浅相间,变化多端,最出彩的是图右下角的题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听竹本是件赏心的乐事,但画家却提醒赏画之人在赏竹的同时别忘关心人间的疾苦。而这,就是郑板桥画作的精髓,追求画外之意,讲究意在笔先。
十年的岁月,十年的颠簸,这种况味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可晓金莲红烛赐,老了东坡两鬓,最辜负、朝云一枕。”——初次读到这一句时,我心里忽然隐隐疼了一下。苏轼的三个妻妾都姓王——其中最聪明最受宠爱的是“老三”王朝云。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被称为苏轼的红颜知己,是她陪伴苏轼度过一生最艰难最困顿的岁月,后来朝云在惠州病逝,苏东坡写了一幅墓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想必,郑板桥思念饶氏吧。
板桥墨竹
冥冥中,雷同朝云的命运,饶氏生一子却不幸于六岁病死。然,饶氏尊夫敬夫却伴陪了郑板桥一生,郑板桥七十一岁时,与袁枚初遇于虹桥修禊席上,袁枚有诗《投板桥明府》,板桥还以“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联答赠,自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段佳话,足以令后人惊羡郑板桥的艳福,同时无限想象饶氏的美丽与风情。
纵观郑板桥书画一生,在绘画题材上,他选择了“专”,在笔墨风格上,他选择了“简”,笔下无怪兽猛禽,一丛竹依石摇曳,一丛竹伴兰姿眉,更能表现他的感触和际遇,更宜于表现那饱受压抑而坚贞自励的情怀,使人感到生命的兀傲清劲,也使人联想到画家对身边女子的那一份爱慕、敬重或是怜惜——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八大兰: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八大墨兰
专与简,也是郑板桥对八大山人的仰望。
郑板桥在高邮时看到一塘接着一塘的荷花,忽然讶异到,自己从来不画荷花,他周边的扬州画友多半写竹、写兰、写梅,但也很少画荷。由此,他把八大与石涛的绘画成就与两个人的声望做了一番比较:在人品志节和艺术成就上,两位遗民大师均不相上下,但在声望上,石涛却似乎不如八大,究其原因,是“博”与“专”的缘故,石涛“博”在创作题材、笔墨风格以及名号上,而八大则纯用简笔“专”于花鸟。郑板桥常画题材除了竹还有兰,八大就像一株幽兰在空谷兀自傲世。
笔者曾带着《八大山人》去寻访八大山人
八大为清初四画僧之一,我有一本《八大山人》,书中几乎汇聚了八大的存世作品,纵观其花鸟山水,墨兰远远不及墨荷多,要么杂生于竹石间,以兰为题仅有二三幅小品。网络搜索也不多见。八大写兰如他一贯作风,画面留有大片空白,令人遐思,兰花两三笔精简至极,他通过夸张把兰花之动态、兰花之神气表现得活灵活现,对笔墨的运用更是已臻化境。可以说八大的兰兰也被其赋予了个人情绪,四野空空,一株兰静静地独自开放成时间里的人,记录画家身上的时间斑痕,因为时间记得这一切,既记得不知从何而来的的过去,也记得不知将往何方的未来。
八大为明代皇族后裔,生长在一个充满文化艺术氛围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擅长书画。身为贵族子弟,他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8岁时就能作诗,能悬腕写北宋书法家米芾的小楷,11岁能画山水画,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八大18岁那年,崇祯皇帝自缢,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终结。明亡第二年,八大的父亲去世。国家剧变加上家庭变故,促使八大决定皈依佛门。清顺治五年(1648年),23岁的八大出家为僧,在进贤介冈灯社和奉新耕香院避居30多年里,不问世事,寄情山水,吟诗作画。八大在自己的诗中就说:“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
八大墨荷
在1680年的一天晚上,八大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并焚烧了自己多年来的僧衣,披星戴月步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南昌,此时的八大,已经是57岁的老人了。面对这样的入世。他还是无所适从,更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流露,仍然疯癫不止。在南昌故郡,人们看见了一个头戴斗笠,身穿长袍,脚踏布鞋,一路走走停停,摇摇晃晃,忽而爬地呜咽抽泣,忽而对天大笑的怪人。八大由焚僧衣到发癫狂,再到身体的恢复,实际上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从尘世进佛门,再由佛门入尘世,都要经过非人的炼狱,对于一般常人来说,这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精神啊!但是,他终于坚持住了,并且很快恢复了理智,回到了现实生活。
我曾与《八大山人》的作者讨论过八大,对于我这种不懂艺术也喜欢八大书画,其表示理解,说:“八大是喜欢中国艺术的人的一个情结,一个始终无法解开的心结——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懂与不懂,都爱八大山人,爱他笔下的小鸟、野鸭,爱他纸上绽放的含露的荷花,和一棵千年的古梅,爱他稚拙的书法,爱他的哭之与笑之。”其还告诉我,八大也非完人,避世又入世,后人研究当时清政府已准许明皇室子孙出山为清效力多年,八大还俗是想过搏取功名或者出人头地,此前与清延的官吏相来往,与他们诗酒酬唱,可能就有“在清王朝欲觅一席之地”念头。
我也想起《个山小像》,在这幅画里八大首次钤上“西江弋阳王孙”印。八大自称此画是老友黄安平为其49岁生日所画,后世研究也有人说是八大自绘托名。而近年来江西拍摄电影《八大山人》时,却又虚构了八大与黄安平的一段爱情。就像八大的每一幅画都是谜团,黄安平也是一个谜团。
2017年11月笔者到南昌八大山人纪念拜谒八大
因为此,我时常臆想八大背后的那个女子。
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记载:“斩先人祀,非所以为人后也,子无畏乎?个山驴慨然蓄发谋妻子。”道光《新建县志》:“八大山人老死无子,一女适南坪汪氏。”这些记载,都说明八大在蓄发狂疾,去南昌返俗后,迅速病愈,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娶妻生子,并确有后嗣。而在其诗偈、印文当中,因对婚姻不满,或朋友代为介绍妻室之事的诗、文均都存世可证。而这些零星记载,就像八大作品中的墨兰,隐藏于空山幽谷,一缕淡淡的清香撩人遐思。
八大传世有《安晚》册,“安晚”两字闲适之极,相当有诗意,堪称是八大画艺的大展示,他所喜爱的主题基本上全都包括在内。画册第一幅作品,即第二开,画的是一只平常的小花瓶中插着一枝兰花。瓷瓶上面画着大片的裂片,说明这是一只仿哥窑瓷器。这种瓷器在明清以来非常流行,在绘画中也有许多表现,八大也不例外。他笔下的这个花瓶上面涂上了一些墨色以表现上面的花纹,这也使得他画的花瓶与众不同,不论是哥窑还是仿哥窑的瓷器,讲究的都是一个素字,而八大的花瓶都有大片花纹,墨色花纹的另一个作用是和插着兰花相呼应,画瓶里插兰花,这也是不同寻常的构思,一般来说,画兰花都是一丛,单折一枝插在花瓶里,实在是雅之大雅又是俗之大俗,雅与俗之间天衣无缝,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八大《安晚》册页
以我之想,八大心中的爱人,当是如兰女子。如兰女子,应是那个拥着一世繁华却依旧淡定的女子,温婉的情思润泽着那颗为生计奔波而疲倦的灵魂。安然恬静里,一庭小院也可以圈起一片清幽的深谷。风雨窘境中,一颗兰心是哥窑瓷般传世的内敛入骨。
关于八大的妻子,或有或无,后人研究资料中也是隐晦曲折。数年前,在拍卖会上出现八大的一幅《画眉》,题跋是:“才多雅望张京兆,天上人间白玉堂。到底鸾台揽明镜,也知牛女易时装。”有人说这也是一幅抵制清朝情绪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画家题画眉鸟联想到张京兆为妻子画眉的佳话上来,可能与画家晚年的爱情有些关系。多次品读,我也愿意相信是八大山人在描绘他憧憬的爱情。诗中着全力描写张京兆的故事,说张京兆在朝廷是朝堂上的近臣,在家里却是一个与妻子亲昵情感笃深的好丈夫,他的生活实在是人间的白玉堂啊!后两句是说:鸾台像明镜一样严肃公正赏罚分明的张敞,也知道为妻子作应时的打扮,懂得“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儿女私情。八大晚年虽娶妻子,但他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从诗人晚年的许多诗文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诗人对这一情感不满足的表现。这首诗,就是诗人在对人间美好爱情生活向往的同时,借张京兆美好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来倾诉自己并不满意的爱情和家庭。终究,画眉莫如化情入心。
八大墓
清朝叶丹曾写《过八大山人》一诗:“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南昌寤歌草堂,是一所简陋的居室,满院子皆是蓬蒿,进了屋则处处落满了灰尘,厨中经常无米下锅,晚年的八大并不安晚,贫困交加,也就是说他终其一生也没有遇到那位可以为之画眉的如兰女子,眉山目水只能飘在梦境里,没有回肠九转,没有从雾里开出绝色的花。一方浅砚,一管轻毫,惟能在寤歌草堂挥写别一样的悲恻情怀——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石涛菊:一叶一清静,一花一妙香
石涛墨菊
书香墨浓,也期待那个懂得的人,期待一生的知音。
八大孤癖,朋友中却有画家石涛。石涛小八大10岁,同为清初四僧之一,原籍广西桂林,出身于明朝王族后裔,其从襁褓中就开始遭追杀,一生隐于庙堂,半生在山水间云游。石涛在艺坛上独树一帜,理论与实践结合,大胆地在作品中表现自我,宣泄个性,为后代写意派开启了先河。齐白石曾经评论石涛艺术成就,认为二千余载只斯僧。
我有一册《苦瓜和尚画语录》,字字句句皆经典,而看书中配画却没有八大山人的画那么惊心。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功败垂成。突然地,我心里面对这位大画家有那么一点点不理解,画语录闲置于桌案不再翻阅。
后来,《八大山人》的作者问我为何不喜欢石涛,我方才得知其还有一本著述《石涛》,在他们艺术家心里,石涛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绕不过去的画家,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乃三百年来中国写意画之一代宗师。
触动我心的,是其还说了一句:八大山人也与清朝官员交往。
石涛《陶渊明诗意图》
八大山人的装聋作哑,石涛上人自画墓门图,命运似是无可触及的神意,因此就有了两位画家的合作绘画。流传至今的,是两人合写的一幅《兰竹图》,画上题款:“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大涤子补墨并识。”此图先是八大山人画兰石,巨石向右拔地斜立,纯用淡墨简约地勾勒皴染,占据半幅画面,石下是左高右低的土坡,石脚一丛展开的兰花仅仅简约的数笔,将兰挺立而又摇曳多姿、生机勃勃之态写出即收笔,堪为八大本色,惜墨如金,高度凝练概括,而恰到好处。石涛后写竹,笔势顺着石势,竹竿劲挺而不失顺势,分披的竹叶用焦墨,以对应淡墨的斜石,更打破画面上幅的虚空,又以淡墨补一竿竹,略微与石势相背,以补画面左方之虚,兼营造出前后的空间深度,以少少笔墨以一胜多地表示出丛竹之境,又与浓墨的竹作了相得益彰的对比衬托。郑板桥就曾称赞:“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
我询问如果我也写石涛的画,该写什么。答案是:石涛菊。——颇感意外,我翻看了石涛的山水,翻看了石涛的墨兰墨竹墨荷,唯独没有留意石涛笔下的菊花。
真见了菊,真动了心。
石涛墨菊
其实,在石涛作品中,菊是常见题材,山水花卉皆见一种浓浓的陶渊明诗意。因为中国文化中,菊之于陶渊明是隐逸品格的一种独特表征,青松会没在众草,幽兰会萎于萧艾,惟菊则代表着诗人平息自己性情中那深感缺憾的部分之后的人格状态,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比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反对,只是那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只是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人生真味。石涛描绘陶渊明诗意,也包括其他画家笔下的菊花,就是作为士人双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现在诗中画里,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与诗人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相契合。因而对菊花的欣赏,俨然成为君子自得自乐、儒道双修的精神象征。
我对石涛的喜欢渗杂了某些情感,也决定了我对石涛菊的喜欢也是一种渐热。
并非那幅被称赞为石涛代表作的《对菊图》:高高的山峰,古老的松树,有一间房子,在房后有菊花一丛,有一个老人,在那里采菊,除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意。
也非石涛花卉册中的写意菊花:有意将菊花处于风雨之中,以墨勾勒,或点或染,甚至有把花叶画得淋漓尽致,几乎成了墨团团的。其有题跋诗云: 兴来写菊似涂鸭,误作枯藤缠数花。
石涛《采菊图》
我最喜欢的石涛菊是一幅人物画。这也是《采菊图》,所不同的是,在此画中山水隐去,人物突出,没有任何景物会干扰观众的意识,造型单纯自足,墨色的浓淡变化幅度不大,仅勾勒出一个采菊先生,神态逼肖,人物开脸的发须笔致细劲而柔和,衣褶勾勒苍涩古拙,特别是那品菊欲醉的飘飘仙容,着实让人陶醉于其中,透着菊的清雅、人的闲逸,还有生活的幽淡,还有时光的散漫。款题:“采采东篱间,寒香爱盈把。人与境供忘,此语语谁者!苦瓜老人济。”看来,那淡淡清香里,分明是前世的魂,故而,采菊人是陶渊明,也是石涛自己。这幅画,除了石涛印章外,画左下方钤有白文印“藏之大千”,右下方盖有朱文细篆印“善孖心赏”,可以看出,这幅石涛菊曾经大风堂主人张大千、张善孖昆仲所珍秘庋藏过。欣赏这幅画,我常常想,每一张名画跟人一样,都有一个曲折多变的故事,当初怎么诞生,怎么被遗在世上,怎么转的手,挂在怎样的房里,怎么换的框,怎么险遭不测,又怎么幸传到今;画若能言,娓娓道来,一定动人极了。
虽然也知道,因为家庭变故,石涛三四岁时就像田野的杂草一样潦草地出家当了和尚,但我还是没有忍住,傻傻地问石涛是否有过爱情或者妻儿。所得答案是:“石涛三无。”这四字,我记得让我发了好长时间的呆。诚然,石涛与友人从未提及他有老婆,仅有一次他在扬州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家”,提到他有许多需要他抚养的家人。所指家人,或许只是家中仆人或作坊助手。
2016年8月,荷花开时,笔者第一次到大明寺寻访石涛墓
人犹如此,仍旧阻止不了我疯狂臆想石涛一生中应该遇见的那个女子。
现实里,艺术的路,归根结底是回家的路。少年的懵懂,青年的冲动,中年的追求,包括抵抗、拒绝、挑战在内,迟早会使人疲倦,一个人最终需要的,只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忘记风雨、坎坷、恓惶,让人安心老去。然而,没有哪个艺术家不希望身边人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而懂得,是气质超群,是见识卓越,可海棠结社,行酒令填新词,可结队浪游,惊起宿鸟碎了花影。
想象中,那个女子,人淡如菊,极清苦中能极清雅,在情薄如纸的世界里,带着本性里的纯情与执着,绿衣捧砚,红袖添香,能够对抗空间的广漠和岁月的无常。
想象中,才盛,情殇,那个女子只能是书香墨浓的一枝菊花。
2019年2月,梅花开时,笔者第二到大明寺拜谒石涛墓
后来,我也读到另一本《石涛》,又大又厚,首先是关于石涛的生平传略,“在清初画四僧中,石涛最有画家的热情,因而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一位。”开篇这句话马上让我有一种释怀的感觉,作者并没有说石涛是最杰出或者最伟大的一位画家,人无完人,反而让我由衷地更喜欢石涛了。这本厚书有文有诗有书画,足见作者博学通识,不乱,不急,不闹,进去的人仿佛立在小庭深院中,感觉着人物的情感波荡和艺术的韵致横生。掩卷时候,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在石涛的百幅罗汉图学术研讨会上,他说到了石涛与曹鼎望的关系,而曹雪芹就是曹鼎望的孙子,红学有人提出曹雪芹写《石头记》,实际上就是写石涛,乃石涛记也。如此这般,我自然不敢多言,只是由此想到菊花,大观园里赏菊,林黛玉魁夺菊花诗,真是天外飞来佳句:“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呤。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林黛玉非凡俗,她是仙界来客,逗留人间,还罢泪,就去了。
折一枝花,敬献石涛
那么,菊花之于石涛,一枝枝情意洇染出灼灼风情,已成其身心的血肉,凝合成一种气质和风韵,仅留给我们在书香墨浓中品味,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一叶一清静,一花一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