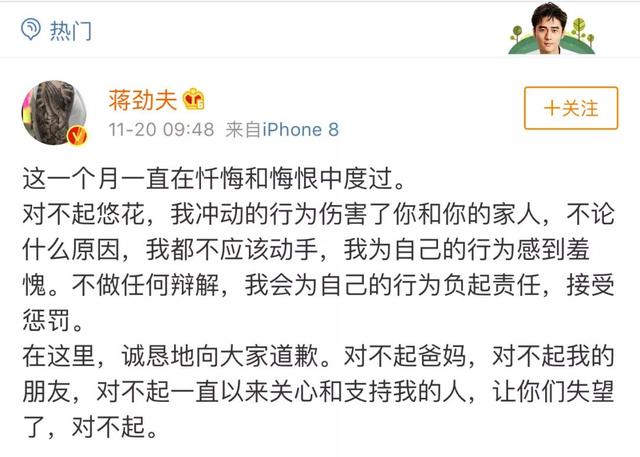山和水都睡醒了的时候,我回到了老家。站在老屋的院子里,我想起了那些树。她们不是婀娜多姿的柳,也不是馨香怡人的桂,而是结实结果的桃、李、杏,还有平常普通的柿子、桑葚和葡萄。
后院挨着山,山很缓,山坡不太陡,树就长在山上头。
最高最东头的缓坡上,生长着最小、最矮的桃和李。早春时节天气还是十分的凉,我和狗娃就相约了在桃李树下等太阳。我们笼着袖子,清冽的鼻涕流下来,也是拱了双手,在嘴唇上头呲一呲,反顺舍不得出手。我们跺着脚,围着树干来回跑,斜乜着树枝使劲看。树枝水嫩嫩地,孕着饱满的芽,一如阳光,死活舍不得跳出来。实在等得烦了,我们就开始用眼光细数着脚下的屋舍,这个是水牛家的烟囱,那个屋山桦一调子紫红的串子,是毛蛋家的柿饼。远远的河槽上,笼着一层薄薄的雾,像是四老爷烟锅里散出来的烟。终于,有一束光,像舞台上的探灯,打在了西头的玉笋岩上了,东边高峰岩的山上就腾起了暖暖的太阳。河槽里的雾气消散了,就又有一层烟雾从一间间的瓦舍的屋檐下、瓦缝里一丝一缕地漫出来。水牛家的烟囱里也腾起了蓝幽幽的袅袅娜娜的炊烟……
我们饿了,饭菜还没有熟,无奈地很,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吟诵起奶奶从豁牙缝里淌出来的歌:“烟子烟子么烟我,我是天上莲花朵,猪拉柴,狗吹火,神仙见了躲着我。”
我们日日来,我们一直等。等到李花儿白,等到桃花儿红。我们一直等,等到时令把太阳都催烫了,等到风儿把狗娃的衣服都吹单了。我们憋着劲,我们一直等,等到桃儿掉了毛,等到红李撑破了脸,我们再采下来吃。
绛紫色的树胶从果树的关节上团成了疤,越是熟透的果越是易生虫。我们不嫌弃,我们把糯糯的果虫衔在指尖上,伸过头顶上,对着阳光看它蠕蠕地动。我们把果虫的秽物剔净了,然后再大口朵颐地吃。利利落落的果核屯下来,还会卖个好价钱。
桃树、李树不长久,没几年就被虫子吃掉了。等到桃树、李树都死掉了的时候,后坡上的杏树又结了果。
杏树生长在塄坎上,分支离地高,实在是难以攀援。然而杏花儿粉,杏果儿繁,处处惹人恋。于是我们用了杆儿敲,找石块儿扔。青果子酸涩,特别地难以下咽。所以我们敲着、扔着就生了烦。最烦的还不在这,最烦一群野孩子。他们不用杆儿敲,他们只用石块扔,他们不是从院子往外扔,而是瞄着杏儿卯足了劲儿从那山上往下扔,忽然一下失了手,那石块就带着泥土携着风,忽地一下冲上了天。石块落下来的时候,不是在院子里,就是在房顶上,不是伤了人,就是碎了瓦。每回逢着这样的时候,大人就冲到院子,一声吼:“碎怂娃,谁?”山腰上便叮叮咚咚一片慌乱的跑路声。
西头还长了柿子树,树杈抻在矮墙上,叶子总墨绿肥厚地醉人,宽大的叶片就像是妈妈的手,摩挲着你的头。柿子树开花的当口,好像袖珍的向日葵。短命的果子落地时,我们就聚在树下玩。我们把小小的柿子果用线串成串,送给李家的小公主做手串和项链,还给胖胖傻傻的毛蛋子做了像模像样佛珠子。毛蛋子欢欢喜喜地,把佛珠子挂在脖子上,嘻嘻哈哈的笑着,睡觉的时候也舍不得往下取。

夜蚊子来了的时候,大人们都热得没法睡,一打黑,家家户户先点着了野蒿子,屋里屋外一遭熏,于是满院满街都是一股子浓浓的刺鼻的野蒿子的气味。大人们把门板放倒在自家的屋檐下,打着蒲扇、吸着烟。月牙儿高高地挂在天上,伴着浮云慢慢地游。我们就蹦蹦跳跳地玩游戏,狗娃喊:“月亮光光,把牛吆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吆到沟垴;沟垴打雷,把牛吆着回。”我们就跟着喊。狗娃喊:“城门城门几长高?”我们应:“三十六长高。”接下来我们再和:“骑白马,呱嗒嗒,走到城门瞧一瞧。”喊累了的时候,我们就捉迷藏,我们躲在高高的柿树上,看着狗娃神秘兮兮跑前跑后瞎忙乎。
我最爱我们家的柿子。虽不似火晶的讨巧,也不似磨盘的笨拙,更不似面柿子普通,我们家的柿树上结的是牛尖柿,果型大气,线条清晰,自带一种男子汉的霸气。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暖在土坛子里几日,取出来便香甜脆爽,没有一丝一毫的酸涩。果子在树顶熟透了,红灿灿的鲜亮,长长的架杆抻上去,轻取果子来,根本用不着清洗,用牙稍稍咬开果子尖端,口唇衔了,微微一吸,于是一股甘甜入了口,一直甜到心里头。
院子里最大的,就数这棵桑葚树。年代久的呀连爷都不知道她的岁数,主干高得我和狗娃、毛蛋子迭起罗汉都够不着头,树干粗得我们团起胳膊都搂不够。开枝散叶的时候,树冠就伸展到几十米开外的地方。两棵碗口粗的葡萄树就缠绕在这棵高大茂密树上头。
葡萄树还不是结果的时候,桑葚就结得繁,层层叠叠地挂满了枝头。桑树的叶子不甚大,果实却饱满匀称。一到了成熟的季节,全街的大人小孩都会提了竹篮来摘。有的就干脆啥不带,带了空人来,利索上了树,紫黑的果子摘满把,直接就往嘴里填。自家吃饱还不算,还给老婆孩子留,接着就满把满把地塞衣兜,结果是紫黑的汁液把浅色的衣服统统都染的变了色,平白地惹下老婆一顿的骂。蜜甜的桑葚实在是太诱人,枝梢的果子够不着,就有人掰着树枝往坏了拗,害得奶奶树下着急火燎的直叫唤:“哎哎,可不敢掰折了树枝子,还有明年呢!”看着谁走钢丝般站在树枝上只颤悠,奶奶的心又悬在了嗓子眼里:“诶诶,要抓牢啊,可是不敢摔了啊!”这边刚刚喊出口,那边又赶紧拍拍嘴:“呸呸!看我这嘴。”
不久,小子们渐渐就吃厌了。然而桑葚却依然是赶着趟地一茬一茬地熟。山坡上、猪棚上、院子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紫桑葚,爷就在院子里拿了笤帚一遍一遍扫,扫也扫不尽,染得院子的地面乌漆漆的黑。猪圈里的猪也却吃馋了嘴,闹哄哄的扬着头。
这时候,山林子里的野物也闻到了鲜,有一种肥美的野兽要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对门的姑爷就要嘈哄,叫来打猎的郑老孟。天撒黑的时候,郑老孟就得赶了来,先是抽足了烟,谝足了闲。后半夜就在树下支起了老猎枪,熄了灯,塌了火,凝神静气地练修行。小孩子们等不起,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后来嘭嗵一声响,院子就是一片叫喊声,一片追逐声。天打明的时候,灶房里就会飘散出一阵阵诱人的肉香。
桑葚罢茬的时候,葡萄就接着熟,一串一串的葡萄挂满在硕大无比的桑枝间,红的紫的十分地诱人。方圆百余里的地方没有人见过恁大葡萄树,没有人吃过恁独特的甜葡萄。
但是葡萄吃不多,葡萄也吃不饱,葡萄是种奢侈品。打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家葡萄的金贵。
葡萄成熟的季节恰好是暑期,前一天,父亲就得爬上高高的桑葚树,一干一干的摘葡萄,摘够一笼了,再用绳索小心地从树枝的间隙放下来。我们不上树,手持剪刀一挂一挂仔细地剪去形色不好的颗粒来,整理好的葡萄再谨慎的放到一旁的箩筐里。偶然的,一颗硕大的葡萄撕落了,母亲就赶紧送到我们的嘴巴里,然后咂吧着说:“嗯嗯,我们家的葡萄好甜呐!明天准卖个好价钱。”
葡萄罢茬的时候,长尾巴的雀儿就来了。一对对的野雀儿起起伏伏地,聚在枝头叫……
我们都长大了的时候,葡萄树死了。桑葚已多年不结果子了。然而柿子年年有,只是稀稀落落几十个,高高地挂在枝头上,我们不去摘,让它高挂着,彤彤红。偶然爬山边,看见杏树还活着,高高的树顶端竟然挂着黄橙橙的果,个个足有拳头大,摘下来尝,竟甜橙橙的,原来杏儿不酸涩,只是小时候性子急了,等不得它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