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爱武
(一)
1944年冬月的一天,伴随着一阵哇哇的哭声,一个女婴在鲁中平原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呱呱坠地。听那嘹亮的哭声经久不息,女婴的奶奶脸上露出了几份嫌弃的表情:“一个丫头片子,声音不小”。
这女婴就是我娘。我娘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那年,全面抗日战争已持续了七年,国家的财力和资源几近枯竭,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贫民之家的弄瓦之喜实在掀不起什么波澜。
我娘的奶奶是个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她从骨子里重男轻女。舅舅长到七八岁,她咬牙把他送进学校读书;大姨过了髫年,她却安置了一架纺棉花的机子让大姨纺棉花。大姨年纪小,手忙脚乱总也纺不好,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急得她满头大汗。她奶奶见状就大声呵斥她。我娘比大姨小一岁,大姨出生时,她奶奶一看是女孩很不待见她,我娘出生时就更不用说了,娘长到七岁,她奶奶基本没怎么关注过她。
某天她奶奶又数落大姨时,正巧我娘从此路过,我娘站在那里看了一会,逞能地说这有啥难的,我试试。我娘从小聪明伶俐,学东西很快。只见她沉稳地坐在机子前,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棉线均匀地、源源不断地抽了出来。她奶奶见她纺起来有模有样,二话没说又找人打了一架纺棉花的机子,从此,姐妹两个面对面,一人一架纺花机纺起来。她奶奶对她们要求很严格,每天纺几个线团是定量的,纺不完她们就不能出去玩,八九岁正是贪玩的时候,赶上村里有红白喜事,她们也只能先干完活再出去看热闹。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腰酸胳膊疼,但这两个懂事的女孩从不叫苦叫累。我们那片地区是省里有名的产棉区,棉花产量大,靠着姐妹俩稚嫩的双手,大量的棉花变成棉线,再由我姥姥把棉线织成棉布,这样,一家老小的被褥、衣裤都有了着落。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年,我姥姥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娘的奶奶在这一年去世,我姥姥开始当家做主。我姥姥看我娘聪明好学,就和我姥爷商量把已经十二岁的我娘送进了学校。考虑到她年龄的问题,学校安排她直接上了二年级。我娘果然不负众望,进了校门后,刻苦学习,很快赶上了前面的课程,而且成绩名列前茅。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学校里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娘就利用课余时间去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好强的她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去干些轻省活,而是跟在男劳力身后去刨地、拉车,像个铁姑娘一样,得到了村干部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1960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人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姥姥姥爷还咬牙坚持让舅舅和我娘上学。这一年,我娘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我们村的完小。读完小期间,我爹和我娘成了同学。每逢考试,要么他第一,要么她第一。他们像那个年代的男女生一样,互相之间不说话,但他们彼此默默地较着劲。
完小毕业那年,中考前夕,碰巧村里相应政府号召去学校选拔人才留用,我娘在村里影响好,又恰逢她姨父是村书记,她姨父跑到我姥姥家,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我娘回村当会计支援农业生产;我爹则考入兖州农机学校,从此跳出农门。
(二)
我娘回村当了一年会计,碰巧村里的小学需要民办教师,村里考虑到我娘在学校时学习成绩优异,在村里各项工作表现积极,堪称学生表率,就把我娘调整到学校做民办教师。
那时乡村学校条件很艰苦,民办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也得负责学校的其他事物。我娘热爱教学事业,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关心学校里的大事小情,只要需要她,她毫不含糊,事事争先。娘说,曾经为了学生冬天取暖,她和另外几个老师一起,推着小推车,一天往返近七十里去周村推煤,别的女教师是互换着推,她咬牙坚持着从头推到尾。晚上回家躺倒炕上,浑身酸痛的像散了架一样。
到了农忙时节,学校一放假,我娘又成了地里的主要劳动力。娘说,每年割麦子时,都是男劳力负责割,女人在后面负责捆扎,她却抢着去割麦子,而且还得争取成为领头雁。割麦子时,一般是五个人一组,割的最快的那个人在中间,由他(她)带着腰子(腰是四声,腰子是用棉花皮搓成的绳子)。
割麦前,他先放下一根腰子,再把自己割的麦子放上,两边的人再陆续割了、放上,等五个人每人放上一大把,后面的人正好可以捆扎。我娘割麦时,就是他们那一组那个带腰子的人。那次,她正起劲地割着,抬头看到一片空地,那其实是一眼井,村民怕冬天冻坏井沿,就在井沿上铺上些玉米秸再压上土,起到保护井沿的作用。
常去地里干活的人都知道这些,他们见到这样的情况都会绕行。我娘不知道,以为只是块空地而已,就不管不顾地冲着那空地过去了,一脚踏上去,她一下有了下陷的感觉,她心里说,坏了坏了,这下完了。好在那井里水不深,只到腰际.....我娘垂直下到井里,咋呼了几声,可惜井太深,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后面割麦的人隔了一会才赶上来,来到最后一根腰子附近,他们懵了:带腰子的人呢?他们往前走走,看到了井,也看到了我娘。他们跑回地头找来绳子,把我娘拉了上来。
看我娘惊魂未定的样子,他们让她回家歇歇。我娘回到家,换下湿透的衣服,心情也调整好了,她想:我在家也没事,还是回去继续割麦子吧。她又返回麦地,她的那些伙伴们还坐在地头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她呢。她把腰子挂在腰间,又带头割起来。她的同伴笑她:你看你啊,掉到井里捞上来也没少割一廉(刀)麦子。
到了谈婚论嫁时,有人撮合她和我爹,那时我家挺贫穷,为了促成这门亲事,我爷爷在我娘去相亲前,跟四邻五舍借了几个大瓮,又借了些粮食,等我娘相亲时,爷爷故意领着我娘去看那几个瓮和瓮里的粮食。我娘后来和我说,你爷爷那么做让我感觉挺好笑,我是喜欢你爹才决定嫁给他啊,与他家有没有粮食、粮食多少有啥关系?
我娘嫁给我爹后,又到我们村里做民办教师,直到1971年,执教九年的娘积极响应公社组织的“教师党员参加农村党支部”的整党活动后,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教鞭,接替老支书,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三)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村支书既要带领村民搞好生产,又要频繁地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参观,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总是带着几分生疏地看着早出晚归的娘。因为娘,我活在别人的羡慕中,我却是从心底羡慕别的孩子:他们可以吃娘做的可口饭菜,穿娘缝制的新衣,她们可以让娘把她们的头发梳成喜欢的样式。我却因为娘的忙碌,过早地学会了自理。
八岁那年,我学会了自己缝纽扣。十三岁,我在七十三岁的奶奶的指点下,学会了拆洗被褥,并从此浆洗着一家五口的衣物。我就那么快速地成长起来。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从教九年的娘竟从来没指导过我的学习。
娘没有教我学习,却用言传身教教会我做人。在村民的眼里,娘是个“官”,她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她那么实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论谁,不论公事、私事,只要有求于她,她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由此,她赢得了更多的信赖。
娘同样深切地关注着那些弱势群体。每逢春节前夕,娘便吩咐我和两个弟弟抬着篮子,里面放上两棵白菜、一罐头瓶食油、两瓢面,去走访孤寡老人。我永远忘不掉老人们看到我们时那感激涕零的表情。
在我的印象中,总是一身灰蓝打扮的娘是那么干练,利落,雷厉风行。我观察过好几次她处理问题的情形,思路那么清晰,语气那么委婉,却从不拖泥带水。我很少见她发火,却没来由地有点怕她。
在娘的领导和带领下,村里的变化很大,而且,村风极好。在我的记忆中,我村放电影最多、按电灯最早,买电视最早,邻里之间纠纷最少。
一九八七年,娘进了城,成了居委会主任,又风风火火地干了十一年。
一九九八年,娘退休。应该安享晚年的娘,遭遇了人生一次大的灾难——我们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失去了最爱的那个爱她的人,一向坚强的娘一时消沉下来。那是我们最揪心的日子。但很快,娘擦干了眼泪,为了我们,她毅然坚强地收拾起了悲伤。
娘独居的日子,正是我事业最忙的时候,我抽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娘。多少次离开娘时,我都能感觉到娘依恋的目光,但娘从来没要求我留下来陪她。她反过来教育我的女儿:“你妈妈那么弱小,工作又累,你要多疼她,不要惹她生气。”当女儿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我又一次感动于母爱的伟大!需要我照顾的娘,得不到我的照顾,却在尽她所能、无言地照顾着我。
现在,赋闲在家的娘,却很难闲的下来,时常地,我们会接到她的电话:“有没有时间过来吃饭?今天我烙了饼。”.......
娘里里外外地忙碌着,看不出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地位在她身上留下的影子,她成了一个最细腻、最周到、最热情的娘。
年轻的时候,总感觉我和娘之间隔着什么,现在,细看娘,感觉娘身上的闪光点象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娘的为人实在、处事扎实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将永远影响着我。

作者简介:杨爱武,笔名阿弥。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青年作协会员,市青年作协常务副主席,《淄博晚报》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淄博财经新报》、《文学现场十年》、《淄博声屏报》、《青岛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画报》《农村大众》等省内外报刊,多次在各级征文中获奖,有散文集《石榴花开》出版。多年来喜欢在名著里徜徉流连,以文字记录生活,在写作里不断修行,希望逐步完美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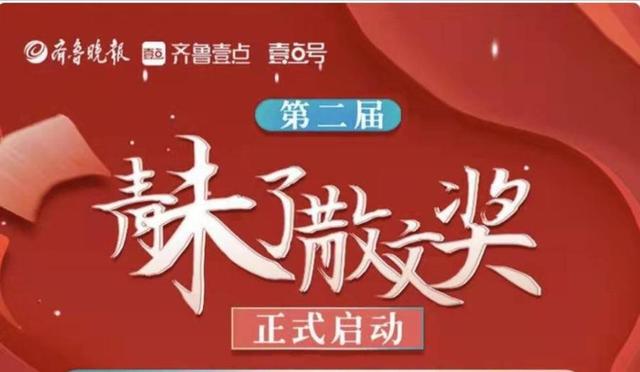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