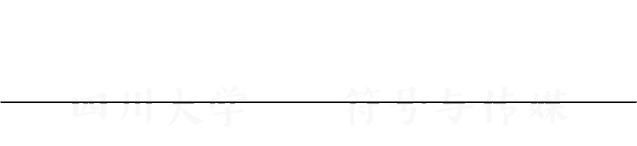

作者|赵毅衡
一 作为分类原则的文本意向性
本书“导论”给出了叙述的底线定义,分辨了与其他叙述学者定义的异同。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活跃于人类文化的各种叙述体裁,做一个全域分类。这个分类方式的基本标准,就是在符号学界称为“模态”,在语言哲学界称为“语力”,而本书称为“文本意向性”的文本品质。在进入分类之前,先介绍一下这个问题讨论的历史。
文本是体现了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组合,在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有一定的意向关系,这种意向体现为意义和时间的方向性:本书上一章在给叙述一个基本定义时指出,叙述文本被接受主体理解为具有“内在的意义与时间向度”,这就是“文本意向性”这术语的主要含义。所有的叙述文本,都靠意向性才能执行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和接收功能。
在展开讨论前,首先要说清楚的是:本书讨论的意向性,并不是人的心灵意向性,而是文本的意向性。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更有区别,这个问题的详细探讨,属于现象学的范畴,本书无法深入,我们只能先说清“文本意向性”(textual intentionality)是什么?至今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术语,但是不少人接近过这个概念。艾柯称之为“文本的意向”(text’s intention),他指的是作者的意向必须表现在文本中才能被解读。即符号学中所说的,在发送意义,解释意义之间,有文本意义。凯·米切尔则称之为“形式的意向”,她指的是文学文本形式具有某种意向性,她的想法与本书的讨论比较接近。
塞尔对此概念作过一个说明(虽然他没有用“文本意向性”这个词):“一般来说,为了解意向,我们可以问‘这行为者想干什么?’那么,他做一个声言时想干什么?他想用再现某物为某态,来造成此物为某态”。塞尔这话不容易懂,实际上却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靠再现(例如言语描写)某认为坏人,来造成此人是坏人的局面。这样我的言语描写就是文本意向性明确的文本。
因此,文本意向性,是符号文本表意中的品格,不是胡塞尔现象学说的作为“意识的基本品格”的个人意向性。但是两者都保持了这个术语的启用者布伦塔诺心目中的“朝向某个方向”的强烈意义。因此,文本用“意向性”以强调方向性,而不用许多论者选用的汉译“意图性”。
第二要说明的是,意向性是任何符号表意文本的普遍问题,因此本书的有关讨论,对一般符号学也有意义,只是在叙述文本中,这种意向性更加重要,也更加明显。本书的目的是,关于文本意向性这种看来抽象的讨论,最后可以落实到叙述文本的体裁分类上。
例如一段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游览海边的文字或影像,似乎是讲的是同样故事,在主导意向性不同的叙述体裁文本中,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出现于过去向度的记录(例如日记,书信,照片)中,是记录某段经历(例如恋情);
出现于现在向度的演出(例如戏剧、现场电视、游戏)中,是某种情景的当场演示;
出现于未来向度的许诺(例如旅行社广告)中,是某种可以期待的情景。
因此,文本意向性,是“文本自携元语言”的一个重要组分,也就是文本对接受者如何解释自己的要求。对于叙述文本的整体意义来说,文本意向性比单纯的情节内容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文本意向性看成是形式问题,至少在类型意义上,形式比内容重要,体裁归类决定意义。
赵宪章教授也说过一个他的亲身经历。2001年9月11日晚上他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看见大楼爆炸等壮观的警匪片场面,他觉得镜头做的很逼真。但是他想到《晚间新闻》不可能改放电影,再仔细看下去才发现时轰动性的新闻。他惊叹“文体类型错乱,能引发如此完全不同的认知!”他的结论是:所谓文类,其实就是文学的“先验形式”。
因此,各种“体裁”的一大不同点,是文本意向性不同。幸运的是,许多理论家讨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论者中有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分析哲学家,因此,关于文本意向性问题,现代思想史上积累的材料极为丰富;本书面临的困难是,论者各有各的术语,各有各的说法,论点散乱,甚至没有人用文本意向性这个术语。只有仔细剔抉,才能明白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而且,大部分论者讨论的都是命题,不是文本,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应用于文本的研究,更无人用此讨论叙述体裁的分类。本书的任务首先是一一梳理他们的看法,然后指出这些方向的诸多理论,只有加以延伸后,才能与各种叙述体裁构成相应关系。

本文出自《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由于篇幅原因,引用注释请见原书。
编辑︱田小梅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