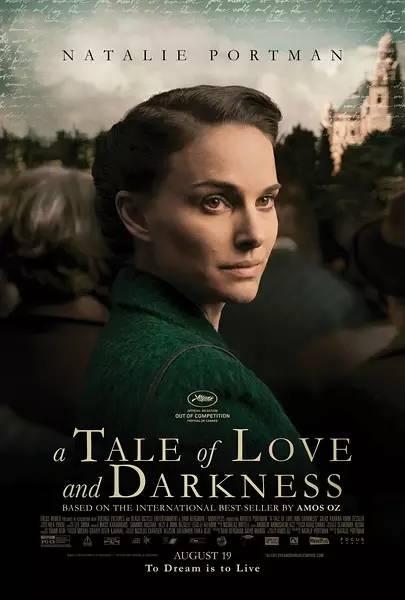十月份结束了。
十月的院线电影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爽快或美好的感觉,但从某个角度来观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影》中影子干掉了真人而夺权;《李茶的姑妈》中穷小子假扮成了女富豪;《无双》中穷小子给自己幻想了一个高富帅的分身,还把一女孩整容成自己暗恋对象的样子;《宝贝儿》中一个被寄养成人的弃婴试图拯救另一个弃婴;《找到你》中高级白领和底层保姆演绎了女性角色中母亲阶级分化的两个极端;《阿拉姜色》中没了父母的“儿子”和没了妻子的“父亲”半路一起踏上了朝圣之路。

整个十月电影中,人们都在纠结真与假、真人与替身,又或者说在对自我身份进行一种质疑、追寻和体认。当然,这些电影也都在身份、自我焦虑的背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弄假成真,假的比真的还真
张艺谋导演在《影》中再次拾起了自己最擅长的故事模型,杀戮的冷冽程度却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张艺谋一直在塑造二元对立,两男一女的三角结构,《影》的故事也如此,讲了一个替身窃权的故事。他在访谈中提到,“一说古装片,大家想到的都是帝王将相,我这次就拍一个平民,成为最后的赢家”。

可他只说了一半。
平民成为赢家的手段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是重回早期张艺谋电影的深层权力逻辑——父一辈是病老且性无能的,所以弑父、娶母、鸠占鹊巢,是三位一体的。比如《红高粱》《菊豆》。
年富力强的境州和孱弱病态的都督,与“我爷爷”和麻风掌柜没啥区别。
极度压抑而焦灼的年轻人,去弑父(旧体制),最本质上采取的是强权手段(更年轻更有力的活下来了)。

只不过《影》比早期张艺谋电影有一些变化,早期电影的元权力者是不出场的,到了《影》中都摆在台面上了(另外,《英雄》的时候王是运筹帷幄的,现在王也被裹挟了)。
不出场,容易抹杀观众的道德感知。所以我们对《红高粱》中的“我爷爷”不容易产生认同的心理,因为毕竟对方是一个未出场又患了麻风病的老掌柜。《影》就不行了,我们强烈感知到了恶。
如果说《影》是弄假成真,那么《无双》便是假的比真的还真。

作为国庆档完成度最高的类型电影,《无双》处处都是真与假的缠绕、真人与替身的互噬。比如李问和他的幻想分身吴复生、秀清和阮文,比如电影中的台词“你的加拿大警官死了,你找的下一个也是替身?”
这部电影给人压抑的地方在于那种随处可见的焦虑感。“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梵高,其他的都没有价值。”“你和世界上所有人一样,是观众,主角没你的份。”
所以,一个卑微的穷小子选择制造伪钞,后来在警察面前编造了一个自己的分身试图脱罪。在幻想中他变成了高富帅,得到了小组成员的认同,找到了认同感和成就感。他甚至还将一个女孩整容,复刻了一个自己的暗恋对象。他一切的行为逻辑是“假的也比没有好”。
黄粱一梦,纯属意淫
开心麻花在《李茶的姑妈》中依然是用“金钱与欲望”的主题、戏剧冲突强烈的身份错位情节、反智的笑梗做文章,但这次穷小子假扮女富豪的故事,却达到了一种令人极端厌恶的地步。

黄沧海是一个底层小职员,他一直为大渣集团勤勤恳恳地工作却得不到提拔,女朋友也跑了,于是他为了升职和50万奖金假扮李茶的姑妈。而李茶,是一个爱上了富家女(尽管即将破产)的穷小子,只有姑妈能助他赢得富家女。
总之,这部电影的基本逻辑是,没钱没人爱,有钱人人爱。
它塑造了一个人人可以意淫的女富豪莫妮卡,随时随地都会有人蹦出来说要娶莫妮卡。而且,达成娶富婆的方法可以说非常反智和低俗了——争先恐后去睡她。
与《西红柿首富》一样,我完全不认同说《李茶的姑妈》也是在讽刺批判金钱。底层的穷小子黄沧海,看似是慷慨激昂发表了一番批判金钱的演讲,但结尾明目张胆地攀爬上了美女富豪。非常打脸了。

《胖子行动队》和《李茶的姑妈》非常相似,都是一场屌丝青年的白日梦。这部电影,因为凸显的是主人公是个“无能胖子”的身份焦虑,所以主题不聚焦在金钱上,而聚焦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自我认同。所以编造了一个非常低龄化的、毫无信服力的两个胖子联手侦破贩毒集团的故事。
另一方面,因为包贝尔饰演的是个已婚的胖子,所以底层屌丝性压抑的问题转而到了文章饰演的胖子特务J身上,因此电影中充斥着特务J意淫朋友妻的低俗桥段。
救赎的可能性
《找到你》、《宝贝儿》、《阿拉姜色》告诉我们,抛开艺术水平的高低,至少还是有人在态度端正、用心地做电影。
这三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提供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找到你》在高级白领女性和悲惨女保姆身上,毫无说服力地给了一个想象性的抚慰。
在《宝贝儿》中,杨幂饰演的江萌和被抛弃的婴儿构建出了一种循环和对照,电影中她也不断地问警察“孩子妈妈怎么说”,像是在追问为什么自己会被遗弃。与前面提到的几部电影都不相同,《宝贝儿》讲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抛弃者,电影里面的人物也都是被抛弃的,比如收养江萌的母亲、聋哑的小军。

这部电影中,江萌有多重困境,救小弃婴、找工作、年满18岁要和养母分离。而要不要办理残疾证来更容易地找到工作的设置很有意味,而她想要坚持“我是健康的”这一点,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表现,尽管最终不得不妥协了。
《宝贝儿》没有提供出路,但《阿拉姜色》是真正提供了救赎的。
男孩诺尔吾与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在学校打架,话少自闭,不受继父罗尔基的待见,他的眼神总充满倔强和愤怒。从诺尔吾气喘吁吁爬上高处看到拉萨(如电影台词所说,看到拉萨等于看到自己),到洗脸剪头发,再到拿出粘好的父母照片、给继父烧热茶,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最终在朝圣之旅中重新建立他们的情感纽带。

无论是想象中朝拜西藏,还是白日梦带来的替代性满足,都是安抚现代人焦虑的一种手段。金钱与权力,成功与爱情如何获得?选择做舞台上的主角还是庸常的普通人?这是十月电影的灵魂拷问了。
电影中的拷问或者说分裂,跟当下的社会生态是一致的。
在这些电影中,尽管也有重新进行自我体认的,但更多的是折射了当下底层普通人对颠覆阶级固化的一种心理诉求,无论事业还是爱情,他们渴望寻找自尊、认同和成功,渴望有主角光环。与这些相比,是非与真假早已不重要。
80年代没有“我爸不是马云”的抱怨,而当下我们不是质疑和不认同上升渠道的机制,而是痛恨自己不在那个机制里面——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
很多人痛恨自己没有机会,所以电影里才创造了机会。
【文/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