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正在经历的乃是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都是这曲悠长的“时代恋歌”的歌手与听众!那么,我们能否谱出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那样的学术长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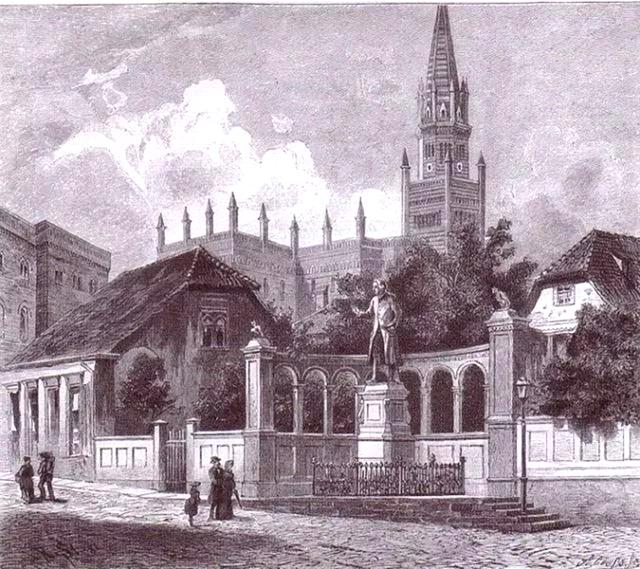
原文 :《“寂寞之原则”与“纯粹之知识”》
作者 | 同济大学 叶隽
图片 | 网络
1925年,陈寅恪留德归来,任教清华;两年之后(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又两年(1929年),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最重要规训之一,也是在现实语境中最值得遵循的基本学术原则。弹指烟云,距静安先生之死近乎百载,寅恪先生墓木之拱亦逾半个世纪,而前贤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学术究竟若何?
笔者以为,或许可以补充的是“寂寞之原则”(das Prinzip der Einsamkeit)与“纯粹之知识”(das Wissen der Reine)。至少对于学者(广义)来说,读书治学,其若立志弘道,探寻真理,固然当持守独立之精神,以依已不依他的果决和坚毅知海扬帆、百折不挠;固然当放飞自由之思想,以海阔凭鱼跃的从容和淡定学山辟径、如风游弋;但若无寂寞之原则,必然难以脱俗于滚滚红尘;若无纯粹之知识底气,则必然会困于功名利禄之重重羁绊。而如果没有对“纯粹之知识”的向往与执着,则更不能在当下不乏焦虑、悖论和仓皇的语境中突出重围。
源自德国学术的“纯粹”追求
陈寅恪先生的主要知识资源来自德国,如此强调德国学术,不仅因为德国在历史上确实曾经以柏林大学及康德、费希特、兰克等伟大学者而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场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所构筑的“学者共和国”(Gelerhtenrepublik)理念成了一种可以引领知识世界的导向性思想。

相对于“精神”(Geist)、“思想”(Gedanke)这类更容易让人饶感兴味的核心词,“原则”(Prinzip)与“知识”(Wissen)无疑略显平淡,但绝非不重要。前者的好处在于振奋精神、激扬意志,但也容易让人陷入过于蹈虚踏空的困局中,所以需要有更为坚实、可以支撑的基础性架构。作为学人,我们应确立的思路是“循原则”“求知识”。大道所在,本是万物共生共享,那么如何能在普遍性基础上建构起学术之道,则是一流知识精英不能回避的问题,如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批判”的路径和方法:“我之所谓批判非指批判书籍及体系而言,乃指就理性离一切经验所努力寻求之一切知识,以批判普泛所谓理性之能力而言。故此种批判乃决定普泛所谓玄学之可能与否、乃规定其源流、范围及限界者——凡此种种皆使之与原理相合。”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将“批判”(Kritik)概念上升到一种“元方法”的理论高度,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一直作为西方知识世界主导原则的理性的自我反思,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但他还是未能进一步上升到二元架构的高度,即“理性—感性”的基本结构中来看问题,也就是“秘索思—逻格斯”的框架之中。尽管如此,如果将“批判”视为可能介于其间的流力因素,则未尝不可寻得第三维开出的蛛丝马迹。康德接着说:“盖此等著作者承当能扩大人类知识于可能经验之限界以外,顾我则谦卑自承此实为我之能力所不及者。”康德之卓越,在其能自知限止之处,与黑格尔之僭越恰成对照,他直承将探究之范围局限在“理性自身”与“理性思维”,将后者又界定为“纯粹思维”,正是这种对于“纯粹”的追求,乃可以进一步阐释“纯粹理性”的概念。康德对于“纯粹理性”(当然还有“实践理性”等概念)的诉求,表现出一种锱铢必较、深入底里的学术态度,这恰是德国学术之所以为德国学术,能成为一度引领现代世界的大纛之根本原因所在。不妨继续延伸,拓展出“纯粹之知识”的原则,这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为中国现代学术甚至世界学术提供根本的学术伦理原则。

在“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提出的两年之后(1931年),陈寅恪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强调:“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并一一拈出中国学术之弊病:“——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实际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国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这就意味着,其实大学职责的命题,并不仅针对学者个体,还有着更为高远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甚至是国家学术的考量,是具有文明史建构意义的“纯粹学术”。
“寂寞”的特殊价值
一般而言,物质量化相对容易,而随着时代发展,知识量化似乎也是一种趋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科学知识的增速是极为惊人的,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测算为:“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20世纪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近10年大约每3年增加一倍。”面对如此浩如烟海的知识及其无限扩展的增量与速度,任何一个个体在有限的生命中都不可能穷尽其涯。在知识的无边海洋面前,若对于其壮阔瑰丽的奇伟没有一丝敬畏之心,那只能被视为无知无识,或者是无耻。学术的谦逊本是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美德,可充斥今世的不少是自吹自擂、胡言乱语、毫无底线之人。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廉耻》),或可模仿一句:“学人之无知,是为无耻。”因为无知,所以利欲熏心;因为无知,所以自甘堕落;因为无知,所以曲学阿世;因为无知,所以没有底线……

与“独立”“自由”等稍显高端的词汇相比,“寂寞”“纯粹”无疑更显得边缘与孤独。可正是这样的比照凸显了这类核心词的特殊价值所在,因为这种寂寞,既可以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的宇宙感知之大,也可以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的英雄事业之难,还可以是“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王国维《临江仙·过眼韶华何处也》)的士大夫的忧患情怀,说到底,这些与现代学者的孤守自持也都是相通的;而所谓纯粹,则既可以是“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唐·白居易《除夜寄弟妹》)的纯真亲情,也可以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的洁身自好,还可以是“体素储洁,乘月反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崇高雅洁……
至少在当下,我以为在承继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前贤认知,认真思考这一学术伦理问题甚有必要。“寂寞之原则”与“纯粹之知识”是否值得作为学术伦理原则,以及可否承担起时代的学术与精神使命有待历史的检验,好在历史既有精英的琴孤引领,也有大众的曲欢相和,两者究竟以怎样的互动关系推动历史的行进,无疑也是对作为高端知识的学术伦理原则的重要考验。所谓“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我们正在经历的乃是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都是这曲悠长的“时代恋歌”的歌手与听众!那么,我们能否谱出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那样的学术长歌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