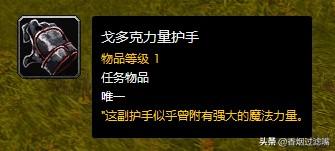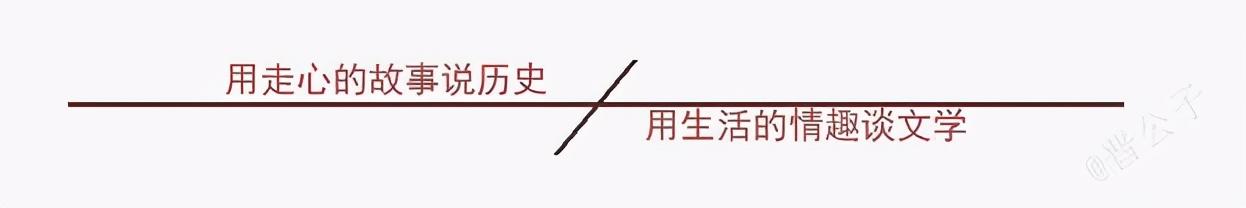

本期话题
今天,我们提到《诗经·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几句诗时,总把它视作祝福新婚的甜蜜誓言。可是在《诗经》当中,这四句诗却蕴藏着一个国破家亡、恋人分离的悲伤故事……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一场又一场婚礼。每逢此时,主持人总要在聚光灯下热情洋溢地朗诵《诗经·击鼓》里头的这四句诗,祝福大婚的新人。
只是新人们和观礼嘉宾沐浴着幸福喜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四句诗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要打开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钥匙就在“死生契阔”四个字上。这四个字该怎么解释,自古以来,众所纷纭。
影响最大的《毛诗传》说:“契阔,勤苦也。”《毛传》所理解的“契”,大概就如《小雅·大东》“契契寤叹”之“契”,作勤苦讲。
而“阔”字则很可能被当成了“活”的通假字。“活”有流动之意,照《毛传》的意思串讲诗文,大意该是“生生死死,奔波亡命之际,我仍记得当初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是《毛传》的解释有个问题:《击鼓》的下一章说: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如果“阔”字是“活”的假借,那“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就变成了“于嗟活兮,不我活兮”。“活”字不但重复两次,而且还要分训二义。怎么看,这都不近情理。
更别提“死生契阔”的“契”,照《经典释文》说该读作“qiè”,而“契契寤叹”的“契”却读作“qì”。汉字的造字原理本是因声以求义。读音差别这么大,字义是不大可能相同的。
汉代四家诗中的《韩诗》一派对“死生契阔”另有说法。《韩诗》说“契阔”当作约束讲。这一派学者大概是将“契”视为“絜”的通假,而以“阔”为“括”的借字。无论“絜”还是“括”,都有约束的意思。这样一来,“死生契阔”四句就成了“从前,我与你定下生死之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可是这个解释照样是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阔”如果通作“括”,训为约束,那“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岂不是成了“哎呀,拘得我如此难受,我不活了”!这还成什么话呢?
其实,要想从字面儿上把这四句诗串讲一通,并不需要像《韩》、《毛》那样迂曲为释。“死生”既是对文,“契阔”也不妨作对文看。“契”训为合,“阔”意为疏。“死生契阔”便是生离死别,聚散分合的意思。
只不过从下一章“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反推,诗人只言分而不及合;只说死而不论生。“死生契阔”似乎只好做偏义词罢了,也就是有死无生,有分无合而已。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层,朱子索性读“契”为“锲”(割裂之意),于是“死生契阔”便成了“生死永诀”。
在不少人心里,“死生契阔”云云,该是像美国电影《恋恋笔记本》那样的故事——一对真心相爱的青年男女经历风风雨雨,携手到老。直到最后紧紧相拥,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可在我的脑海里,这四句诗勾勒出来的却是另一幅场景。它像法国电影《漫长的婚约》:年轻的马蒂尔德在一战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没有盼来未婚夫曼尼奇的荣归,反而接到了他阵亡的噩耗……

之所以我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因为诗人在《击鼓》的第三章里写道: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毛传》解释这四句诗说,“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换句话说,男主人翁正置身于一支行将分崩离析的军队。军律已然名存实亡,根本约束不了人心惶惶的士兵。开小差逃跑者有之,心思懈怠以致战马遗失者亦有之。
要知道,这支来自卫国的军队此时正远离本土,在南方的陈国境内与宋军厮杀。孤军南征,构兵异域本来就是极其凶险的事儿,更何况此时久役于外,以致厌战的情绪泛滥于全军,上无约束而下有败形。
难怪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主人翁会向远方的爱人发出绝望的吶喊:“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卫国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而陈国远在淮阳。卫国为何发兵入陈?它又为了什么非要和殷宋在陈地刀兵相见呢?要厘清这里头的来龙去脉,我们的话题还得从公元前597年的清丘之盟说起。

也就是在那一年,不可一世的楚庄王兵锋北向,在邲之战中一举击溃晋军主力。晋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以来辛苦建立的中原霸权无奈易手。
为了阻遏楚国的进一步北侵,晋国收拾起自己的残余势力,与仅剩的几个同盟国宋国、卫国和曹国在清丘举行会盟,签订了“恤病,讨贰”(即一国有难,相互救援;共同出兵,讨伐叛逆)的同盟条约。
只是《左传》的作者说,签约各方心怀鬼胎,并不是真的同心同德。起码,在同盟书上签字画押的卫国执政孔达是别有打算的。因为不久之后,由宋国引发的一场军事冲突暴露了孔达的心思。
清丘会盟刚一结束,宋国就出兵讨伐楚国的附属国陈国。此次出兵攻陈,宋国很可能是为了报复南楚。因为就在前不久,楚国刚刚灭掉了宋国的与国萧国。
按照清丘之盟的约定,宋国兵发淮阳,作为盟友的卫国应该遣军与它并力作战,可卫国执政孔达不但拒绝援手,反而出兵救陈。对自己吃里扒外的决定,孔达振振有词地向宋国解释道:
“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孔达的意思是,卫国先君卫成公(实时任卫君卫穆公的亡父)与陈共公那是老交情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万一召集清丘会盟的盟主晋国不能理解卫国的这份儿苦衷,我孔达一身任之,有死而已。
话说得虽然大义凛然,有情有义。但在晋景公听起来,怕是有些玄外有音呢。
孔达口里的卫成公是什么人?40年前,晋国公子重耳流亡诸国,过卫之时曾遭到过成公之父卫文公的羞辱。而成公继位之后,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爆发城濮大战,他又左袒南楚。
楚军攻宋,晋军要求借道卫境,南下援宋;成公不允;晋国要求卫国与自己联兵援宋,成公又不允。
父子两代卫君铁了心要与晋国为难,晋文公怎能不怒?于是城濮战后,文公挟战胜之余威,用武力将卫成公赶出了卫国。甚至连周天子亲自出面替卫成公求情,晋文公也不买账,密令手下人鸩杀卫成公,差一点儿就把他药死。
说到底,晋、卫两国的矛盾并不是晋文公与卫成公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卫国趋红踩黑,不甘心在晋楚争霸的夹缝里选边站队,死心塌地做晋国的附庸。尤其当楚国势力大张,深入中原的时候,卫国对晋国的态度就会越发暧昧起来。
城濮之战让晋国掌握了中原争霸的主导权。可时间转到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已经在邲之战中还以颜色,摧败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在这当口,卫国执政孔达口称成公遗命,公然背弃清丘盟约,发兵援助楚国的附属国陈国,焉知道他不是要改换门庭,向楚国缴纳“投名状”呢?
邲之战创痕未愈,自己的小跟班儿居然又要反水!收到消息的晋景公勃然大怒。他遣使入卫,扬言说:
“罪无所归,将加而师!”
——《左传·宣公十三年传》
如果卫国不就背盟投敌的行为作出解释,不惩办相关的责任人,晋国就将对卫国宣战。从《左传》简短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此时卫国国内的民心舆情,但《邶风·击鼓》这首诗却以一个普通卫国军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战云密布之下,卫国国民普遍的恐惧心理: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诗·邶风·击鼓》

卫国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同时与晋、宋两大强权开战。所以晋国使者一旦发出战争威胁,卫国举国上下便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国都帝丘和重镇漕邑纷纷开始加固防御工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是卫国首先擂起了战鼓,派出了军队。
从诗人的语气看,他似乎对执政孔达出师援陈的决定颇有微词,埋怨他不自量力,与两大国构衅。而更让诗人忧心如焚的是,此时帝丘和漕邑都已经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了,可他自己却和卫军主力一起深陷在陈国战场,不得抽身回援。
国内已是危如累卵,人心惶惶,而入陈的卫军又久役厌战,军心涣散。假如此时晋国真的出兵攻卫,恐怕诗人“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的预言就将成真!
幸运的是,卫国执政孔达兑现了自己出兵之前的诺言:“若大国讨,我则死之”。他用一根白绫自缢身亡,向晋国谢罪,将自己的祖国从战争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马蒂尔德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看着他。在温暖的微风中,在花园的阳光下………,马蒂尔德看着他,她看着他,她看着他……”
虽然《击鼓》也像《漫长的婚约》一样,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与恋人分别的沧桑,但或许,远征陈地的主人翁还能幸运地活着回来,再见到他的“马蒂尔德”吧……

参考文献:
黄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孔颖达《毛诗正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