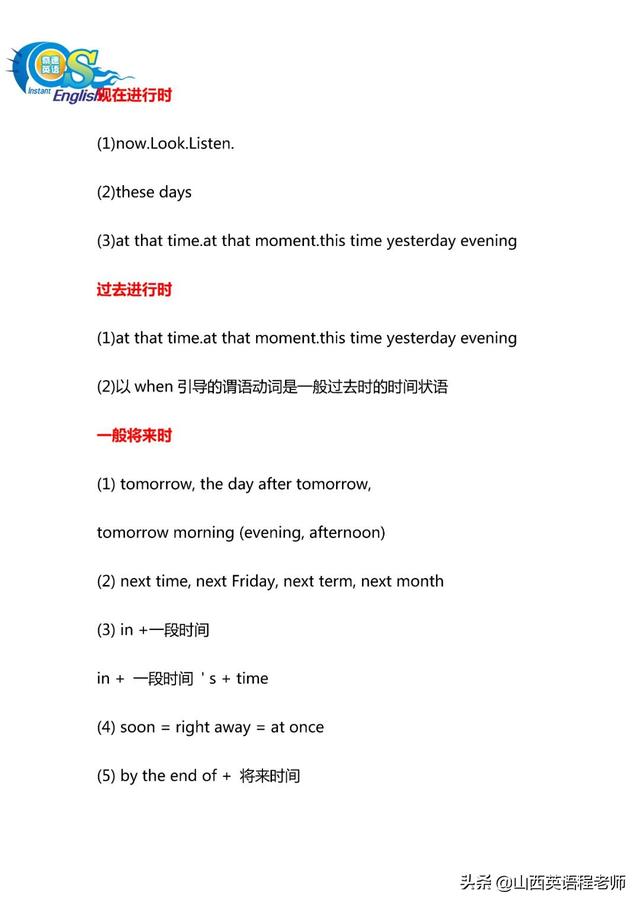“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怒吼秦腔,晊一碗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每回我把这几句哇哇一唱,就是想着要吃碗擀面。等把面擀了,吃了,喝碗面汤,心里那点儿自满还得“哇哇”几句秦腔才顺畅:“吃好了,喝胀了,就跟皇上他大一样了。

离开老家好多年了,自个儿擀面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有一年,我在老家削了根擀面杖带回来。擀面杖自然是硬木头的好。定要等木头干透再削,不然会弯、会裂。擀面杖哪怕弯一点点都不好使,擀出来的面条会薄厚不均;倘是裂了,也擀不好面。前两年有位博士写了篇论文,说擀面是一场非线性力学行为,擀面杖不合格,这个力学行为就不成立。
这根擀面杖带过来几年,一次也没用过——没有面板。可带过来了就像给自己留了一个伏笔,等着能有一场启发。有一次,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张图:一个面团,一簇面条,一碗酸浆水。这像是一个甩出千里的鱼钩,也不知怎的就钩着我了,我大口大口地呼气,老鱼吹浪似的,心想非得干点儿什么。于是,飞快上网去淘,下单买了面板又买了面盆、面碗、面粉。
事情就这样成了,一碗擀面吃得我百感交集,喜气洋洋。小学生写作文的结尾喜欢写“春天真好呀”“同桌真好呀”“老师真好呀”,换我来写:“面板真好呀”!老家人做面讲究“三光”。盆光,面光,手光。其实,这不是说擀面,是说和面—水多了,无论如何也光不了,面粘手;水太少,面不成团,自然也光不了。说起来简单,真要“三光”,得有个熟悉的过程。

好在,我从小看祖母擀面。但祖母绝大多数时候擀的不是白面。我们那儿都是山地,小麦长得不好,平时白面省着吃,逢年过节才能擀。祖母有双巧手,平时吃的玉米面黏性差,可祖母能用它擀出长面,她用一种我们叫“阳桃”的植物的根磨成的粉来和面。“阳桃”的学名叫黄蜀葵,人们每年都种,纸厂收去做“纸药”,黏性好。祖母有了这个,有如神助,擀成的面条断不会瘫软,并且很有嚼劲。我偶尔吃上那么一碗,是要跟陈老师说一声的:“我也吃面啦!”陈老师刚从师专毕业分到我们这儿时,穿个喇叭裤,白色的的确良褂子,洋气得让我们抬不起头。可她总是站在讲台上,我们
不能不多看她两眼。另外,她从我们身边经过,身上有股像刚磨出来的面粉味道的香味,好闻。陈老师吃食堂,师傅总要问她今天吃啥。她有时说“酸菜面”,有时说“油泼面”,有时说“面皮儿。吃商品粮嘛,我们眼羡啊
不久,陈老师和吹笛子的王老师恋爱了,他们缓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像神仙。过了一段时间,这二位不吃食堂了,自个儿做饭。不知谁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啪啪啪,捣大蒜,你烧火,我擀面。”我们都学会了,集体喊叫,陈老师听到就脸红。当时只是觉得好玩,长大之后才觉得这几句话里的烟火气竟是那么迷人。就如同收麦子也有烟火气,那么多锋芒,来不及避开,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搂进怀里,从古至今,都这么搂过来的。丰收总是令人开怀。

北魏农书《齐民要术》里说面条叫“水引饼”:“授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授令薄如韭叶,逐沸煮。”这是在扯面条。到了唐宋人们又管面条叫“汤饼”。
唐代时,家中添新丁要吃面条。刘禹锡有诗:“举箸食汤饼,祝辞添麒麟。”宋代苏东坡也有两句:“甚欲去为汤饼客,唯愁错写弄獐书。”他开玩笑说,添新丁了,想去你家吃面,可是我把“弄璋”写成“弄獐”了。这原是唐相李林甫的段子。
后来,人们过生日要吃一碗长寿面,好像也顺理成章了。
擀面杖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根木棍与面团那叫一个相得益彰,自此便相依为命了。
好多小说喜欢描写女人擀面,男人觉着好看,于是两情相悦,吃嘛嘛香。其实,最好看的是年轻妇人擀面,小孩儿嗷嗷待哺,妇人实在腾不出手来,直到小孩儿哭起来,这才蹲下来,帮着擦眼泪,结果面粉留在孩儿脸上,粉扑扑的,可爱极了。
张爱玲在杭州“楼外楼”吃了一碗螃蟹面,“吃掉浇头,把汤滗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有点造孽”。她没吃面条。她这个做派和袁枚很像。袁枚说面要汤多,碗里看不见面才好,汤是用鳗鱼熬的。李渔不这样想,他在《闲情偶记》里说:“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饮汤也。”这般,他家做“八珍面”待客,“五香面”自用。只是那么多食材放在面粉里来和,好不好擀呢?
“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虽说这句是尤三姐笑骂贾琏的——别以为你干的丑事我不晓得,可用在吃面这事上,却也很恰当:面是面,汤是汤,不杂七杂八,清清楚楚的,才算得上一碗好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