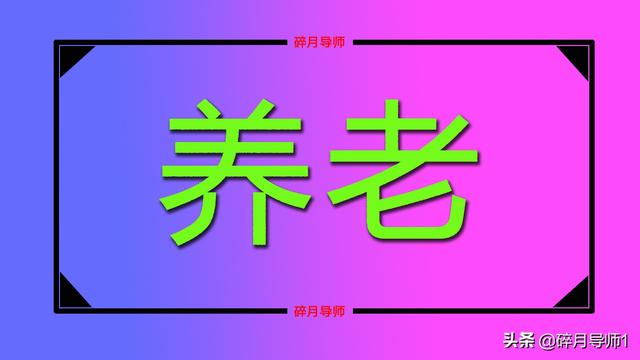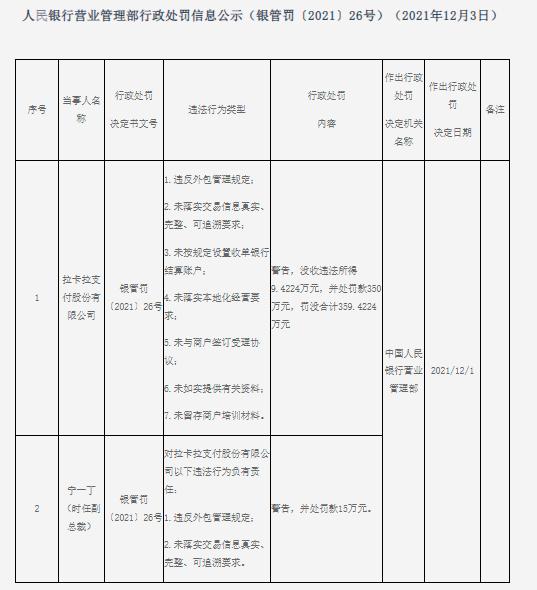(文学与新闻学院作者:吴艳函)踏平坎坷艰难寻‘它’,埋进深山志在高远——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南仁东老先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南仁东老先生
(文学与新闻学院作者:吴艳函)踏平坎坷艰难寻‘它’,埋进深山志在高远。——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他的政治面貌一栏写着“群众”——不是党员,甚至不是团员。像万千星河中的一簇光亮,亦或是滔滔江海中的一缕细流,闪耀或奔涌都是无声的,却带来希望,滋润涸辙。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在贵州省平塘县的喀斯特洼坑中落成启用,并开始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电磁波。南仁东拖着病躯飞赴贵州,亲眼见证自己花费22年心血养育的工程落成。而在2017年9月15日,他便因肺癌突然恶化,与世长辞——还有十天,就是FAST的“周岁宴”。如果突如其来的变故没有夺走这位老人的生命,他大概会和基地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吹一根蜡烛,分一块蛋糕,庆祝FAST的一岁生日,遥望射电工程的美好未来。
不知道这个特殊的孩子有没有收到宇宙深处,来自自己父亲的生日祝福呢。 南老逝世三年有余,我们却从未忘记这位人民科学家。在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遐思飞逸,在荒芜的洼谷中测量选址,在精密的实验仪器间穿梭操纵,在狭窄的病床上翻覆牵肠……南仁东先生所留下的,远不止FAST,还有心无旁骛的专注态度,精益求精的至高追求,坚守本心的奉献精神和鞠躬尽瘁的家国情怀。他用22年时间,书写了中国科学史的又一奇迹,也在炎黄子孙心中,留下了瑰丽诗篇。
“咱们也建一个吧。”
时年48岁的南仁东并不年轻了,但此刻他的眼中跳跃着如同少年般鲜活的期冀。
1993年的中国并没有发达的科技傍身,像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多种多样的营养。别国的科学家们就全球电波环境恶化的问题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地讨论着如何深化研究,推进相关科学设备的进一步建设。南仁东和他的同事们却要思考,如何让建造射电望远镜在中国从可能成为现实。
1994年7月,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提出。
在此之后,便是二十二年的坚守。
前文提到,彼时中国的科技并不发达。而FAST的选址在没有科技辅助的情况下,是难以推进的。
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后,南仁东及其团队便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奔赴贵州。那时候没有高铁,冒着蒸汽的绿皮火车便载着他从北京到贵州,再从贵州回北京。单程近50个小时,往返便是四天,不知不觉,就是四千个日日夜夜。路途的辛苦不必赘述,寻址也从不是轻松写意的游山玩水——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南仁东去遍了每一个无人到访的角落。崎岖坎坷的山路已经习以为常,禽鸟野兽的造访也屡见不鲜。南仁东如同科学界的苦行僧,终日以石为枕,以地为席,先后对比1000余个洼地,才找到FAST的“家”——大窝凼。 “这里好圆!”站在窝凼的正中间,南仁东向上看去。天地被包裹在圆圆的凼口中,他却更感宇宙无垠,星河浩渺。 选址完成,设想距离落实更进一步,南仁东却没法放心——没有钱,所有努力都是打水漂。初期勘探结束后,昔日的工作伙伴们大多回到原先的岗位“重操旧业”,只有他奔波劳碌,跑遍中国寻求一丝契机。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的立项申请书上,光是合作单位就有二十多个,足足三厘米厚。为了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实,他想方设法多参加国际会议,像个不成熟的新手父亲,急于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孩子的好。
“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
南院长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收获一片叫好,无数掌声。但究竟遭了多少白眼,承受多少打击,除了他,没有人知道。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大会,南仁东不待点名,便抢着向路甬祥院长喊话——要名分,要钱!一一得到允诺后,他在国际评审中用背下的英文稿子表明了自己的诉求,被国际专家开了个小玩笑:“英文不好不坏,别的没说清楚,但要什么说得特别明白。”
恶意的嘲讽和故意的冷落再也不能阻挡前进的步伐。南仁东冲破一层层的桎梏,将流言甩在身后,历时13年,让FAST成为“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被提上日程。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核心技术遭遇封锁……建设射电望远镜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项目启动后,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南仁东愈发忙碌,他不仅要参加每一次会议,听取每一条意见,还要去亲自审核每一张设计图纸并提出修改意见。工作量之大,工作内容之繁杂,实非常人力能及也,南院长却坚持事事亲力亲为,担任着团队的主心骨,为每一个焦躁的失望的灵魂打下定心针。他自称“战术型老工人”,长期待在施工现场,睡工棚,跑工地,爬高塔,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一线建设。那时的南老已经年逾古稀,仍能为了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迸发出如此高昂的热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学习过程中轻易喊苦喊累呢?
“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他这样说。“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轻描淡写的语气里,是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为了“面子”,他在罹患肺癌,手术伤及声带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为了“面子”,他在100米高的塔架爬上爬下;为了“面子”,他带领团队从跟踪模仿大步迈向集成创新……正是“要面子”,才换来了FAST的高性能和高创新——与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FAST的灵敏度提高约10倍,与阿雷西博望远镜相比,其综合性能也提高了10倍。同时,FAST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利用变形反射面工作的射电望远镜。这些成就,是22年的焚膏继晷换来的,是以南仁东为领导的一代科研工作者们用自己最灿烂的年华交换来的。
2016年9月25号,FAST工程如期完工,与项目批复的工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好2011天。南仁东再次回到大窝凼,仰起饱经风霜的面庞,望向星空。
宇宙无垠,星河浩瀚,却不再如镜花水月般难及。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不远的未来,宇宙终会传来回信,为这项辉煌的工程添一笔浓墨,绘一片重彩。
有人痛恨病魔的无情,为南仁东先生的逝去扼腕叹息。我也为科学界巨星陨落而哀伤,却想起南老的乐观,又记起天文学的浪漫——
会不会“中国天眼”发现的240余颗脉冲星里,有一颗是南老的化身。即使在人间的躯壳长眠地下,崇高的精神却在更深邃广袤的银河里,永恒发光,为科学工作者们指引航向,为我们在未知的黑暗里点亮一束光。
斯人已逝,令他魂牵梦萦的大约只有FAST。
(责任编辑:朱琴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