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秋》学与柳宗元古文的论辩艺术*

文/谢琰
内容提要
经学影响文学,应有“观念影响内容”和“思维影响表达”两条路径,学界通常重视前者,本文则重视后者。柳宗元积极接受新《春秋》学并应用于古文创作。新《春秋》学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柳文论辩艺术,藉由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运用及相互关系而呈现出来。柳文常以“生人”为论辩立场,以“去名求实”为论辩技巧,皆从新《春秋》学的思维方式转化而来。柳宗元还将新《春秋》学的征圣意识,树立为古文的主要论辩目标,由此表达了对判断力的重视,区别于韩愈对价值观的强调。韩、柳的思想分歧,与两人古文论辩艺术的差异密切相关。廓清新《春秋》学与柳文之间概念相沿、思维相传的轨迹,既是探索经学研究的新可能,更可提供作家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柳宗元 新《春秋》学 论辩艺术
中唐前期,除了官修《五经正义》持续发生基础性影响之外,经学发展的概貌可由李肇所述的代表性学者窥知:“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①]其中,啖、赵、陆的新《春秋》学最具创新性,在当时政治界和学术界影响最大,留传后世的著述也相对充实,堪称中唐经学中的显学。学界已经论述了新《春秋》学与柳宗元的思想及古文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②],但这些被发现的联系,往往停留在人际关系层面或观念层面;而观念层面的联系,通常表现为“经学观念影响古文内容”这样一种较为直接、醒豁的路径。事实上,相比于有限的几部经书,经学对文学的影响更复杂、更深刻、更曲折。经学不仅包含一系列知识与观念,而且包含特定的阅读、思考、写作、行事的思维方式;该方式常常支配了很多政治行为和文化活动,如果形诸语言,则会造成特定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经学影响文学应该具备“观念影响内容”和“思维影响表达”两条路径。
笔者在反复阅读柳集的过程中得到一个鲜明印象:柳文的各种体裁中都包含大量论辩内容,论辩对于柳宗元而言不是几种特定文体的特征,而是特定思维方式的普遍应用,是特定表达方式的自觉磨砺,不妨称其为“论辩艺术”,以区别于古文研究通常使用的狭隘的“论辩文”概念。在施展论辩艺术的过程中,柳宗元持续、严谨且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具有特殊内涵与特殊用法的概念,这些概念往往来自新《春秋》学,或至少同样被后者频繁使用。正是这些特殊概念的存在及其运用效果,使得本文的研究企图成为可能:笔者希望在新《春秋》学与柳宗元古文之间,建立一条“思维影响表达”的新路径。为了将有关“思维”和“表达”的研究落在实处,笔者借鉴了西方学界“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经验。“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和一般意义的“观念史”的最大区别是,它更关注思想的横切的、系统的、动态的一面[③],不仅关注概念内涵,更关心其历史运用[④],所以有学者将其等同于“历史语义学”[⑤]。如果说“概念史”是研究少数概念在多人手中的运用,以彰显历史发展的线索,那么本文则是研究多个概念在少数人手中的运用,以勾勒思维传导的轨迹。笔者认为,廓清新《春秋》学与柳宗元古文之间的深层关联,既是探索经学研究的新可能,更可提供作家研究的新思路。

一 背景与过程:柳宗元对新《春秋》学的接受
经学并不专属于经学家,一切士人都可以而且通常是必须拥有经学。柳宗元对经书及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学习,但对于新《春秋》学之外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新颖的应用兴趣。比如在《易》学方面,相比于刘禹锡的勤奋和兴奋,他的态度明显保守。他批评刘禹锡、董生没有认真阅读“韩氏注、孔氏正义”而随便相信毕中和、僧一行的学说,并认为所谓“新奇”之处“具在正义《乾》篇中”[⑥]。他还批评“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务新以为名,纵辩以为高”,认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⑦]。此种固守注疏的态度,必然阻碍《易》学深入影响他的思想及古文创作。他对待经学的其他方面,除了做出少量文本辨析工作,大致也无新锐之见。类似“柳宗元对传统的儒家章句之学则给以坚决的批判”[⑧]之类的笼统论调,可以休矣。因此,中唐虽是剧变时代,柳宗元虽是新锐人物,但真正影响他、造就他的经学因素,只是他所遇见的广大因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只不过,这一小部分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深刻塑造了他的古文创作。
中唐经学对柳宗元的影响,以新《春秋》学为主导,既是一种时代因缘,也是柳宗元的自主选择。目前学界对二者关联的研究,达成一些基本共识,集中体现于《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笔者根据学界成果,结合读书所得,对柳宗元接受新《春秋》学的背景与过程略作勾勒如下。
《春秋》学发展到唐代,《左传》学占主导而《公》《榖》之学衰微。在唐人谈论中,“所谓‘春秋’,有相当多的部分实际上是指《左传》”[⑨]。中唐新《春秋》学兴起之后,《公》《榖》之学才有起色,《春秋》学遂“变专门为通学”[⑩]。柳宗元之前的古文家,受《左传》学影响较多,每好以“褒贬之学”述史、论史。比如萧颖士感慨“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于是“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11]。权德舆《两汉辩亡论》则云:“予因肄古史,且嗜《春秋》褒贬之学,心所愤激,故辨其所以然。”[12]柳宗元的“家学”中,也沉淀着这样的学术基因和写作习惯。其父柳镇明晓“《春秋》之惩劝”,“作《晋文公三罪议》《守边论》,议事确直”[13],其堂兄柳元方“通《左氏春秋》,……嗜为文章,辞富理精”[14]。有意思的是,柳宗元族叔柳并与赵匡同为萧颖士弟子,权德舆和柳镇则在李兼江西幕府中为同僚[15];权德舆又与陆淳关系密切,且将新《春秋》学思想引入科举考试[16]。由此可见,对于《春秋》学的旧传统和新学说,柳宗元都享有便利的接受条件。就《春秋》学知识而言,柳宗元在贞元二十年(804)所作《祀朝日说》中[17],充分展现了自己对《左传》《国语》诸事的熟悉,而其古文中言及《春秋》及三传处亦颇多,不遑备举。从生涯前期的几篇古文《辨侵伐论》《驳复雠议》《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来看,《驳复雠议》据《公羊》说立论,而其他三篇皆批驳《左传》的观点或记录,可见就《春秋》学立场而言,柳宗元明显偏向《公》《榖》一系。而《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的论辩思路与现实指向,又显示了新《春秋》学的深刻影响。在中唐古文诸家中,柳宗元对新《春秋》学的学习最为精勤、深入、持久,他的相关古文创作,也就脱离了述史、论史的窠臼,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湛的论辩艺术。
在新《春秋》学三家中,柳宗元主要学习的是陆淳著作(陆淳后因避讳改名陆质,本文统一称陆淳)。根据《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的自述[18],他对陆淳钦仰颇久,后“执弟子礼”,陆淳《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对他影响最深[19]。这三部书在贞元十一年(795)之前就全部完成[20],所以它们对柳宗元的影响可以非常早,这是笔者展开研究的重要前提。《微旨》《辨疑》的作旨及体例有别[21],但基本内容不外乎三个部分:先列经文,再列三传传文,后附啖、赵、陆的辨正或新说。《集注》一书今虽不存,但根据书名及吕温《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所述来判断[22],应该也“汲取了啖、赵及三传的合理解说”[23]。就《微旨》《辨疑》来看,两书的具体写法正好构成互补。比如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一例,《微旨》主要是自立新说[24],而《辨疑》则针对《左传》和《榖梁传》逐条驳斥[25],一立一破,相得益彰。柳宗元对待《集注》《微旨》《辨疑》三书,应是相参阅读。《集注》或许最完备,《微旨》则最醒豁,《辨疑》则可用来解惑和补充。至于被当代学者视作新《春秋》学代表作的《春秋集传纂例》,反倒没有被柳宗元和其他陆门弟子提及[26]。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纂例》的体例:它打乱了《春秋》经传的顺序,按照书写辞例的类别而重新编纂。对于绝大多数唐代士人而言,以事件为单位逐条阅读《春秋》经传是最习惯的学习方式。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所讲述的学习经历和研究心得,皆循此法。《纂例》呈现的是非常成熟、高度专业化的学术成果,而将思考过程基本隐去,对于学术传统的照顾也不周到。以“楚人杀陈夏征舒”为例,它在《纂例》中出现在《杀他国大夫例》之下[27],作为此种辞例的一个证据,而其背后史实和相关义理,作者只提供了寥寥两句说明。《微旨》则提供了近600字的征引和辨析,显然更便于学习与思考,而《纂例》或许会被当作工具书备查。不过,由于《纂例》中的“学术成果”,实与《辨疑》一样,是从啖、赵其他著作中钞撮而来,故其具体观点或思路被柳宗元所学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纂例》卷一的八篇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卷是“全书总义”,户崎哲彦则认为是单篇文章的辑录,而这些文章很可能是啖、赵、陆相关著作的序言[28]。无论怎样,这八篇文章与现存的《微旨》《辨疑》《纂例》三书之间,构成“总”与“分”的关系:前者使用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概念,也分散出现在后者之中。柳宗元既可以向《微旨》等书学习这些概念的内涵及用法,也不妨从这些可能是著作序言的文章中得到更为集中的教导。此过程无法复原,但大约从贞元十五年(799)开始(以《辨侵伐论》为表征),柳宗元就已经学习并运用了其中一些概念,是没有疑问的。而他学习与应用《春秋》学的全貌,极为清晰地展现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后期古文中。此种运思严谨的人格特质,既是他形成独特论辩艺术的基础,也是笔者分析其论辩艺术的前提。

二 立场与技巧:从新《春秋》学到柳文论辩艺术
《纂例》卷一的八篇文章以及陆淳《微旨序》《辨疑凡例》,集中呈现了新《春秋》学惯于使用的重要概念。拆开来看,这些概念极为平凡、常用,可以出现在任何著作和文章中,但组合起来看,则有可能呈示出鲜明的特殊性。不局限于解释概念的基本内涵,而是注重梳理概念之间的关系、厘清概念的具体用法及其功能,这是“概念史”研究的特色与优势。这些概念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政治概念,通常被用来表达政治观念或表明思维立场,比如“尧舜”“夏”“周”“圣人”“孔子”“生灵”“生人”“皇极”“道”“教”“理”“礼”等;另一组是形式概念,通常被用来表明解经方法或思维技巧,如“文”“辞”“心”“情”“意”“中”“常”“权”“名”“实”等[29]。对于上述概念,柳宗元一方面积极吸收,另一方面则有增益、微调和侧重。一般的观念史研究,只是孤立地解释上述概念(主要是政治概念)的内涵,而很少关注政治概念的运用及相互关系[30],也忽略了形式概念所体现的思维技巧。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柳文的实践与反思中,找到其运用概念的特殊方式与深层意旨。本节着重考察“尧舜-生人”“文-名-实”两组概念。
吕温记录陆淳教诲云:“子非入吾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观吾之奥,睹宣尼之奥。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31]柳宗元总结得更为精辟:“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32]他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则举例为证:“于‘纪侯大去其国’,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33]检《微旨》此条,陆淳云:“国君死社稷,先王之制也,纪侯进不能死难,退不能事齐,失为邦之道矣,《春秋》不罪,其意何也?曰: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故尧禅舜,舜禅禹,非贤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故《语》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禹,吾无间然矣。’达斯语者,其知《春秋》之旨乎?”[34]在这段论述中,“先王之制”“为邦之道”“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实质都是啖助所反对的“周典”。而陆淳显然要以“尧舜之道”来凌驾“周典”,他赋予前者的政治内涵就是“重生人”。就政治象征而言,啖助主张“变周从夏”,赵匡主张“从周”[35],陆淳则接近啖助,但又升华为“尧舜”。陆淳作出这样的处理,极大提高了“生人”概念的重要性。他并非简单借此表达“民本”观念,而是表明思维立场:以“重生人”为“第一政治原则”。对此立场,柳宗元的学习与应用非常早。他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说:“往年曾记裴封叔宅,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36]此事必在贞元间。他对“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为何如此重视?检《微旨》,陆淳云:“晋文公未葬,晋襄公用师,不书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晋为盟主,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丧,而袭其同姓。若不能救,则先父之业坠矣。故圣人为之讳,许其以权变礼,异乎匹夫之孝也。”[37]这显然是同一立场的另一次应用:“和其民人”可以凌驾于“孝”之上,同样意味着“尧舜之道”可以凌驾“周典”。早在贞元十五年(799)的《辨侵伐论》中[38],柳宗元就对此论辩套路进行了第一次演练。他认为《左传》“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之说以及《周礼·大司马》“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之说,都没能揭示正确的政治原则,即“罕知侵伐之端焉”。他提出要满足“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三个条件,才是“为人之举”,才是“公”,于是“钟鼓作焉”;否则,“非为人之举也,故私之。私之,故钟鼓不作”。可见,他拨开了关于“侵”与“伐”的礼制迷雾,直接依据“为人”原则来权衡善恶,与陆淳的思路如出一辙。而他提出“三有余”之说,很可能也是受了啖助启发:“啖子曰:凡军旅,国之所以安危也,故纪其善否焉。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以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39]
在诸多论辩场合,柳宗元并不想时刻表达“民本”观念,而是借助“生人”立场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封建论》就是典型例子[40]。以往“封建论”的逻辑通常是:第一,封建制是圣人所定,所以肯定是好的;第二,郡县制会出问题,尤其短命的秦朝,是郡县制的“硬伤”,所以只应该封建。柳宗元《封建论》明显针对这两点进行了精确打击:他将圣人定封建的事实,拆分为“意”和“势”两层面;将郡县制出问题的事实,拆分为“制”与“政”两层面。为什么会这样拆分呢?因为他接受了“重生人”是“第一政治原则”,甚至可能直接从陆淳“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若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的说法中袭取了批驳封建制的基本思路。他发现郡县制比封建制更利于“理人”,因为前者可以随时调整管理者,后者则只能“继世而理”,于是“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言下之意,只有利于“理人”的郡县制才符合“圣人之意”。可是,上古时代的封建制也包含“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的政治内涵,应该如何评价呢?由此他制造出“意”与“势”的二分:前者是自上而下的主动之意,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被动之势。封建制的创立过程根本不包含圣人意志,而“殷周圣王”不废封建制,也是因为“不得已也”,当然也不包含圣人意志。那么,郡县制为什么也会出问题?答案是“咎在人怨”。于是他又制造出“制”与“政”的二分。郡县制本来是利于“生人”的,但应用起来却可能损害“生人”,原因是秦始皇掺杂了“私情”,“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可见,柳宗元在历史发展、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观察“生人”的作用与处境,不断分剖名相、撑开理论空间,尽可能周到地评估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得失[41]。
极为正当、高度合法的“生人”概念,成为柳文论辩的一大法宝。在《断刑论下》中[42],他指出顺天时行赏罚对于“生人”的荒谬效果,并刻意夸大:“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再如《非国语·救饥》[43],批判箕郑之言“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对于国君而言,“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则,但在“救饥”面前显得极为无力,故曰“未尽乎术”。又如《非国语·三川震》[44],对于“天地之物”的运行有近乎科学的想象,但其敢于骋辞的底气在于:“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意思是周幽王灭国不是“天之所弃”,而是因为理人理财之“术”的丧失。又如《非国语•不藉》[45],虢文公以“求福用人”为由劝谏宣王不要“不藉千亩”,柳宗元站在“生人”立场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也就是说,“藉千亩”对于“劝农”的促进作用,是“礼之饰也”,是间接的引导;而“时使”“节用”等措施的促进作用,则更为直接和明显。这个逻辑在《非国语·无射》中有更为极端的表达:“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乐之不能化人也,则圣人何作焉?曰: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所以明乎物无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46]礼乐对于“化人”“理”几乎无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故“不可忘”。柳宗元似乎特别反感“饰”,相应地,他又特别强调“功”和“利”。比如他常有“利于人,备于事”“兴功力,致大康于民”的说法。在《吏商》中,他甚至宣称“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47]。引起更大争议的是《伊尹五就桀赞并序》[48],认为伊尹怀有“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的大志,他在汤和桀之间反复去就,是因为“心乎生民”“急生人”“欲速其功”,期待夏桀一旦被他感化就能立刻救民,而商汤尚不具备这样快速的能力。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善于运用“生人”概念,对“生人”的处境、需求、心态进行多方面的体察与思考,往往能开辟新见,形成凌厉、新锐的论辩特色。陈弱水指出:“柳宗元思想的原创性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特异性的来源,显然是他坚定地坚持把人民的福祉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49]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剖析“特异性”。笔者以为,如果将“思想的……特异性”改为“古文的特异性”,或许更容易讲清楚。

如果说柳宗元反复运用“尧舜”“生人”等政治概念,确定了其古文的论辩立场,那么他频繁运用一些形式概念如“文”“名”“实”,则塑造了其古文的论辩技巧。柳文对这些概念的运用方式,同样是从新《春秋》学那里借鉴、转化而来。
我们再回到《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又举一例:“于‘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见圣人褒贬予夺,唯当之所在,所谓瑕瑜不掩也。”所谓“当”,也就是啖助所谓“原情为本”,赵匡所谓“著权制”“以定厥中”,陆淳所谓“表之圣心”;根据柳宗元《断刑论下》的说法,“当”又可等同于“大中”[50]。这些方法,是经学家所看到的圣人制经方法,其实也就是经学家自己的解经方法。传统《春秋》学者尤其是《公》《榖》学者的解经过程通常是:从经文入手,分析时间、人物、地点、称谓、动词、语序等信息,找出正常或反常之处,揭示圣人的褒贬态度,然后根据典籍、师说所提供的政治原则以及相关历史事实,解释褒贬的原因。但问题是,原则与事实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经文本身的复杂程度,所以《春秋》学者所看到的“文”与“实”的关系,是极为摇曳、迂曲的。他们需要从大同小异的“文”中,不断分析出一些差异巨大的“实”。比如《公羊》家既要解释“书”与“不书”,“言”与“不言”,“称”与“不称”,还得解释“不当书而书”,“不当言而言”,“当称而不称”,“不当称而称”[51]。有意思的是,啖、赵、陆一方面批评三传学者“诡辞迂说,附会本学”,倡导“《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52],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说《春秋》“辞简义隐”,既不同于“史氏之书”也不同于“里巷之言”,不能“苟尔而易知”[53]。就解经结论而言,他们往往显得简明、直接[54],但就过程而言,他们丝毫不比三传学者轻松,甚至因为要对旧说“择善而从”而付出更多的思力[55]。啖助批评旧说云:“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56]柳宗元评价啖、赵、陆云:“《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57],“《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58]。可见,新《春秋》学派不仅要直面《春秋经》的极简之“文”,试图发现背后的“实”,还要不断去除旧说之“文”对于“实”的种种遮蔽和歪曲,让“实”得到更为显著的示现。他们常以“中”“当”“权”“原情”“圣心”自居,处处表现出“去文求实”的强烈信心及思维技巧。比如柳宗元所举“楚人杀陈夏征舒”一义。《公羊传》认为圣人将“楚子”改称“楚人”是明贬暗褒,以贬为经,以褒为权,这叫“实与而文不与”[59]。《微旨》则认为圣人前言“楚人”而后言“楚子”,正好是前褒后贬,不需要分明暗、经权,这叫“指事原情,瑕瑜不掩”[60]。可见,陆淳既坚持了《春秋》学“权衡文实”的解经传统,又为此传统注入了“去文求实”的信心与技巧。

柳宗元对于新《春秋》学“去文求实”的思维技巧,有深刻的了悟。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他指出孔子记录荀息、仇牧、孔父三事使用了完全一样的文辞,以往学者包括赵匡都认为孔子的态度一律是褒美[61],但柳宗元认为是贬荀息。在《非国语•荀息》中[62],他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荀息“不得中正而复其言,乱也”,故不能以“信”许之。进一步,他又对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一例,提出了关于文实关系的新见解:许止误用药而导致许悼公死亡,圣人书“弑”,是故意进行文过其实的恶评,来警戒世间一切儿子要谨慎事父;荀息虽然为国君而“死节”,但之前的所作所为是“奉君之邪心”“不务正义”,属于“伪忠臣”,而圣人却用同一套文辞记录仇牧、孔父、荀息三事,仿佛将“真忠臣”与“伪忠臣”混为一谈,其实是想激励世间一切臣子要勇于死节。圣人对这两件事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是明贬暗悯,一是明褒暗贬,但却通过非常简单的文辞表达出来。柳宗元经过反复权衡,才最终祛除了容易引起误解的“文”,笃定地揭示了正确的“实”。他自信地说:“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征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谓信道哉。”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柳宗元还自觉将此种“去文求实”的技巧转化为一种针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更具普适性的论辩艺术,即“去名求实”。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63],他称赞元洪“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而他自己讨论“均赋之事”,是期待“求往复而除其惑焉”“来至当之言”。他再一次将“大中”和“当”的概念与《春秋》学紧密系联在一起。那么他究竟如何展开论辩呢?蒋之翘的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元饶州意在仍旧籍,而不必扰民,而子厚意在必核贫富之实定之。”柳宗元认为,抛弃贫富之名、勘定贫富之实是“定制”的前提,而此种思路正是得益于新《春秋》学;新《春秋》学特别强调揭示“文”背后的“实”,而柳宗元建议对方要注意考察“名”背后的“实”;对方既然也是通晓新《春秋》学的同道中人,应该深悉此理吧![64]
将社会现实转化成文本模型来作分析,这成为柳文论辩的又一大法宝。在《䄍说》中[65],柳宗元一方面站在“生人”立场来判定“䄍之说”的不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则为此判定过程填入了一套精致的论辩技巧:他认为圣人设立䄍祭就如同设立文辞,是通过“黜神”来警戒“吏”,“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这与《监祭使壁记》所谓“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66]是同样意思;进一步,他将“黜神”之“礼数”视作“名”,将圣人之“意”与“教”视作“实”,反对“其名则存,其教之实则隐”,主张“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也就是“去名求实”。同样道理,他分析“守道不如守官”之说,认为“官”是一种命名方式,是“道”的表达,不能将“道”和“官”当成平行事物去比较,更不能本末倒置[67];他分析佛教学说,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遂主张“去名求实”,认为韩愈的排佛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68];他读韩愈《毛颖传》,认为不能只观其“怪于文”和“俳”,而应该看到它能够“尽六艺之奇味”,甚至使“学者得以励”从而“有益于世”[69];他讨论“大钱”,主张不能被“轻重”之名所拘束,应根据“其时之升降轻重”来判断是否可以铸大钱[70];他在多篇古文中谈到识人之术,比如主张“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胜质、行无观、智无考者,下之”,反对“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71];他认为无论学书法还是学服气之术,都应该去“形”而求“理”,去“文”而求其“不可传者”[72];他还非常认真地与人辩论,寻找石钟乳不要迷信产地,要“取其色之美”,“求其至精”[73]。以上种种论辩技巧,都可归类为“去名求实”。贬谪期间,柳宗元还常将“去名求实”的技巧应用于分析自身的人生处境。比如他对着“愚溪”发牢骚,是通过分析名实关系来制造戏谑效果,最终认定这条可怜的溪水具有“愚”之实而必须接受“愚”之名[74]。同样道理,元和八年(813)后他写了一系列书信《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反复申说“取其实而去其名”[75]、“去其名,全其实”[76]的道理,并说自己贞元以来一直坚持“避师名”[77]。总之,柳文不仅将“去名求实”的技巧施用于文本,而且施用于一切社会现实问题乃至人生问题,制造出一以贯之的雄辩之气。
综上所述,柳宗元古文的论辩艺术主要表现为:以“生人”为论辩立场,以“去名求实”为论辩技巧。这两个方面的特征,皆由新《春秋》学的思维方式转化而来。而柳文“去名求实”的论辩技巧,恰可与韩愈古文的“正名”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以“五原”为代表的韩文论辩艺术,主要致力于对重要概念“作出明确的本质界定”以及“别同异”“明高下”,从而“开启儒家伦理本体化的趋向”以及“树立了儒家伦理的权威地位”[78];相比之下,柳文极少围绕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其所谓“名实”主要指向形式与内容、表象与事实、现象与原则等事物深层结构,从而比韩文更显务实和精严,思想上也表现为融通儒释。
三 原道与征圣:韩、柳文论辩艺术的思想分歧
经学思维影响了柳文的表达方式,新《春秋》学塑造了柳文的论辩艺术,已如上所述。而柳宗元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论辩,除了现实经历的刺激之外,还有更为内在和一贯的根由。众所周知,韩、柳二人都推崇“圣人之道”,他们各自梳理过一套“道统”序列,并且都将对于“道”的某种赞助或发扬,视作古文的理想功能。笔者认为,恰是在“圣人之道”四个字上,韩、柳的思想及艺术发生了重大分歧:韩愈更重视“道”,而柳宗元更重视“圣人”;韩愈主要致力于“原道”,而柳宗元主要致力于“征圣”;通过论辩,韩愈最终证明自己秉持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而柳宗元最终证明自己的判断力与圣人保持一致。

诚然,“圣人”是一个过于常见的概念,任何儒家乃至诸子经典似乎都在诉说这个概念的内涵与用途。但柳宗元思考它、运用它的特定方式,依然与新《春秋》学密切相关。一方面,啖、赵、陆解经以“中”“当”“权”“原情”“圣心”自居,都是打着“圣人”的旗号来论辩,甚至直接“尊之曰孔子意也”;另一方面,他们权衡旧说,也是以“圣人”为标准进行“取舍”,动辄曰“不近圣人夷旷之体”[79]。啖助由此建立了颇具现代学术眼光的“文献层累”观:“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三传所记,本皆不谬。后人不晓,而以滥说附益其中,非纯是本说,故当择而用之,亦披沙拣金,错薪刈楚之义也。”[80]他的意思是,三传旧说原本都符合圣人之意,但掺入了伪说,故须“取舍”。他为此设定了复杂的义例,如“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义”,“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传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择其当者留之,非者去之,疑者则言而论之”[81]。从啖助的《春秋集传》,到陆淳的几本集大成的著作,都是循此认识而写成。他们没有将“圣人”视作特定价值观的载体,而是视作最佳判断力的象征,并且自觉学习和应用此种判断力。柳宗元说陆淳著作“明章大中,发露公器”,“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专圣人之教”[82],显然是深刻体会到了“圣人”的特定内涵与价值。其《时令论下》云:“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83]又《六逆论》云:“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84]这些写于贞元年间的古文,都明确表达了应该侧重于从判断力角度去理解和学习“圣人”。
从贞元年间一直到永州末期,柳宗元反复使用着一套论辩措辞:他撰写古文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某些违背圣人之意的言论或行为,或是为了发现某些不为人知的圣人之意。比如短短三百多字的《四维论》中,相似的措辞出现了三遍:“《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85]《守道论》的套路几乎完全一样:“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是固非圣人之言,乃传之者误也。……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果矣。”[86]《桐叶封弟辩》还巧妙利用这套措辞增添了论辩的波澜:“古之传者有言:……吾意不然。……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87]他认为周公这样的圣人不会纵容与摆弄君主,故其所言非真,甚至其所为也可能是他人所为。在《非国语》中,柳宗元不断讥讽《国语》作者的“诬”“妄”“愚”“赘”“迂诞”“迁就附益”,认为他遮蔽了圣人之意,歪曲了圣人之言,如《非国语序》谓“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88],《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谓“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89],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谓“此在明圣人之道”[90],则又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力与决心。与上述文章相反,《辨侵伐论》认为《左传》和《周礼》的言论虽无本质错误,但没有揭示“侵伐之端”,而柳宗元却发现了“圣人之所志”[91]。同样道理,《论语辩二篇·下篇》宣称发现了“圣人之大志”[92],《伊尹五就桀赞并序》声称“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93],都非常自信。更有趣的是《乘桴说》[94]。此文从《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段中读出了寓言的意味:“海与桴与材,皆喻也。海者,圣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为桴者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时,将复于至道而游息焉。……其终曰无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于闻义,果于避世,而未得所以为复者也。”有人向他提出疑问:“子必圣人之云尔乎?”柳宗元回答:“吾何敢?吾以广异闻,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为学,其于无闷也,揵焉而已矣。”他很清楚此种解读非常主观,但仍坚信“吾言”值得“遁世者”学习,因为它符合圣人之意。柳宗元的以上两种征圣意识,一是据圣纠谬,一是依圣立新,都可以在新《春秋》学著作中找到最直接的根由。
综上所述,柳宗元不仅将新《春秋》学思维方式转化为古文论辩艺术,而且将新《春秋》学的征圣意识,直接树立为自己的主要论辩目标。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此种自我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柳文长于论辩的特征以及峻切决断的论辩风格,区别于韩文酣畅热切的论辩风格。从思想史角度来看,柳文所极力辩护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士大夫成长的路径:价值观的觉悟是次要的,判断力的培养才是第一要义,而判断力的培养只能依赖不断重复的具体实践。《天爵论》云:“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95]所谓“明与志”,就是判断力的培养,而所谓“道德忠信”,则是价值观的觉悟。这篇可能写于早期的古文显示,柳宗元与韩愈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走在完全不同的路径上:前者的方向是功利主义,后者的方向是伦理主义。包弼德指出:“对于柳宗元来讲,问题是如何履践(engagement);‘中’没有特别的内容,但是它可以在应物和作用于世界的时候用诸事(‘及物’)”,“在柳宗元手里,典籍传统变成思想和表达中所包含的品质。圣人之道没有被解释成一个教条的说法;而是说,它指拥有某种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养成好的个性。这是一个人可以期待于一个官员和执法者的品质”[96]。这些都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但只有从新《春秋》学的影响入手,才能将上述观察放在一个系统的解释体系中,才能为柳宗元思想与艺术的特质与价值寻找到一个至少起到主要作用的内在根由。藉此个案研究,笔者希望呼唤一种作家研究的新思路:将文学的本质视作一种深刻而系统的思维方式,不仅重视作家的表达内容,而且重视他的表达方式,从而揭示文学世界与思想学术世界之间的深层关联;此种关联本身,也就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某些民族化、历史性的本质。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宋转型视野下的散文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4CZW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4ZDB066)阶段性成果。
[①]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②] 参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张稳蘋编辑《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40页。
[③] 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④] 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⑤]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9页。
[⑥] 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册,第2042页。本文对柳宗元诗文的系年,主要依据此书,间亦参考孙昌武《柳宗元评传》。
[⑦]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五《送易师杨君序》,第5册,第1645页。
[⑧] 寇养厚《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170页。
[⑨]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⑩]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春秋”之部第59页。
[11]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二三《赠韦司业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册,第3278页。
[12] 《全唐文》卷四九五《两汉辩亡论》,第5册,第5047页。
[1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二《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第3册,第755-756页。
[14] 《柳宗元集校注》外集补遗《万年县丞柳君墓志》,第10册,第3377页。
[15]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6页。
[16] 查屏球《唐学与唐诗》,第34-37页。
[17]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祀朝日说》,第4册,第1111页。
[18]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第6册,第2057页。
[19] 柳文记《微旨》皆作《微指》,二字可通。又柳文提到《宗指》一书,户崎哲彦怀疑就是《纂例》卷一八篇文章之首《春秋宗指议》(参见[日]户崎哲彦著,王青译《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73-474页)。
[20] [日]户崎哲彦著,王青译《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88-490页。
[21] 具体考辨,参见葛焕礼《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著作考辨》,《西部学刊》2015年第4期。
[22] 《全唐文》卷六二六《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第7册,第6322页。
[23] 葛焕礼《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著作考辨》。
[24] 陆淳《春秋集传微旨》卷中,《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8册,第211页。
[25] 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卷八,《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44页。
[26] [日]户崎哲彦著,王青译《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71页。
[27]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七,《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93-294页。
[28] [日]户崎哲彦著,王青译《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73页。
[29] 有些概念是一词多义的,比如“理”既可表“治理”也可表“义理”,“心”既可泛指“心智”也可专指“圣心”。但大致的概念体系,由以上两类构成。
[30] 户崎哲彦注意到柳文中概念的相互关系以及特殊用法,比如“大中”屡屡与“圣人之道”并记,“及物”与“化人”连用,“大公”与“大中”密不可分,以及“在柳宗元来说,圣与儒是被严格分别开来的,……孔子则拥有圣与儒的两种属性”([日]户崎哲彦著,金培懿译《柳宗元的明道文学》,《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27-447页)。这些都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可惜由于他的论述方向是“明道文学观”,仍受制于一般意义的观念史视角,不能再行深入。
[31] 《全唐文》卷六三一《祭陆给事文》,第7册,第6370页。
[32] 《柳宗元集校注》卷九《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第2册,第576页。“生人”,一作“圣人”。据吕温《祭陆给事文》所记陆淳语,应作“生人”为宜;且世彩堂本、《英华》本皆作“生人”。
[3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第6册,第2057页。
[34] 《春秋集传微旨》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01页。
[35] 刘宁《论中唐春秋学的义例思想》,《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
[36]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第6册,第2057页。
[37] 《春秋集传微旨》卷中,《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08页。
[38]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辨侵伐论》,第1册,第268页。
[39] 《春秋集传纂例》卷六《军旅例第十九》,《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88页。
[40]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封建论》,第1册,第185页。
[41] 孙昌武分析《封建论》认为:“(柳宗元)显然借鉴了佛典论书中名相辨析的方法。避免概念的游移,求一言一语的准确,也是造成柳文精悍之气的重要因素。”(孙昌武《柳宗元评传》,第318页)此种论点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笔者不取。副岛一郎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则从封建、郡县的体制本身的得失出发来阐述封建制的是与非,站在民本思想的立场上主张封建之非。”([日]副岛一郎著,王宜瑗译《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笔者很赞同。但他又认为杜佑《通典·职官十三·王侯总序》与柳宗元《封建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上,第72-73页),笔者认为此种联系也不能证实,不如从啖、赵、陆著作中找根源更为合理。
[42]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断刑论下》,第1册,第262页。
[43]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五《非国语·救饥》,第9册,第3223页。
[44]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三川震》,第9册,第3139页。
[45]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不藉》,第9册,第3135页。
[46]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无射》,第9册,第3165页。
[47]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〇《吏商》,第4册,第1421页。
[48]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九《伊尹五就桀赞并序》,第4册,第1314页。苏轼《柳子厚论伊尹》驳云:“元祐八年,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036页)
[49] 陈弱水著,郭英剑、徐承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50]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断刑论下》,第1册,第263页。
[51] 许雪涛《公羊学解经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9页。
[52]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7页。
[53]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7-258页。
[54] 葛焕礼认为,新《春秋》学派对于《春秋》书法的解释,除了传统的修辞原则和伦理原则之外,又增加了记实原则。具体而言,他们常从“人情”“事理”等角度解经,故常显简明(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4页)。
[55]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386-387页。
[56]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7页。
[57] 《柳宗元集校注》卷九《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第2册,第575页。
[58]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第6册,第2057页。
[59]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宣公十一年”条,《十三经注疏》,台湾艺文印书馆2013年版,第7册,第202页。
[60] 《春秋集传微旨》卷中,《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11页。
[61] 《春秋集传纂例》卷七《杀例第二十六》,《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93页。
[62]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荀息》,第9册,第3198页。
[6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第6册,第2089页。后引蒋之翘评语见文后“集评”。
[64] 关于《春秋》学与“核名实”的关系,刘禹锡对吕温的评价可为旁证:“师吴郡陆质通《春秋》,从安定梁肃学文章。……遂拨去文学,与俊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六《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059页)
[65]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䄍说》,第4册,第1128页。
[66]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六《监祭使壁记》,第5册,第1709页。
[67]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守道论》,第1册,第240页。
[68]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五《送僧浩初序》,第5册,第1680页。
[69]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第4册,第1435页。
[70]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大钱》,第9册,第3162页。
[71]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第5册,第1568页。
[72]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二《与李睦州论服气书》,第6册,第2114页。
[7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二《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第6册,第2095页。
[74]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四《愚溪对》,第3册,第898页。
[75]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第7册,第2178页。
[76]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第7册,第2197页。
[77]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第7册,第2200页。
[78] 刘宁《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79]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7页。
[80]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啖赵取舍三传义例第六》,《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6页、第258页。
[81]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第六》,《丛书集成新编》第108册,第258页。
[82] 《柳宗元集校注》卷九《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第2册,第575-576页。
[8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时令论下》,第1册,第258-259页。
[84]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六逆论》,第1册,第273页。
[85]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维论》,第1册,第229-230页。
[86]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守道论》,第1册,第240-241页。
[87]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桐叶封弟辩》,第1册,第304页。
[88]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四《非国语序》,第9册,第3131页。
[89]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第6册,第2066页。
[90]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一《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第6册,第2071页。
[91]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辨侵伐论》,第1册,第269页。
[92]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论语辩二篇·下篇》,第1册,第331页。
[93]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九《伊尹五就桀赞并序》,第4册,第1315页。
[94]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乘桴说》,第4册,第1133页。
[95]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天爵论》,第1册,第236页。
[96] [美]包弼德(Peter K. Bol)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51页。
作者简介
谢琰
谢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出版专著《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讲《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唐诗选读》《〈文选〉精读》等课程。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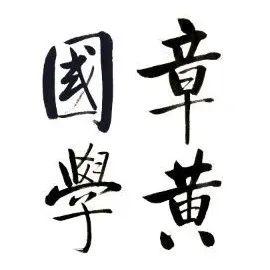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林丹丹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