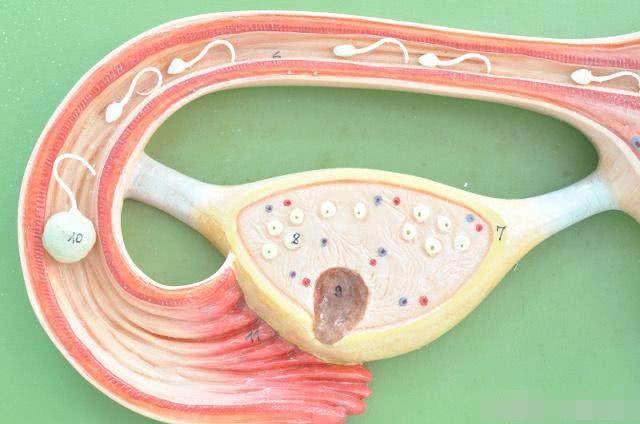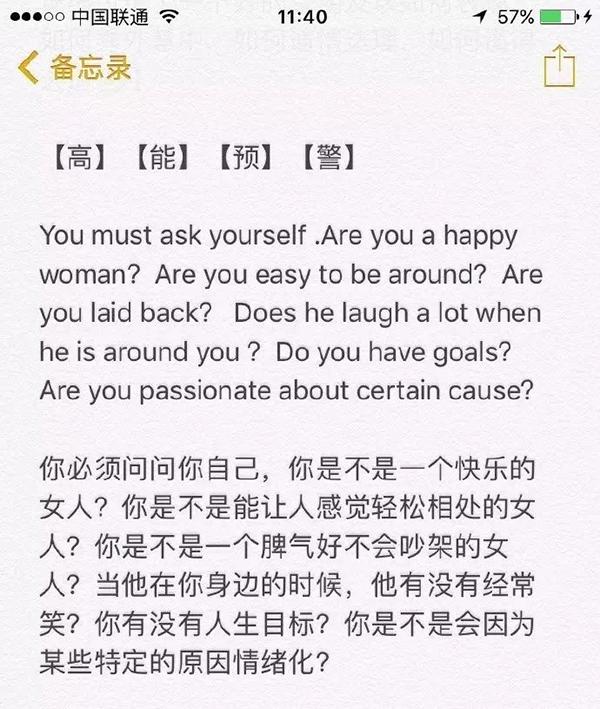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散文范围广泛,可以说除去诗歌、小说、戏剧等之外的一切文体都是,而它又可以分为散体文和骈体文。
骈体文简称骈文,也叫四六文,它的形式上有很多要求:两句相对,四字句对四字句、六字句对六字句等;上下句的词语要对称,虚词对虚词、实词对实词。在音节上,出句与对句要平仄相对;并且要求多运用典故和华丽的辞藻等等。
散体文又称“古文”,它的行文自由,句式长短错落,用语自然,是先秦两汉时期流行的文体。到了唐代,人们把这种文体视为学习的对象,先秦两汉对于唐代来说是“古代”,所以就称之为“古文”。(“古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很明显,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笼统的指的是19世纪中叶以前,我们所说的古文也就是这个概念下所有的古代的文章,本文论及的“古文”不取此意。)
在唐代,骈文的使用频率特别高,章、奏、表、启、书、记、论、说等文章样式都可以用骈文写成,甚至可以说是“官方”文体。但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主要就是反对这种文体。那么,骈文到底好不好呢?为什么要反对骈文呢?

一起了解一下散文在中唐以前的发展状况。
明代文坛上的“前七子”曾经提出一个审美规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可见,秦汉时期的文章在明代人眼中可以视为写作“标杆”。在先秦时期古代散文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当时有以议论为主、陈说主张的诸子散文和以历史题材注入主观评价的历史散文;到了汉代,虽然赋被认为是有汉“一代之文学”,但也出现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传散文巅峰之作《史记》,班固的《汉书》同样在散文史上闪烁着光辉。(当然,这种最初的文史不分离的现象,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最初的甲骨文、铭文上的只言片语记述观点、事件,至秦汉逐步发展为议论与抒情交织而后发展成多种文体样式,所承载的文学、实用功能逐步扩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散文的界定也越来越模糊。
六朝时期,出现了“文”“笔”观念的对立。简单地说,当时的区分是这样的——“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刘勰《文心雕龙》)。也就是说,“文”就是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笔”就是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这样的一个区分,导致骈文和散文成为相对的文体。
骈文写作者在辞藻、声律、隶事(就是用典故)、对仗等方面不断追求艺术美,构筑完美流转具有音乐色彩的精美骈文,产生了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徐庾体”风靡六朝,而这股风气很自然地延续到隋唐。
但是在形式上过分追求完美,很容易导致意思与情绪的表达不够到位,也就不够实用。当然,骈文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比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来两句感受一下:“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勃的这篇骈文恐怕不论是写古文的还是写骈文的都会在心中默默献上膝盖。但是从魏晋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带来的是模仿之风趋盛,导致文风式弱,更多的人写骈文是比较浮夸的。
当然,抛开骈文本身的局限,从当时的大环境看:随着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破坏,中唐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手段、兵制等各方面已经和初盛唐时期不同,此时心忧天下的官僚士大夫的惶恐地应对变化,这个时期思想上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实用。
而盼望中兴的唐王朝统治者,大举着儒学复兴的旗帜企图为社会问题找到药方,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就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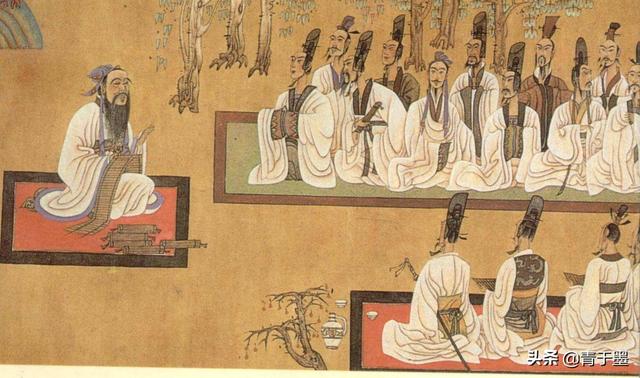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韩、柳诸人名义上打出的是“复古”旗号,实际行动上却是搞创新。
首先,在理论上,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这场“古文运动”可不是纯粹的文坛运动,它的落脚点在于发现社会弊病,试图为李唐王朝建立牢固的统治思想,以待王朝的中兴。
韩愈在《争臣论》中提出“文以明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在这里,“修辞”就是写文章,“修辞明道”即“文以明道”。为了避免写作者把古文简单当成一种形式的模仿和言辞的因袭,韩愈提出为文者要注重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他追溯的是孔孟的心性论,重新激活了养“浩然之气”传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意思是说精神修养方面的浩然之气是其《孟子》之文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而韩愈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鼓励中唐文人更多注重对道德的修养,实现“文以明道”,从而重振中唐儒学的统御,最终完成中兴李唐的历史使命。
韩愈的《师说》直指当时社会上“不耻相师”的不良风气,期待青年一代科学从师学习;柳宗元《捕蛇者说》在末尾说得很清楚,他写作的目的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其次,在语言上,改变古语深奥的一面,力求让文章语言通俗化、生活化。
除了文学家这个标签,韩愈还有另一个身份是思想家。作为一名思想家,他本人深知对待古人的“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进学解》中有一段太学生对国子先生的评价,可以看作是韩愈的观点:“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在韩愈看来,周代的诰书和殷代的《盘庚》,是艰涩拗口又难读的(像这种佶屈聱牙的文字,韩愈是反对的);《春秋》的语言是精练准确,《左传》的文辞是铺张夸饰;《易经》行文多变而有法则,《诗经》思想端正而辞采优美;再往下到《庄子》《离骚》,司马迁、扬雄(子云)、司马相如的创作,同样巧妙但曲调各异。正是博采众长、批判的继承吸收,韩愈的文章内容宏大而外表气势奔放。
骈文的语言多半是比较书面化的,韩愈改骈为散,目的就是为了使语言接近生活化的口语。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这里的“陈言”含义比较广,骈体文的浮词丽句、古旧的经典话语等等都是。所以“去陈言”就有反对因袭、模拟的意思,也就是说别人已用过的词、说过的话,在写作中一概不使用,即“辞必己出”。(可见,在韩愈心中,原创的标准是相当高的。)
与“去陈言”配套的,他又提出“文从字顺”。也就是说,文字的表达还要流利顺畅,合乎语法。实际操作中,标准是死的,写作是活的。在韩愈笔下,一切陈规都被忽视,他是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自己的个性选择最适合的语言和艺术形式。古代汉语也绝不是一味抵制,他拿来创造性地改变使用,并且善于吸收当时的口语;骈文他也不是一味反对,他在追求文从字顺的时候,也间杂着骈俪句法。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杂说》之四《马说》就有很明显的骈体迹象。
他的杂说四篇(《龙说》《医说》《崔山君传》《马说》)虽然讲的是大道理,语言却是很通俗的、很接地气的,同时又是意味深长的。还记得电影《银河补习班》中一个场景中传来学生背诵“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声音,(《马说》)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讽刺性是非常强的。
韩愈对于语言的运用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今天仍然在用的一些成语,有不少就是出自韩愈的文章。如《进学解》中就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俱收并蓄”等成语。
其三,写作方式上,骈散结合、自由舒展,进而充分展现创作者个性。
韩愈倡导“文以明道”,但也不是说作文就是一味重视“道”的承担,事实上,他重视“道”也同样重视“文”,正是有这种文道并重的态度,因此古文写作者在积极吸取骈文形式、音韵的基础上对传统散体文加以创新,充实文章内容与追求形式两手抓,创造了散体单行(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自由体散文新形式。
除此之外,韩愈同样注重创作主体情感的抒发,提出“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明道,也是不平、反映现实,“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可见,韩愈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是“恒发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被漂泊过程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作者受外界的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才会寄托了作者更多的思绪,才能表现出作者更真实的情感。
骈文在六朝其实是一种贵族文学,文士互相逞才争宠,加之宫廷生活雍容闲适,因此骈文创作内容不离宫廷事物,题材狭窄贫乏。中唐古文家正是深刻认识到其内容贫瘠而追求形式的创作缺陷,力求创作出内容质实的散文,韩愈究主张将创作主体的个性禀赋和情感力量贯注于行文中,使文章具有感发人心的强大力量。
如,韩愈《进学解》假托国子先生与学生之间对话,看似是先生勉励学生勤学,实则是抒发自己遭到的困境;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本是悼念亡侄的,但是也包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感伤和对社会的控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既是对被人遗忘、忽视的自然美的挖掘,也是蕴含着作者自身遭际的苦闷。
这种感发人心的力量,与韩愈所说的“气”有关——“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这个方面,骈文的声韵方面的技巧却也可以助长文章的“气势”。

总之,古文运动使得散文逐渐向文学本体回归:散文摆脱了声律的束缚,打破了许多框架,是一种更为贴近生活、更能适应时代进步和语言发展的新文体;散文从骈文这一贵族的殿堂里走了出来,走向市林、走入社会。
韩愈、柳宗元等古文运动倡导者用自己的理论与创作为古文重新定了位,拓展了古文的发展之路,昭示了古文具有多种风格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的不说,同样在中唐,传奇小说也逐步成熟,传奇作者多半是用散体写作的,试想,如果用骈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产生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古文运动,打着“复古”的旗号,做的却是创新。打着“复古”的名义进行“创新”,是不是耍流氓呢?对此,我想要说的是,即便是其他领域的“复古”,同样不是纯粹的复古,比如时尚界的种种“复古”。因为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人不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过去的场景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制。因此,所谓“复古”,当然更多的是“古为今用”。一味机械地照搬,更多的可能导致“邯郸学步”。
虽然到晚唐,骈文“死而复生”,以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为代表的“三十六体”(三人在家族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而擅长写骈体,世称“三十六体”。)再次确立的骈文的统治地位。但是,并不能说韩、柳的这场“古文运动”就是毫无意义的。
到了宋代,古文再度兴起,由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古文大家的继续努力下,骈文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宋人的基础和理论渊源,就是唐代古文运动。韩、柳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是一直有生命力的,他们二人后来被明代人评选入“唐宋(古文)八大家”,甚至于在今天读其作品依旧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