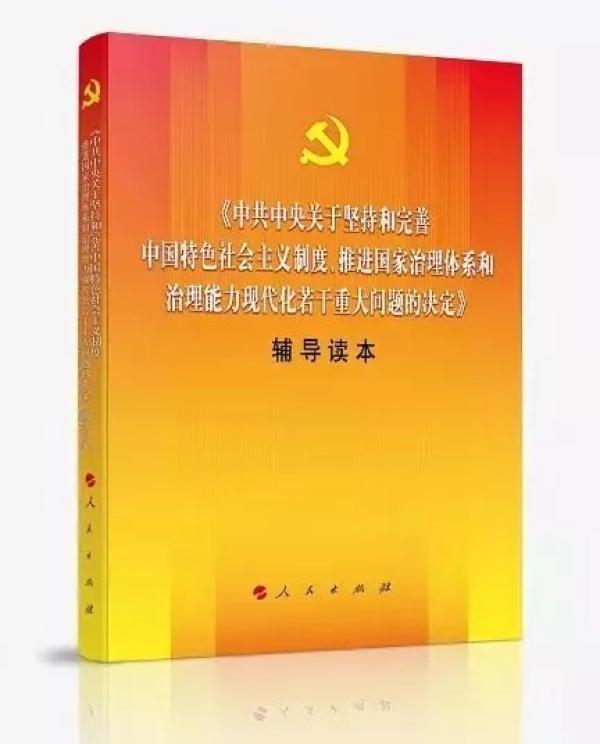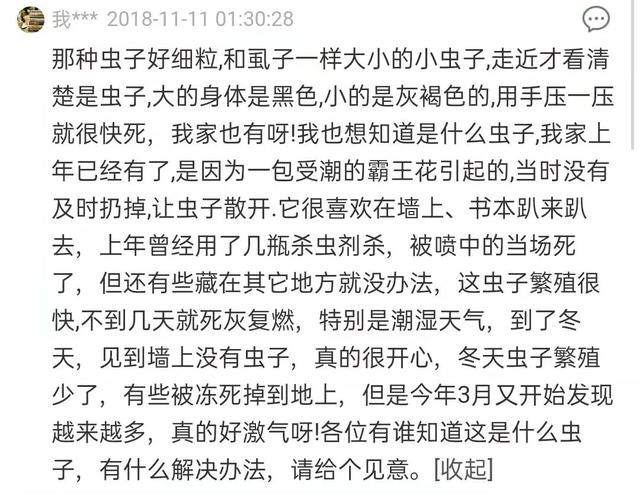滕吉文,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6年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探矿系,1962年获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动力学研究。
滕吉文曾主持青藏高原、攀西构造带、华北及陆缘、华南地区、西北造山带与沉积盆地等多项国家和院(部)级重点研究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1975年,滕吉文带队首次系统地开展青藏高原地球物理探测,首次获得了第一手科研数据,改正了当时国际上对青藏高原唯“地壳叠加说”和“地壳重力均衡学说”等理念,相继开启了一系列相关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

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滕吉文一直强调在国家战略需求和自主创新导向下的学科交叉和深化认识地球本体研究。
6点10分起床、8点办公、晚11点睡觉,闲暇时喜欢听古典音乐、看芭蕾舞剧,与人讲电话时夹杂着“OK”“Thanks”等英文单词……86岁的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滕吉文过着自律又时髦的晚年生活,有着超脱同龄人的硬朗身体与清晰思维。
作为首批对青藏高原进行地球物理系统观测和研究的科学家,滕吉文曾率队在高原湖中进行9次水下爆炸试验,最终得到了第一手精细数据,推翻了此前西方学者建立的“地壳叠加学说”和“地壳重力均衡学说”等理论,创建了陆—陆板块碰撞的新模型。
为“对得起院士这份名誉”,滕吉文仍在坚持每天研读国内外最新学术资料,每年坚持发表两篇论文,并将自主创新,特别是理念创新视为科技强国的根本。“越过地平线触摸地球动态脉搏”,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奥义。
9次爆炸次次成功
我国第二次青藏科考于2017年启动,滕吉文是科技部对该项目进行最后审查的专家之一。他直言,第二次青藏科考的主要工作不是地球物理学,而是气象、土壤、冰川等生态项目的考察,“地球物理太花钱了,且车到不了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设备上不去。”
时间回到1975年,41岁的滕吉文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地球物理分队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带队进藏,首次对青藏高原地球物理进行系统观测和深部过程研究。他形容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最高的高原,也是构造最复杂的高原。对地球物理学来讲,当时是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进藏前,滕吉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脑子里不断盘旋着各种问题:为什么青藏高原那么高?地壳那么厚?地下那么热?有那么多地震……而整个科考的投入非常大,涉及重力场、古地磁、电磁波感应场、地热环境、天然地震等的观测和标本采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通过人工爆炸来研究地球内部结构和动力学状态。
在成都军区协助下,滕吉文将60吨TNT炸药运入青藏高原进行湖中水下爆炸试验,第一次爆炸试验选择在羊卓雍措进行。
“当时下炸药的时候受到湖底巨石阻隔,下不去,这是非常麻烦和危险的,因为不是几斤或几十斤炸药,是3吨TNT炸药,水柱起来后威力堪比核爆炸。为排除故障,一些技术人员率先跳进水中,工兵也跟着跳了下去。”据滕吉文回忆,3吨炸药不轻,移开障碍物需要时间,而湖里都是从雪山上流下的冰水,“他们下水几分钟就感到喘不过气来,上岸后再下水,折腾好多次,但没有一个人喊苦,排除了险情都十分高兴。”后来,第一次水下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得知后亲自批示:“科考队同志们很辛苦,很努力,要给予表扬。”
此次青藏科考,滕吉文带队在水深20m-50m的羊卓雍措、普莫雍错、纳木错共进行了9次爆炸试验(3t,5t,9t,10t,15t),且次次取得了成功。通过这些爆炸,滕吉文和团队进行了亚东-当雄近500公里的长剖面观测,成功获得了地下深达100公里之内的壳、幔结构信息,这也是我国科技人员在青藏高原腹地采集的第一批宝贵的地球物理数据。

滕吉文曾率队在青藏高原湖中进行9次水下爆炸试验,次次成功。
满口假牙的年轻教授
在首获第一手地球物理数据的背后,是青藏高原严峻的自然环境和科考队员的数次遇险。
“一开始让我负责该项目的时候确实有点担心,将这一由18个部门、228人组成的队伍带进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试验是不得了的。首先要克服自然条件,缺氧三分之一,食、住、行与实施都很艰难。”据滕吉文回忆,那时进藏科考每天早餐是一块压缩饼干,冲一杯奶粉,“刚开始大家觉得挺好吃,但长时间吃就不行了”。住宿方面则是“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不管是对贴满牛粪的帐篷,还是黑得发亮的被子,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除生活条件艰苦外,整个科考过程也是险象环生。重力测量组一次行驶在盘山道时,由于路况差不慎发生车辆侧翻,滚了几道盘山路后幸好被一块大石头拦住。“车上同事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仪器状况。那时这台重力仪器是从美国引进的,经过了好多渠道,所幸仪器没坏,车也没坏。”
还有一次去羊卓雍措检查工作,滕吉文和藏族司机住进了一所兵站。睡觉前,藏族司机帮滕吉文整理好被子,并再三对他叮嘱:“第一,不能脱衣服;第二,不能躺下睡觉;第三,一切听我的。”直到第二天早上,藏族司机才向滕吉文道出原委,“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曾有不少汉族人因为睡觉一觉过去了,所以我让你靠着睡了一宿,不至于出问题。”
然而,状况还是发生了。进藏后不久,由于高原缺氧,滕吉文的牙齿开始松动。“到拉萨陆军医院看病,医生让我马上回北京。我说我不能回去,必须在这里,因为我是总指挥呀!后来医生建议我先到海拔相对低的亚东待一段时间。到亚东后,我一共掉了7颗牙,之后回到拉萨工作。第二年牙齿又开始松动,我就干脆把牙都拔掉,为的是持续入藏工作。”
由于抽调了原成都地质学院一个班的40多个学生进藏考察,滕吉文答应科考完成后给该学院讲一学期的课,可没牙怎么办?“我嗓门大,讲课问题不大,但吃饭是个问题。幸好我大学分到他们学校一个老师,曾任团支部书记的袁庆华,看我不能吃饭,就天天、顿顿给我做馄饨吞着吃。回京后,我才把牙镶上,从40多岁开始就满口假牙了。”
第一个知道数据的人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回京后,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1979年12月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签署的嘉奖令。让滕吉文高兴的是,这次青藏科考取得的首批数据和成果,引起了国际地球物理学界的极大关注。
此次科考前,美国学者Holmes早期曾提出过一个猜想,认为青藏高原地壳之所以有七八十千米的厚度,可能是由两个地壳叠加而成。1855年,美国两位物理学家艾瑞和普拉特提出了“地壳重力均衡学说”,认为喜马拉雅山脉隆起时重力已达均衡。
“喜马拉雅山的隆升确实很高,达到8844.43±0.21m。在这样一个高山地区,从加德满都开始测量,它的重力均衡异常是 120毫伽;翻过喜马拉雅山,一直到雅鲁藏布江,均衡重力异常才趋近于零,即近达均衡,而在整个喜马拉雅山麓地带是不均衡的。我们证明了美国两位物理学家的判断是不对的。”滕吉文说。
滕吉文团队还通过爆炸研究,证实了青藏高原不是由两个地壳叠加而成,而是一个有序的成层地壳,是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陆—陆碰撞的结果,这与海—陆碰撞完全不同,且形成了一个宽达300多公里的“碰撞挤压过渡带”。通过古地磁工作,还证实了印度次大陆块体与欧亚大陆板块之间首先在西构造结处相碰后,块体呈逆时针旋转,后又在东构造结处碰撞,从而得到了青藏高原各板块如何衔接的证据。
1980年5月,“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180位中国科学家和来自法、美、俄、加、日、瑞等18个国家的77位外国科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滕吉文和我国另外一位地球物理学家作了大会报告。
“在我国召开地球物理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滕吉文记得,大会开幕当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地球物理科学家Peter Molna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滕教授,咱俩先别客套,你告诉我,青藏高原上地幔顶部的速度是多少?”滕吉文回答“8.1±0.05km/s”。Peter Molna听后当场跳了起来,“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数据的人!”
以此次讨论会为契机,我国与西方国家首次开启了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合作。1980年-1982年,中法开展合作项目“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又一次获得了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以南、以北两条EW向共长约1200km人工源深地震宽角反射/折射剖面的探测等第一手观测数据。
理念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滕吉文一直强调在国家战略需求和自主创新导向下的学科交叉和深化认识地球本体研究。
1934年,滕吉文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他随父亲辗转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漂泊。1952年,还没读完高二的滕吉文参加高考,本想报考唐山铁道学院车辆制造和桥梁涵洞专业的他,最终选择了“服从祖国建设需要”,进入当时的东北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学习。
1956年大学毕业填报志愿时,滕吉文再次写下“服从组织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至今,傅承义先生的一句话还在滕吉文脑海里回响:“我这里不是幼儿园,是科学院,你将来的目标是当科学家,对一切科学问题善于独立思考才能有所发展。”
1958年,仅学习了3个月俄文的滕吉文考上了前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所研究生。
在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自主创新始终贯穿在滕吉文的教学理念中。“招生时要提倡学科交叉,学生毕业时也不要全留或强留。如果学术近亲繁衍,科学永远发展不了。”滕吉文认为,科技强国同样需要自主创新,而理念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地震预测是个世界性难题”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滕吉文经常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来形容什么是地球物理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Ms 8.0级地震。中国科学院受命开展有关地震的科普报告,这一任务落在了滕吉文身上,最终将报告题目定为《动荡的地球》。
滕吉文认为,地震预测是个世界性难题,“首先,地震是突然发生的,猝不及防。其次,地震发生的机理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拿这次的机理套那次地震。此外,搞地震研究的人希望地震越多越好,有助于总结规律,但地震会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是一对矛盾。所以地震预测难度确实很大,但也有着一线希望。”
滕吉文回忆,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前,距离辽宁营口约120公里的郊区有一个地震台,监测记录了几百个小地震。在记录达到571次后,地震突然停止,辽宁省地震局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发出预报,最终证实了这次预报的成功。
然而在1976年唐山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类似的成功预测未能上演。滕吉文说,汶川地震发生前的30多个小时,有一处井下地应力观测台发现过一个脉冲信号,但谁也不敢断定是大地震将要来临,故未敢发出预报。“没有报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无法确定这个信号是地震前兆还是其他因素干扰。这个信号也是在地震发生后反推,才认识到可能是前震的前兆反映。”
“汶川地震后有个记者问我,说有人预测还有大地震,我说你没有依据,不能这么报。假如预报今年会发生一次强烈地震,但不知道何时何地,是不是全国的生活、工作都要停下来等着地震?这是不可靠的。”滕吉文说。
【匠人心语】
新京报:你觉得在完成自己的成就中,如何呈现匠心精神?
滕吉文:我觉得是八个字,刻苦奋进,勇于创造。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滕吉文:第一,在科学研究中,必须了解这门学问在世界范围的最新发展形势和趋势,你做的东西在哪一个环节上,你如何跟上或超越,思索、发现和“猎奇”。第二,必须坚持在工作中永不懈怠。我给自己规定每年至少发表两篇文章,要符合院士的声誉。第三,一切要规律化,即有序,无论工作、生活、学习。最后,和谐共事,刻苦奋进,勇于创新。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您认为最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滕吉文:在科学研究的环节中,青藏科考是我最艰苦的一段。这是一块未被地球物理学开垦的处女地,是发现和创新的沃土,我必须奋力追求科学的真谛。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滕吉文:我现在在做一件事,就是由我国与越南接壤的凭祥,向北一直到中蒙边界满都拉,探测这条线长达3000多千米的剖面。加起来已坚持十多年了,还剩最后一段人工爆炸工作未完成。这是一条经过很多盆地、山脉、矿藏、地震区、油气田区,内涵非常丰富的世界上第一条连续的超长综合地球物理大剖面。愿“上帝”保佑,如果能做完乃一幸事。
新京报:你感觉你获得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滕吉文:当我取得的数据是第一手数据,提出的是最新的理念,而被众人承认和共识的时候。
新京报记者 郭铁 图片 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汤文昕 摄
编辑 袁秀丽 徐晶晶 校对 张彦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