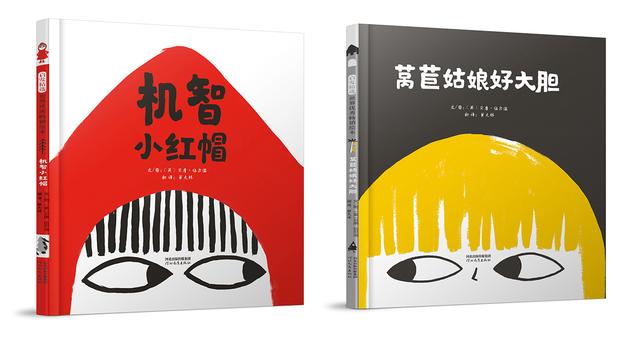编者按:自两宋以后,荀悦《汉纪》常被后人讥讽“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本文作者从历史叙事学角度切入,指出《汉纪》吸收、发展了《左传》“言事相兼”、《史记》《汉书》重人事的特点,形成了事中有人、人在事中的叙事结构。其问世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规律的形成。《汉纪》以“综往昭来,永监后昆”为旨趣,具有鲜明的监戒意识和“资治”目的。其“志在献替”旨在帮助汉献帝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而“立典有五志”则是荀悦的“献替”之志在史学上的具体表现。“省约易习”“有便于用”昭显出荀悦意欲通过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历史撰述,向统治者进献可行之策、废替不可行之举的思想。
摘要: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名著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人物史事的准确批判、叙事行文的丰满可读而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东汉末年成书的荀悦《汉纪》即是一部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史学名著。然而,在《汉纪》的流传史上,对于它的评价和定位出现了以“叙致既明”和“叙事无味”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汉纪》叙事的结构之“新”、荀悦本人“志在献替”的撰述意旨,以及是书“有便于用”的具体表现,旨在对《汉纪》的叙事特点和撰述旨趣做进一步探索、评价。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对于史体史例的评论是一个核心环节,在这个领域,唐人刘知幾提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即以编年、纪传“二体”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史学的整体面貌。刘氏又以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分别作为“二体”典范,他的论断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也”。这里提到的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是中国史学发展前期两部关系密切而又各具代表性的史学名著,前者为纪传体皇朝史之祖,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开创了编年体皇朝史体例。
在荀悦《汉纪》的流传史上,其自书成之际到纪传体大行其道的唐太宗时期,大多时候被政治家、史学家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此书自两宋以后流传渐微,南宋郑樵一度指出:“学者循习班、马之日久,故此书不行,自唐以前犹不能忘焉,今或几乎泯矣。”明清之际大学问家顾炎武批评“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的治学路数,对改写《汉书》而成的《汉纪》批驳甚苛,称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顾氏论点与唐太宗称《汉纪》“叙致既明,论议博深”形成鲜明对比,强力扭转了《汉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致影响了今人对荀悦及其史学成就的评判,是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中颇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荀悦《汉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包括历史编纂思想、历史鉴戒思想)、史论特点、史源分析等方面,并对《汉纪》发展编年体史书体裁予以充分肯定。近年来,随着叙事主义史学在国内学界的流布,以“叙事”视角研究、阐发史学文本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但其所说的“叙事”(narrative)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体系中的“叙事”,在含义及其适用范围上并不一致。按刘知幾、洪迈、赵翼、章学诚等史学批评家所论,在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叙事”所关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史书结构、记事丰简、叙事与说理、史文审美、史书功能、史家身处等,下文将从这些方面讨论、揭示荀悦《汉纪》叙事的结构、思想及其特点。
一、《汉纪》叙事结构之“新”及其渊源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秘书监荀悦受命“依《左氏传》体”对班固《汉书》删繁取要,首尾三年,撰成《汉纪》三十卷进献,显示出撰述者卓越的史才。《汉纪》成书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统治者和学人的重视,公元8世纪初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称其“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可见是书所享有的学术地位。《汉纪》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上一种崭新的撰述形态——编年体皇朝史的产生,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史学自身发展的生命力。《汉纪》能够在史学史上取得如此成绩,首先是因为它采用了恰当的叙事结构,在八十万言的《汉书》基础上仅用十八万余言就写出了西汉一代的军政大事。近人梁启超曾称该书“结构既新,遂成创作”,那么,《汉纪》的结构之“新”具体体现在何处呢?
20世纪中叶,白寿彝先生先后三次讨论过《汉纪》的结构特点,颇具代表性,在这样几个方面指引我们认识《汉纪》的面貌。第一,从历史撰述体裁的发展史上看,《汉纪》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它的价值体现在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空间,拓展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功能,推动了编年体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史书体裁,从而与纪传体史书形成分庭抗礼的格局。从这一点出发,《汉纪》被视为中国历史撰述体裁第一个演变时期结束的标志。第二,《汉书》记事有“文赡而事详”的特点,这是其优点,但也成为汉献帝阅书的苦恼。《汉纪》则“以《汉书》的纪为纲,大量吸收了传的材料,还吸收了一些志表的记载”,散入编年记事之中,用简约的文字呈现多方面的历史进程,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博物洽闻”的传统。第三,荀悦所提出的“通比其事,列系年月”的方法,“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白寿彝先生讲到的“类举的办法”“类比的办法”“连类记载”“连类列举的办法”等等,其核心都在于“类”,是《汉纪》结构之“新”最突出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史上,两汉时人已经熟练地运用“以类相从”方法进行大部帙著作的编纂,《史记》中出现了叙述同一类人物群像的类传,《汉书》则创造了把与传主品行事迹相类的人物集中附写的类叙法,其间包含着丰富的“类例”思想。《汉纪·孝平皇帝纪》叙王莽即真后不得人心,便是对《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篇末类叙“清名之士”段落的简化。同书《孝武皇帝纪四》记李少翁、李少君等方术之士,则是在糅合选取《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有关内容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一条关于方术之士的叙事线索:从元鼎四年(前113)夏“封方术士栾大为乐通侯,位上将军”写起,进而借栾大“臣恐效文成将军”语引出李少翁事迹,并增添汉武帝杀文成将军后“诲之”及得栾大“甚喜”;接着以追叙之笔写李少君、公孙卿等人皆受汉武帝信任,在社会上引起“是时言神怪方术者以万数,入海求仙人者数千人”的不正风气。这里,《汉纪》作者对《汉书》中的有关内容重新组合、连类列举,意在批评“武帝之世,赋役烦众,民力凋敝,加以好神仙之术,迂诞妖怪之人四方并集,皆虚而务实,故无形而言者至矣”。总之,“类”的方法由纪传入编年,顺利地帮助史学家将兵略与政化、休祥与灾异、华夏之事与四夷之事、常道与权变、策谋与诡说、术艺与文章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分类取舍、散入编年,搭建起新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另一种历史解释。
在分析《汉纪》叙事结构时,不能忽视史书叙事各要素所遵循的叙事逻辑以及各要素之间在叙事逻辑上的主次关系。在编年体史书中,时间、事件、人物及其他叙事要素有各自所属的叙事结构,其中,时间线索是基础结构,陈垣先生曾说“言论文章,典章制度,势不能尽载,体例如此,固无奈何”,这是编年体史书叙事结构的根本特点。《汉纪》可以将同一历史人物的事迹分散到不同年月、不同卷帙之中,而挑选某处特别突出(或随某事,或因任迁,或因免官,或因卒世)设立小传,但却绝不能将记事或记人置于时间线索之上进行叙述。例如书中记万石君石奋小传于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而记其四子小传及行事于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便是将《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对石奋及其子孙的合传拆开,各依其生活时代重新列入年月。其他如记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皆是此法。就记事(这里说的事也包括制度、灾异、四夷等内容)和记人两种要素来看,《汉纪》发展了《左传》“言事相兼”的特点,吸收了《史》《汉》重人事的思想,形成了事中有人,人在事中的叙事结构。从各要素间的相互配合和叙事逻辑出发,《汉纪》的叙事结构有这样两种形式:其一,因记一事,而连类记载与此事有关的事或有关的人;其二,因记某事涉及某人,而连类记载与此人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人。这两种形式往往交叉、交替出现,形成年月日之下人事相连的叙事结构。
《汉纪》叙事结构之“新”的背后,还蕴含着一条古代史学发展的规律,即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次重要革新,《汉纪》以后,张璠、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著书,或以“春秋”为名,或以“纪”“典”“志”“略”为题,编年体史书取得了蓬勃发展,其首发之功,当归于荀悦《汉纪》。与此同时,《汉纪》又是编年、纪传两种史体之间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它的问世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规律的形成。
从以上诸多方面来看,梁启超称“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又称《汉纪》“结构既新,遂成创作”,是一条既符合历史的也符合逻辑的评价。
二、从“志在献替”到“立典有五志”
一部历史著作的面貌,总是受到史学家撰述意旨的影响。荀悦撰《汉纪》,以“综往昭来,永监后昆”为旨趣,具有鲜明的监戒意识和“资治”目的。范晔《后汉书》叙述荀悦事迹,这样介绍他撰写《申鉴》的初衷:“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正是在“献替”之志的驱动下,荀悦撰写《汉纪》时虽于体例、材料各有所依,但又能够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叙事结构,以实现其撰述意旨。
荀悦出身颍川荀氏,为“荀氏八龙”之首荀俭之子,少家贫,善诵记,十二岁通《春秋》,“尤好著述”。他在汉灵帝年间讬疾隐居,表现出对朝局的失望,但他深受家族文化影响,隐而不遁,始终心系汉室得失兴亡。建安元年(196),曹操听从荀彧建议,“迎天子于许都”。在大致同一时期,荀悦从在野士人辗转成为汉献帝身边的中朝官,任秘书监、侍中,自此周旋于权力斗争的中心。能够在隐居之后出仕,说明这位“性沉静”却“志在献替”的士子心中燃起了对于汉室再次“复兴”的希望。彼时,汉献帝方历董卓之祸及李傕、郭汜之乱,迁都于许之后,曹操正打着“讨贼”旗号为汉室征战四方。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对于怀忠汉室的荀悦而言,能够与孔融、荀彧一同“侍讲禁中”,显然给予了他实现“献替”之志的平台。
在《汉纪》的前后序中,荀悦反复向读者传达一种观念,即把汉献帝迁都于许视为汉室走向“拨乱反正”的标志。因此,荀悦着重参考汉高祖和光武帝两朝统治政策为汉献帝建安朝政提供参考。如指出承弊于祸乱的建安朝应当奉行“赦政”;又如根据“高祖初定天下,及光武中兴之后,民人稀少,立之易矣”的时与势,建议汉献帝仿古井田之法实施土地政策,等等。这些针对汉献帝建安朝如何“守成”而提出的政策,皆表明荀悦在撰写《汉纪》之时(即建安初年),是将建安朝视为又一个“复兴”政权来看待的。
《汉纪》以《汉书》为母本,二书作者也具有相近的历史观,不过,荀悦比班固表现出了更加集中、突出的“监戒”意识和“宣汉”思想。两相比较,光武“仲兴”对于班固而言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献帝的“复兴”则是荀悦等人心之所向,是“一个幻想”。在“复兴”观念的驱动下,荀悦认为自己在汉献帝“拨乱反正”之后编撰《汉纪》,就像班固在光武“仲兴”之后编撰《汉书》一般,进而暗示着又一个“复兴”政权的兴起。这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暗示自己接续了周公、孔子的使命如出一辙。在这里,史学成为荀悦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途径,他撰写《汉纪》,很明确地是在继承“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他尤其重视史书能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监戒功能,大力提倡恢复古史官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献帝朝起居注的修撰,为后人了解建安年间的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从荀悦所遇之世、所处之时,以及他的家族传统等方面来看,“志在献替”四个字是人们进入他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在“献替”之志的推动下,无论是奉命所修的《汉纪》还是稍晚成书的《申鉴》,均旨在帮助汉献帝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如果说汉献帝提出的“依《左氏传》体”为荀悦撰述《汉纪》规定了外在的表现形态,那么,荀悦在撰写《汉纪》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春秋》的致意,则是史学家主体抉择作用于史书形式、内容和宗旨的结果,尤其是今本《汉纪序》自述此书记“二百四十二年”事,更加透露出以《汉纪》“傅《春秋》”的意旨。
《汉纪》卷首所提出的“立典有五志”是荀悦的“献替”之志在史学上的具体表现。“立典有五志”,是历史撰述所应具有的五个主要方面。“达道义”为“五志”之首,针对汉文帝即位之初贾谊、晁错上疏论贵粟安民、重农抑商的建议,荀悦指出:“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他又说:“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这就是要通过历史撰述实现以儒家伦理纲纪作为教化标准的目标。“彰法式”是在史书叙事中彰显皇朝统治的成规和经验,其中心思想是维护皇权。荀悦认为史官应当“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即突出那些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的国家纲纪、制度以及人物言行的楷模。“通古今”是要通过叙述西汉一朝的兴衰成败,为汉献帝复兴汉室提供经验和智慧,即勾画出“西汉盛世—东汉中兴—献帝复兴”这个理想中的进程。荀悦认为上至君王、诸侯,下至庶民百姓,其言行得失虽在一朝一夕,却由于史官执笔记载而荣辱千载。“著功勋”和“表贤能”都着重在写历史人物,前者是要彰著文武功臣的历史功绩,后者是要表现有才能、德行的人物行迹,使他们的事迹流传后世,贻鉴将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首次明确提出要在编年体史书中着重地写历史人物,不能不说是受到《史记》所开创、《汉书》所发挥的人本主义史学精神的影响。
荀悦在“立典有五志”之后继续写道:“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这就是说,“立典有五志”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考察、明辨天人之际、事物之宜,这是着眼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立典有五志”论还隐含着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结构,“达道义”和“彰法式”是从国家纲纪、制度措施的大方面来谈,“著功勋”和“表贤能”是从具体人物的行为、事迹来谈。“通古今”居其中,不仅是写一朝兴衰,也是要沟通国家与个人利益,国家为先,个人为后,个人荣辱系于国家盛衰,这是对太史公“通古今之辨”旨趣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荀悦将时代赋予他的“献替”理想、“复兴”抱负和“监戒”观念充分地倾注到历史撰述中,铸成了《汉纪》一书的精神内核。
三、释“省约易习,有便于用”
《汉纪序》讲是书宗旨:“凡为三十卷,数十余万言,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这里,“无妨本书”是朝向《汉书》所言,真正点明《汉纪》主旨的,应是“省约易习”“有便于用”二句,其着眼点要落在“用”字之上,即要通过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历史撰述,向统治者进献可行之策、废替不可行之举。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编年体皇朝史,《汉纪》以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的特点在汉唐之际大行于世。对自身史笔颇为自负的范晔也称该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这表明,《汉纪》十分擅于阐述事理。《汉纪》除抄录《汉书》“赞曰”和偶尔援引《史记》“太史公曰”之外,也进一步发挥了《左传》随事发论和《史记》寓论断于叙事的传统,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讲明事物发展的大势和道理。
儒家的纲纪、道义是荀悦心中理想的政治秩序。在总结自汉高祖至汉元帝朝的统治得失之后,针对汉宣帝“任法审行”和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劝以用儒术”之间的思想矛盾,荀悦提出“德、刑并用”的主张。“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这不仅是治国要道,也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法则。教化、刑法当分别作用于君子、中人、小人三类人。按荀悦自己的说法,《汉纪》就是写给“君子”读的,他还在全书结尾处强调:“《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为式’。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对于君臣之道,荀悦提出了著名的“六主六臣”论,又通过对奸臣石显的批评,从“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八个方面,强调了“真”与“正”对于王道的重要性。这篇宏论,言之切切,叙述流畅,立意高深,表现出荀悦在建安年间严峻政治形势之下的忧患意识,被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引用。
《汉纪》之“用”,最突出地体现在对于朝廷职能的重点叙述上。荀悦选取《汉书》十志的有关内容散入编年记事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强调制度对于治国理政的核心作用,即“先王之政,以制为本”“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二是以土地制度作为各项制度之首,即“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三是以发展的眼光配合因时制宜的思想讨论制度问题,强调“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
以对屯田制的论述为例。建安初年,为了供给“讨贼”军用,曾被汉武帝用于储备军资的“屯田”制度被重新启用。屯田的施行,对于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曹操打赢了建安五年(200)与袁绍的官渡之战。然而,屯田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束缚和剥削,在根本上还是服务于世家地主、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为日后曹魏的代汉提供了经济基础。《汉纪》着重阐述了屯田制的历史影响,于《孝宣皇帝纪》载赵充国三次奏事(尤其是他如何以“屯田便宜十二事”说服汉宣帝),接着以“充国初奏事,议臣非难充国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后十三人”写出朝臣对屯田的排斥,进而记载张敞、萧望之关于能否令罪犯以参与屯田的方式赎罪的辩论,揭露了屯田制的长期施行必将导致“豪强吏民请夺假借,至为盗贼以赎罪,奸邪并起”的严重后果,由此勾勒出屯田制对于皇朝统治的利与弊。荀悦还吸收了董仲舒、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观点,强烈地斥责东汉末年豪强兼并土地,以致朝廷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其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虽然荀悦度过了贫困的幼年时代,但他本人仍然属于他所批判的“豪强”的一员。从这一点出发,他能够从维护皇朝利益的角度发出如此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更深刻的是,尽管后来史家回溯东汉末年政局时,得出“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的结论,但是,如果从荀悦撰写《汉纪》所处的具体历史形势出发,自汉献帝迁都至官渡之战的几年之中,汉廷面临的最大敌人还不是代替天子出征四方的曹操及其家族势力,所要“拨乱”的对象,先有李傕、郭汜,后有袁绍等“乱臣贼子”。荀悦的《汉纪》正成书于这个历史阶段,而他能够预见屯田对曹氏权势的助长及其对朝廷的威胁,并在《汉纪》中着意于屯田、赋税等问题的编排和叙述,充分显示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所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
从历史后来的走向看,受益于屯田制提供的经济基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自任丞相,次年,荀悦卒。《汉纪》应汉献帝的现实诉求而问世,遗憾的是,它并未能帮助汉室走向“复兴”。然而,在长时段的流传过程中,《汉纪》中的“天人三势”论、“六主六臣”说,以及关于时事、游侠、教化、刑法的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对后世产生影响。在《汉纪》书成的四个多世纪之后,它被另一位重视“史籍之为用”的帝王视作瑰宝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叙致既明,论议博深,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这说明,《汉纪》之“用”是切实存在并发挥影响的。
在中国古代,“良史”总是与“善叙事”联系起来的。在这个方面,荀悦的贡献在于较早把“辞达”观念应用于历史撰述。《汉纪》叙事,娓娓道来,婉而成章,以发论之锋锐、辨析之透彻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收获了“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典丽婉通,缅嗣西京之绝响”的美誉,它带给读者锋利畅快的阅读体验,以致“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行文于此,当我们再读到诸如称《汉纪》“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的观点时,胸中或许会作出另一番思考和评价。
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下卷(总第23卷),第7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