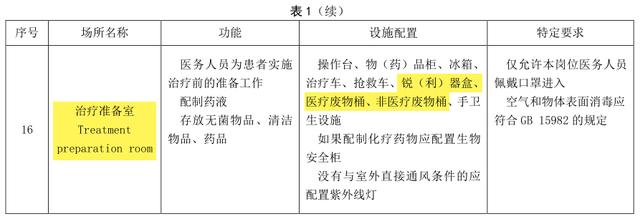知道“关锋”这个名字的,大多都是60后、70后的人了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关锋”这两个字可谓是如雷贯耳,显赫一时。
在当时的“两报一刊”上,每天都能见到署名“关锋”撰写的文章,而这个“秀才”,也凭借着一篇篇文章,声名鹊起,成为一时风云人物。
关锋和王力、戚本禹三个人,被时人统称之为“三秀才”,也被合称为“王关戚”。
本文,我就以一篇文章作为关锋的人生缩影,聊聊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

“关锋”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的笔名,1939年,20岁的他在山东乐陵县工作的时候,取了个笔名“关锋”。
或许,他也想不到,这个笔名会成为他的人生符号。
他的本名是叫“周玉峰”,还曾用过“周秀山”这个名字,这个出生于山东庆云县的汉子,打小就对舞文弄笔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早期的工作履历,都是在山东工作。在地方工作期间,也算是闯出了一点小名声,这点小名气也为后来被调进北京工作,积攒了一些基础。
1956年,这一年,对于37岁的关锋而言,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
这一年,他被调到了北京,在政研室工作。
能进政研室内的人都不简单,这是中央的一个秀才智囊班子,这个政研室的功能,是一个高级研究、咨询以及参谋的机构。
所以,能进政研室的笔杆子,要么在理论方面有着独到、深厚的研究,要么在资历和文笔上受人瞩目。
这政研室里面的笔杆子们,随便一个站出来,在文章方面都可以是独当一面的人物,譬如: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等。
所以,37岁的关锋,从地方上被调进北京的政研室,那真真是鱼跃龙门。
人生巅峰陈伯达,这个被同僚称之为“陈老夫子”的人物,比关锋年长了15岁。
当37岁的关锋进入政研室的时候,52岁的陈老夫子,初始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没啥大的印象。

但是,关锋在哲学领域颇有研究,功底也很深厚,恰巧陈老夫子对于哲学这方面也有着研究,兴趣也颇深。
两人时常讨论中国古典哲学,这一来二去,老夫子对关锋这个后生也是越发的欣赏。
1958年6月1号,《红旗》杂志正式创刊,陈伯达被任命为该杂志的总编辑。
同年,关锋也被陈伯达调进了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工作,借助于这个平台,即将步入四十不惑的关锋,逐渐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起飞。
关锋初进杂志社的时候,还是个无名小卒,但是陈伯达很看好这个后生,有意重点提拔栽培他。
在关锋进入杂志社,仅仅过去了半年,他就被陈伯达提拔为“编委”。
当时能在《红旗》杂志社内担任编委,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要么是有着相当深厚的理论水平,要么就是级别高才行。
客观的说,关锋的文笔实力也是不错的,他写的文章,分析高深的哲学问题,大多是深入浅出、文风活泼,有着属于自己的文风特色。
不得不说,1958年这一年,对于关锋而言真真就是一个“幸运年”。
这一年,他不仅进入《红旗》杂志社,仅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编委;也是在同一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
伟人看到了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对其中的观点颇为赞许,还特意在文章下面写了一段批示。
由此,关锋不仅进入了伟人的眼里,而且还由此声名鹊起。
不久之后,他被提拔成为杂志社里哲学组的组长。

要知道,伟人对于历史和哲学都颇有兴趣,能在《红旗》这么重要的刊物里,担任哲学组的组长,这地位自然也就举足轻重。
此时的关锋,已经是一个首长级别的人物了。
在1966年后,关锋同王力、戚本禹一起,相继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
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陈老夫子,由于身兼数职,工作繁忙;因此,负责杂志社实际领导工作的,是“王关戚”这三个副总编辑。
然而,人生就是这么一句话的轮回: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在你红极一时的时候,人生的厄运也会在转角处和你不期而遇。
如果从1958年,关锋进入红旗杂志社算起,到1966年步入职场巅峰,这八年的时间,他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到了1967年,人生的厄运就在转角处不期而遇了。
厄运已至,浑然不知关锋所在的圈子是“江、陈”二人的小集团,在这个小集团里,他所充当的角色,往往都是“急先锋”、“先遣队”的角色。

“江、陈”不愿出面的事,“王关戚”三秀才来做,以手中笔作为杀人不见血的刀,每一个字犹如利刃一般,划碎了不知多少身躯。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王关戚”三人得势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其实都不怎么买陈老夫子的帐。
这也难怪,一来那个老夫子不太愿意培养自己的势力,因为他担心自己所提拔起来的人,出事之后会牵累他;二来,他擅长文章,不擅长权术。
而且,相比于江而言,谁的大腿更粗,这三人心中自然明了。
我们重点来说说本文当中的关锋,在1967年1月10号这一天,关锋在《解放军报》发表一篇社论。
其论调就是要在军队里搞事,说白了,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把军队的指挥权给弄过来。

好嘛,你这还得了。
军队被称之为最后的万里长城,在伟人眼里,这军队,是不可动摇的国本。
一句话,谁碰谁死。
关锋这个马前卒,第一次染指国本,这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而他,却对此还不自知,仍旧在深渊的边缘策马奔腾。
同年的七月底,关锋执笔,在《红旗》杂志上又再次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
好嘛,这一次惹出了更大的祸端,也直接让他成了阶下囚。
这篇社论一经刊发,各地不少的军事机关都受到了冲击,甚至还演变成公开的抢夺武器。
这篇社论所带来的影响,让林帅十分的不满,伟人也直接表示了自己的震怒。
八月上旬,在上海的为人看到了这篇社论,直接作了如下批示:
“大毒草”、“还我长城”
很显然,这动摇国本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得知伟人的这一批示后,“江康陈”纷纷把责任往下推,而关锋作为直接的执笔者,自然难逃其责。
1967年的8月26日,关锋被要求“请假写检讨”,其实也就是被隔离审查,与之一起的,还有王力。
起初,他被关押在钓鱼台的2号楼,后来,在同年的10月,他被转到了北京西山的一栋别墅里。

1968年1月,关锋被转进了监狱,由此,开启了他14年的牢狱生涯。
不过,他被免于刑事起诉,也就没有被审判,没有被判刑。
晚年生活1982年的年初,62岁的关锋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他被安排住在北京的沙滩北街2号院,这个大院是《红旗》杂志社的宿舍大院,和他一起居住的,还有其妻子和儿子(本文由今日头条“贱议你读史”原创,其他平台均为抄袭搬运)。
关锋刚出狱的时候,还没有其他的安排,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起初每个月给他发放一笔15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涨到了500。
本来呢,当时他是想离开北京,回到山东老家安享晚年。
山东德州那边得知他打算回乡,还特意给他新盖了一栋二层的小楼房。
不过,他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能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这才打消了回乡养老的念头。
从1982年出狱,到1988年的年底,这段时间,关锋每个月都领生活费,但是其他的待遇安排都还没落实。
一直到了1988年的年底,他的待遇才落实了下来,其住房、工资和医疗等等,由《求是》杂志社负责,按照局级待遇管理。
这里说明一下,创刊于1958年6月1号的《红旗》杂志,于1988年7月1日正式停刊,取而代之是《求是》杂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关锋的收入,包括其稿酬等收入,每个月接近四千元。
他晚年的生活很单纯,就是一个普通文人笔杆子的纯粹生活,每天就是看书、写作,闲暇时分,就去附近的公园练练气功。
他所看的书目,大多都是哲学类的书籍,毕竟他这一生都在和哲学打交道。
而关于往事,他一直遵循四不原则:不看、不想、不写、不谈。
也是因为这“四不原则”,所以他才没留下一本回忆录,和有关回忆的文章。所以,对其相关的研究和了解,也就只能从旁人的文章,已经相关的资料当中,得知一二了。
晚年的关锋,可以用这么三个字来评价:蛀书虫;而他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这么一句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出狱后,过了23年平静的晚年生活,86岁的关锋于2005年去世,走完了他这,或好,或坏的一生。
本文由今日头条“贱议你读史”原创,其他平台均为抄袭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