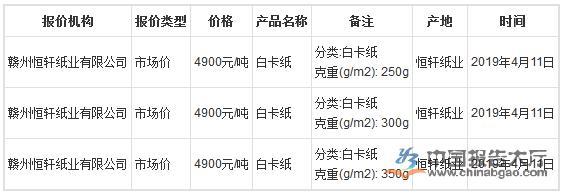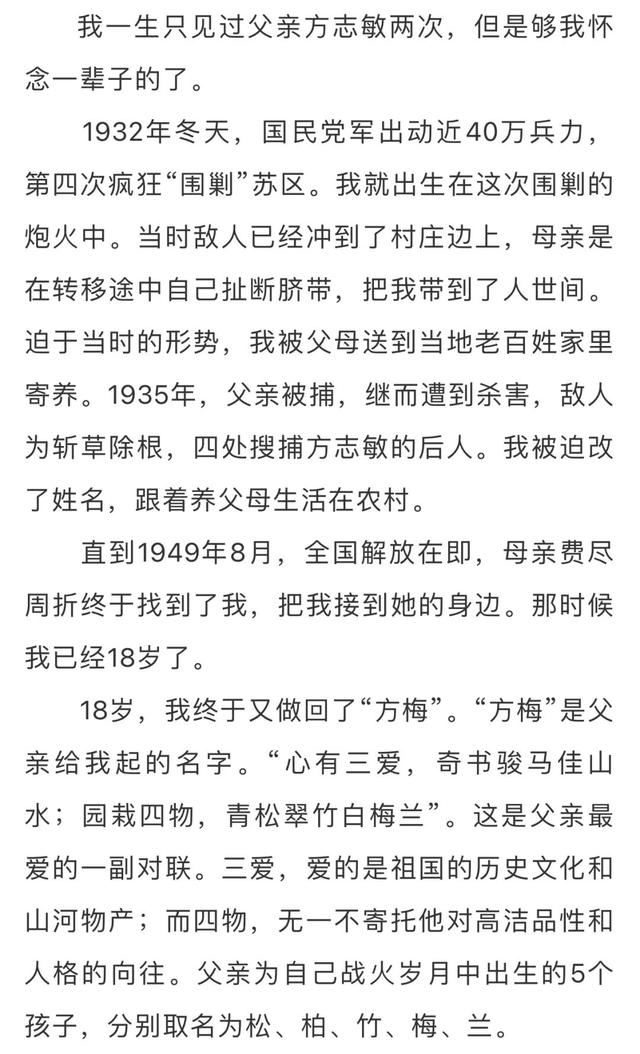成书于战国初年到西汉初年的上古时期故事神话及志怪集《山海经》, 保存了大量关于图腾崇拜的神话传说, 通过此书可以透视远古时期我国先民的群体信仰。本文将从图腾崇拜的概念入手, 着重研讨《山海经》中图腾崇拜的类型及演变, 在弘扬龙凤文化的今天, 意在透过《山海经》对我国先民的群体信仰作初步论证。
一、图腾崇拜的概念界定及世界奇书———《山海经》图腾, 系北美印第安语totem的音译, 源于奥季布瓦族方言, 意为“他的祖先”、“他的先知”, 后来引申为“他的标记”。而正是这个标记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社会组织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原始人认为他们中的每个个体、每个部落都与某种特定的生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而又绝对的联系, 他们往往把群体部族的兴衰成亡, 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与这种特殊的生物或无生物简单而又绝对地联系着。由此, 对这种特殊的生物或无生物进行神化和偶像化, 产生了具有早期宗教色彩的图腾崇拜。同时, “图腾也是禁忌, 这一概念意味着被神圣化, 禁止触摸之物。”[1]他们相信, 通过图腾崇拜, 就能获得崇拜对象的某种自己不具备的力量和能力, 得到他们的保佑和庇护。
图腾崇拜从世界范围来说, 具有普遍性。它发源于旧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早期, 不是个别地区和某个部落特有的现象。如俄罗斯有对熊的崇拜;埃及对太阳神和鹰神的崇拜;西欧对谷神的崇拜等等。成书于战国初年至西汉初年的上古时期神话及志怪集《山海经》, 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图腾及图腾崇拜的资料。
《山海经》是一部先秦古籍, 全书18篇, 约31 00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 也是第一部记载我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 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 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 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 作者亦非一人, 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神话奇书。《山海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 《山海经》作为远古时期的著作, 它的真实程度有限, 而想象色彩非常浓厚, 一般把它视为地理著作。其地理叙述往往存在很大误差, 各山之间的方向大都稍有偏离, 各山之间的距离亦不正确, 误差甚至大到十几倍。《大荒经》部分神怪内容最多。可以说, 《山海经》这部远古著作充满了各种想象。顾颉刚认为, 《山海经》开创了中国地理学幻想的一派, 而禹贡开创了征实的一派。
其二, 《山海经》在历史上主要被当做志怪之作发挥社会功能。尽管刘歆等人力图证明《山海经》真实可靠, 但未能改变对待《山海经》的基本态度。叶舒宪把它定性为神话地理书。把它作为中国最早的神话之一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
二、从“日月崇拜”到“龙凤图腾”的形成———《山海经》中图腾崇拜的内容《山海经》中不但有大量的图腾崇拜的内容, 而且勾勒出了我国先民从日月崇拜到龙风图腾形成的脉胳。
(一) 日月崇拜和植物崇拜以日月为图腾而进行早期的图腾活动, 在原始社会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是世界的普遍性宗教行为。以日月为图腾的氏族在古代并不少见, 直到现在有些地区的原始部落仍然保留了这种遗风。
在《山海经》中也记载了大量关于日月崇拜的资料。十日并出和羿射九日以及夸父追日都和太阳图腾有关。如《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 甘水之闻, 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 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 帝俊之妻, 生十日”等。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大量象征太阳的火鸟或直接是太阳的图画及器物。
月崇拜和日崇拜往往联系在一起, 日月的起落和日昼月夜的现象是古代先民最早认识的自然现象。《大荒西经》云:“有女子方浴月, 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常羲生月的神话后来衍化成黄帝令常仪占月的故事, 即利用常氏族首领以测月之盈亏的仪器月规观测太阴 (月) , 创立太阴历。仰韶文化和马家窖文化也曾出土过象征月崇拜的玉兔图画。
先民对植物的崇拜, 主要集中在《五藏山径》之中, 而最主要关注的就是植物的实用价值, 如:“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状如榖而黒理, 其华四照, 其名曰迷榖, 佩之不迷。”又如:“又东五十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 大五十尺, 其枝四衢, 其叶大尺馀, 赤理黄华青柎, 名曰帝女之桑。”这些都是希望植物有强大的力量, 通过接触可以产生巫术反应, 而借此来保护人类。
图腾制度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 甚至可以理解为其是所发生的时代的社会制度的一面镜子。许多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思想文化体系主要是图腾文化, 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图腾制度, 最早的宗教形式是图腾崇拜, 最早的艺术是图腾艺术[2]。
(二) 动物崇拜和龙凤图腾的形成图腾是建立在狩猎生产和原始农业生产经济基础之上的, 因而动物是重要的图腾物, 《山海经》中反映动物图腾的材料十分丰富。
动物崇拜的具体原因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先民们过着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的艰难生活。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作为人的优势的时候, 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先天的种种限制。比如, 他们不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 鱼儿在水里游荡, 不能像陆地上的动物那样有着惊人的速度和超人的力量。这时先民们便认为它们与某种神灵相关联, 从心里产生崇拜。
《山海经》中的动物图腾最早的是单一的具体动物, 如:鸟、鱼等。如《海内经》云:“有盐长之国。有人焉, 鸟首, 名曰鸟氏。”而于1972年和1976年分别在广西西林和贵县出土的西汉墓葬铜鼓的腰纹上, 就绘有头戴羽冠, 上身裸露, 下身披有前短后长的吊铲的舞人群像。
《山海经》中有不少鱼崇拜的材料。《海内北经》云:“陵鱼人面, 手足, 鱼身, 在海中。”这种人化了的鱼, 应该属于鱼图腾的反映。《大荒西经》亦云:“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颛顓为著名古帝, 死后得鱼之救援, 与鱼合为一体而复生, 更是一种鱼崇拜无疑。
上古草木茂盛, 人迹稀少, 爬行动物曾盛极一时, 崇蛇成了世界各地古文化的共同内涵。《山海经》中有大量崇蛇的资料, 这也是“龙”图腾的前身。根据经文内容, 这些资料共分为三类:一类是描述蛇的巨大威力, “巴蛇食象, 三步而出其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是蛇或蛇的一部分直接被当作神祇, 如《五藏山经·北山经》称“自单狐之山至隄山, 其神皆人面蛇身。”等。第三类是作为神的御物或饰物, 如《五藏山经》中有诸多描写神:“人身而手操两蛇”的资料。而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和伏羲等人皆是“人首蛇身”更充分地说明了先民对蛇的崇拜程度。
随着氏族部落之间婚姻关系的演变, 上古时期由对单一动物图腾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复合图腾的崇拜, 而这种复合图腾分两类, 一类是同类动物的复合图腾, 另一类是不同动物的复合图腾。《南山经》云:“东三百里曰基山, 有鸟焉, 其状如牛, 九尾四耳, 其目在背, 其名曰猼犯”等等。
而不同动物的复合图腾则是以某一个动物的躯体为主干, 肢体属于不同类动物的形象。如:《北山经》云:“钩吾之山, 有兽焉, 其状如羊, 人面, 其目在腋下, 虎齿人爪, 其音如婴儿, 其名曰袍鸽, 是食人。”而这种以羊为躯体, 结合了人、虎等诸种特征的复合图腾基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部落融合以后产生的新的图腾标志。
而我国古代先民图腾崇拜的集大成者———龙凤图腾就是这样一种复合图腾。
龙图腾的出现与以种植经济为主并结合渔猎、养殖为一体的原始农业形成有关, 龙形象的四个主要部位头 (猪首羊角) 、爪 (禽爪) 、身 (蛇或鳄) 、尾 (鱼) 代表了原始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凤和龙一样也是综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形象。《说文》云:“凤之象也, 鸿前, 鳞后, 蛇颈, 鱼尾, 鹤颗、怨思、龙文、鱼背、燕须、鸡嚎。”这样, 影响中华文化数千年的龙凤图腾作为一种复合图腾出现在了《山海经》中。
《山海经》中记载的龙图腾材料主要见于神祇, 《五藏山经》各经所述山神或龙首, 或龙身, 都是龙崇拜的反映。如《南山经》首经称所记十山神为龙首, 《南次二经》所记十七山神为龙身, 《南次三经》则称“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禹之山, 凡十四山, 其神皆龙身而人面”。
凤是鸟崇拜的集大成者。在《南次三经》中有记载:“丹穴之山, 有鸟焉, 其状如鸡, 五采而文, 名曰凤皇”, “是鸟也, 饮食自然, 自歌自舞, 见则天下安宁。”美化崇敬之心跃然可见。
三、龙凤图腾的影响力民族的起源就是民族文化的起源, 龙凤图腾形成后, 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形象源远流长, 上溯至炎黄, 顺流达当代。《山海经》之后, 《说文》中记载:“龙, 鳞虫之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临渊。”而凤作为神鸟, 也是原始社会人们想像中的保护神。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 皇帝称真龙天子, 皇后称凤仪天下, 到今天的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龙凤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龙凤文化也成为中国人寻根的标志, 成为凝聚所有华夏儿女, 炎黄子孙家园母亲的标志, 成为全球华人心中共同的旗帜。
参考文献[1] 张岩.图腾制与原始文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2] 何星亮.图腾与人类文明形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