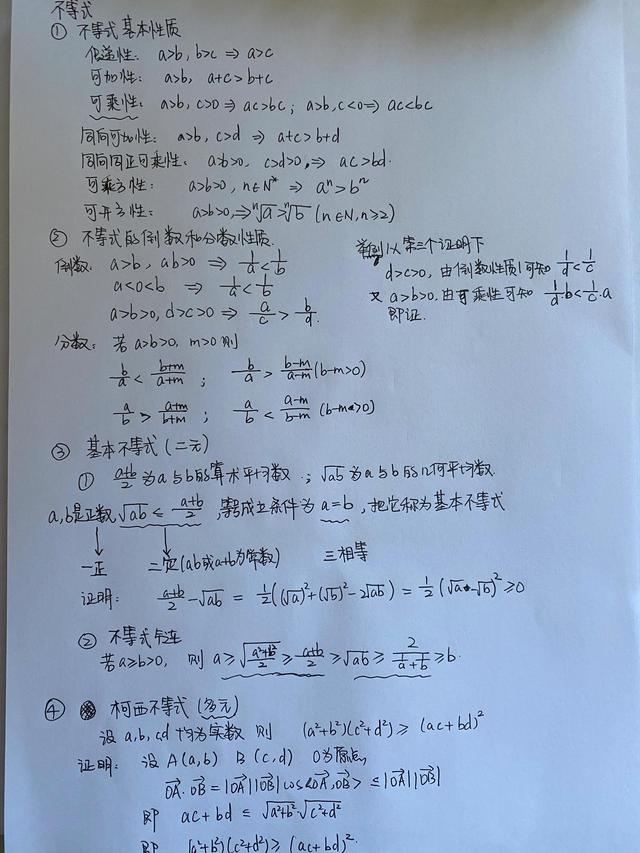城市边缘的小工厂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来自更加偏远地区的少年们,用低廉的薪水和重复的工作麻痹着他们本就不大的野心。在工厂里上班是这群少年踏入城市的第一步,可能也是他们追求生活的最后一步。
我想起他们,想起然哥,想起阿兰,
想起小玉,也想起我自己。
那些广袤的土地上,
还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们一样的少年。
他们行走在夏天的烈日下,
流着汗,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
从一个个小村落,
走向一个个工业化的大城市。
从一个笼子,走向另一个笼子。
变成螺丝钉,变成汗水,
变成另一种人。
1

今年四月底,我在QQ空间看到了然哥的结婚照,翻了翻他的相册,最近的一张,是穿着白衬衫的他坐在驾驶位的笑脸。我猜大概是他副驾驶位的老婆拍的。
自2015年入秋,我离开中山起,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联系了,期间唯一一次联系还是空间说说下的评论。这五年里我甚至很少再主动想起他,直到看到他的结婚照。
照片里他笑得很开心,以前从来不发照片的他愿意在社交软件上分享生活了,我猜他现在或许过得不错,至少也应该接近了他当年的愿望。
我翻看他的相册,那张脸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有些莫名的恍然。我们同在广东的日子竟然已经过去了五年。我们仍然年轻,但那时候的日子始终成了阻碍这份“年轻”肆意生长的围墙。
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们,从四川,从贵州,从广西,从湖南,从大山里或是平原上某一个隐匿的小村镇里,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走出去,离开学校,寻求生存和另一种更有力的教育。

那时候我十四岁,我以为我忘记这些事了,可我写下这些话时,才发现这些事原来是整个少年时代为数不多的清晰的记忆。它真实且沉甸甸地活在我的人生里,甚至决定了一部分如今的我。因为这些情绪,我想是该把它拿出来晒晒了,仅此。
这就是我想讲这个故事的起因。
2

2014年三月底,因为爷爷的去世和对学校的厌倦,我选择了辍学步入社会。
2014年四月中旬,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刚开始泛黄,那时候我十四岁,只身坐上了南下广东韶关的火车。到了韶关后,我找到我大伯,他带我去了客车站,让我上了前往中山古镇的大巴车。
到古镇已经是深夜了,堂哥开着厂里的小货车来接我。我们经过一片漂亮的住宅区,拐过一片低矮的平房,就到了昏暗的工业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黑暗颠簸的道路,街上的路灯不多,隔很远才有一个,两盏路灯的光芒孤零零地照亮一小片路面,彼此像海面的孤舟。路面上有很多坑坑洼洼,本就颠簸的小货车晃得厉害,我紧张地抓住把手,一旁开车的堂哥不但毫不在意,还耷拉着眼皮犯困。
在古镇的第一晚跟着堂哥住在一起,广东炎热的天气让我极其不适应,一夜难以入眠。第二天堂哥带我进了一家做灯具的小厂,把我介绍给了老板。

厂子很小,在一栋四层小楼的二楼。生产间加上库房总共只有三间教室的大小,是一整个空旷的楼层,生产用的工作台和库房之间也没有隔断。墙壁上开了几个大窗户,窗户大概很久没有清理过,绿色的玻璃上沾着一层肉眼可见的灰尘和黑色的污迹。
有四个女孩正在工作台上拼着塑料灯具。放材料的库房里还有一个中年大叔,正用拖车运着包装用的纸箱。当时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正在打磨灯具配件的年轻男生,因为他穿着干净的衬衫,看起来也彬彬有礼,和印象里的工人形象差别很大。
当天晚上,老板带我去安排的宿舍,路上告诉我,现在是两个人住。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年轻人和中年大叔,到了以后才发现宿舍里只有那个穿着衬衫的年轻人。我是两个人里的另一个。
这个年轻人就是然哥。
一切收拾妥当后,我躺倒在宿舍的硬木板床上,深夜的窗外仍有工厂运转的声音,月光洒在大片大片的蓝皮厂房上,反射出惨淡的光亮。我把床头的电扇风力开到最大,还是很热,心神不宁。然哥在床上玩手机,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就这样开始了混迹在工业区的生活。那年我十四岁,在广东中山,做起了堂哥托熟人替我找到的工作,一个月1800,加班另算,包住不包吃。
3

然哥1995年出生,比我大四岁,当年他也只有十八岁,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两岁。和我起初猜的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是技术人员,而是和我一样的工人。
那时候然哥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会放一些电视剧。那几年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但远没到如今“伪器官”的程度,一部好的智能机已经够潮流,电脑对我来说就成了更高级的东西。

我们常坐在他的小桌子前,买两碗五块钱的鸡蛋炒粉、两罐啤酒,一边吃,一边看金庸的武侠剧。每天如此,也慢慢熟络起来。
适应工厂的生活后,我开始觉得然哥很奇怪。
厂里的工作灰尘不大,但也容易脏衣服。那四个广西女生做最干净的拼装活,每天早上也要换一身工作的衣服来上班。可然哥却总是穿着衬衫,并且都是干净的衬衫。
然哥有很多衬衫,有短袖的,也有长袖的,每件的价格都不低,最贵的一件四百多。
2015年,这个价格的衣服对我来说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他每天上班都穿着这些衬衫,而且每天都会把穿过的衬衫洗得很干净。
那时候的古镇还有些乱。厂区外面的街道上几乎都是外地人,绝大多数来自云贵川。在路上每隔五十米就能看见一个光着膀子、各种纹身、眼神犀利的人。有一次,跟着然哥去物流中心送货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几家开着大门的工厂,往里一看,大门里面供着显眼的关公像。
我舔舔嘴唇,口干舌燥地问他:“这些供关公像的都是这里的黑社会吗?”
然哥头也不转,一手开着车淡淡地说:“都是来讨生活的。”
后来我才了解,那里有很多各地的人抱团,形成了不少类似帮派的团体。白天他们都是厂区里各个工厂的年轻工人,晚上他们聚在路边的破旧台球桌边,喝着啤酒,肆意欢闹。
然哥跟他们不一样。事实上,在中山的日子里,我从没有看到过第二个跟然哥一样的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时彬彬有礼,爱穿干净的衬衫,才十九岁,又已经懂得一些世故,全然不像那些已经放弃更高人生的打工仔。
那时我很敬佩他,尽管他做着跟我一样的工作,拿着跟我一样的工资,跟我一样在本该灿烂的少年时代选择一种灰色的生活。
就连“灰色的生活”这个说法,也是然哥对我说的。
有天晚上太热,实在睡不着。我们去楼下买了几瓶冰啤酒,坐在超市的门口乘凉。然哥平时沉默寡言,也从不提及自己的故事。那天他好像说了很多话,但依然没有提及关于他的过去。
“灰色的生活,就是——往前望不到前路,回头回不到从前。”
然哥喝了一口酒,说:“你小子,最好还是走吧,回去读个技校也好,别像我。”
他有心事。但我依然看不懂然哥,就像看不懂这里的生活一样。
当年我十四岁,去中山的火车上,书包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手写的书稿。我是从小镇里出来的,中山对我来说是大城市,即使是工业区,也是城市。城市就代表机会,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像韩寒一样。
在古镇多如牛毛的各种厂里,我本以为很少有比我岁数小的。那时候我戴眼镜,身材瘦弱,还是一个孩子的模样,与周围格格不入。但后来我见识到了不少跟我年纪相仿的少年们。
他们都有各自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的原因,但都选择了来到这里——劳动力廉价的小工厂,不需要技术,不需要资历,不需要未来。偶尔雄心壮志,又长时间安于现状,好像每个月两千块的工资,已经足够让这些农村出身的少年们麻痹于生活。
而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大多数无外乎几种:家庭贫困、学习成绩差、对外界的向往、少年时代躁动的情绪……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每个原因上都或多或少都占据一点。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或许尚未理解到“灰色的生活”,但人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是切实的感觉。实实在在且沉重地挂在生活中那些无法言喻的感受里。
有一次看着那个工厂里下班后常去发廊的中年男人,然哥就悄悄对我说:“你如果安于现状,就会像他一样。”

我依旧对然哥有些好奇,因为他从不提起他的过去。他不提,我也就从来没有问过。至于厂里的那几个女生和中年男人,他们对然哥的评价都是“怪人”。大叔说,然哥不去镇上的发廊,这个年纪对女人不好奇的太少。那几个女生说,然哥听一些奇怪的歌,平时也不和她们聊天。
然哥喜欢听一些独立音乐,就是后来的文艺青年们推崇的那些。有一次他在宿舍放过左小祖咒的歌,唱腔怪异,歌词不着边际,我也欣赏不来。几年以后,我也喜欢上左小祖咒,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想起他和那年中山酷热的夏天。
2014年夏天,我依然在厂里工作,然哥却突然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走得很突然,那天下班后我就没有见到他,给他发消息也没有收到回复。后来问起老板,老板也只说然哥请了假,不知道多久回来。
大概半个多月后,然哥才回到厂里,依然穿着干净的衬衫。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变化,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工作时沉默寡言,晚上洗着那些衬衫,喝一罐冰啤酒,戴着耳机听歌。
没过多久,到了老板的生日。老板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包了两个大包间,请了五桌人,大部分是朋友和生意上的人。厂里的四个女生,中年男人,我和然哥,坐在角落里的一桌。
那天然哥喝醉了,因为他帮老板喝了很多酒。此前我从未见过然哥喝醉的样子。吃完饭后回到宿舍,然哥连接了几大杯纯净水喝下去,然后跑到厕所里狂吐。
那天晚上我才大概了解了然哥的一些事。他吐完后坐到床上,点了根烟,开始跟我有一茬没一茬地说话,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不像是在对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然哥的父亲离世,就在他请假的那个月。泸州的村里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他一个人回去料理了父亲的后事。父亲是他最后一个亲人,那时候他刚过完生日不久,十九岁。
然哥很早就出来工作,大概像我当时的岁数,十四岁左右。那时候他带着大包小包,揣着两千块钱去了广州。在广州待了一年,后来又去了深圳。在深圳的时候,然哥喜欢上一个姑娘,他们年龄相仿,混迹同样的圈子,一个打工仔,一个打工妹。
那个姑娘喜欢穿衬衫的男生,因为男生穿衬衫看起来很干净,也因为他们的年纪本就应该生活在干干净净的象牙塔里。于是然哥开始穿起了衬衫,到后来自己也喜欢上了衬衫。

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是打工仔和打工妹未能善终,因为打工妹悄无声息地在广西老家嫁了人。十五岁?或者是十六岁。就这样消失在他的生命里。
然哥出来工作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太多故事,因为穷。父亲残疾,多病,他成绩很好,但读不下去了。国家的教育贫困补助可以解决他的上学问题,但解决不了他和父亲的生活问题。
那天晚上然哥给我讲了他对以后的憧憬:要看很多书,做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穿衬衫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手里拿着别人敬过来的烟。
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事实上,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时候十九岁的然哥也还是个少年,即便他经历苦难,孑然一身,人生只剩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因为真正的成年人从来不会说“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5年8月,我准备离开广东中山,告别工厂的生活,回家读技校。临走前,为了感谢然哥的照顾,我花了两百块给他买了一件衬衫。他那时十分落魄,靠预支的工资生活。然哥送我去了车站,提着我买的衬衫,一路无言,分别时才嗫嚅着挤出一句话:“常联系啊。”
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他的头像在我的QQ列表也变成了灰色。回到学校后,我一路顺风顺水地读到了大学,走上了和那时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在中山的日子成为对我影响最大,也是最灰暗的回忆,我努力不去想,但那段日子的灰暗却常常能变化出一些鲜艳的色彩,给予我成长所需的养分。
直到2019年夏天,我如愿接触到向往已久的影视行业,给一部微电影撰写剧本。成片在网上发布后,我在QQ空间发了一条推荐,在我生活里消失了五年的然哥突然出现,在下面评论了“赞”的表情。

当年我下班后常常在宿舍写东西,同事会笑我,然哥不会,我没有成功,但很想让他知道我坚持了下来。
我很开心,找他聊天,可依然没有回复,然哥的头像也依然是灰色。但我想他一定看到了我发的消息。
我不知道然哥如今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
他已经结了婚,妻子是否像从前那个深圳的姑娘一样,喜欢看他穿衬衫。他是否已经变得开朗许多,是否还记得那年的种种。是否已经脱离了禁锢在工厂里的生活,成为了可以“光明正大穿衬衫”的人。是否还像从前那些少年一样,活在灰色里。
时过经年,从前那个和“灰色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人生是否已经不止眼前路,还有身后身。
我都不知道。
4

2014年,在中山古镇的工厂里稳定下来后,我跟着学了厂里的所有流程,以便后面货量大时能跟得上出货速度。最开始我跟着那个湖南的中年大叔在库房搬纸箱,用板车运包装好的成品灯具,这是体力活,每天衣服要被汗水打湿很多遍。
后来货单多了起来,那四个做灯具拼装的广西女生忙不过来,我就去工作台那里和她们一起做拼装。灯具拼装很简单,在底座上安上灯管或是LED片,盖上灯罩,装进包装盒里,只需要两只手不停地动,甚至不需要出什么汗。

一直面对面坐着做事难免尴尬无聊,她们经常用广西话聊天,我听不懂,但也乐得清闲。有时他们突然说起普通话,我就知道多半是需要我参与的话题,便跟着参与一下。于是那段时间也了解到不少关于她们的事情。
这四个广西女生里有一对表姐妹,那年姐姐二十一岁,妹妹十六岁。姐姐是雷厉风行、大大咧咧的女汉子性格,已经结婚很多年,有两个孩子。据说她们那边的农村里早婚很正常,姐姐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就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她老公也只比她大两岁,结婚时两人都没有到法定年龄。
我离开广东后,有一年夏天,关于“早婚”的话题被讨论得很火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个姐姐。
厂里的人叫她阿兰。阿兰的老公也在工业区,给一家大厂开货车,每月收入不少,两人在外面单独租的房子,两个孩子在老家。他们或许是中国最年轻的那一批留守儿童父母。
阿兰常常讲起自己的感情生活,哪怕对着我也不例外,当时我确实还是个半大孩子,她什么也不避讳。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并不好,她老公不太老实,被她发现过和别的女人聊天约会。可为了孩子她只能忍受,每次吵完架后还是要给男人做一顿饭。
“小唐,你以后可不要这样子。”阿兰叹口气,对我说,“要是以前,我把他皮都扒了。”
她这话或许更多是说给自己听,我也不会和女人们开玩笑,只能干笑着应和两声。
妹妹叫小玉。小玉的性格和阿兰很像,毕竟是表姐妹,但小玉身上的戾气更重。小玉给我讲过她在学校时的经历。
她们的老家在广西河池。小玉离开学校前,因为性格大大咧咧,和一些混混男生的关系很好,她也成了乡镇上的小太妹。她的家乡很穷,但她对一个地方“很穷”没有什么概念,用她的话说:“念书念得下去的少得很。”
小玉身边的很多人都早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他们大多数都去向广东的各个城市,一头扎进各地运转的工厂里。因为工厂工人的要求最低,不需要出苦力,技术性强的工种也不多,她们一出来就能挣到钱。没有去打工的那些女生,很多在十六七岁就嫁了人。
小玉不想嫁人,所以来了广东。古镇有很多各地的老乡聚在一起,这些人也是分阶级的。在外混得好的结交厂老板的圈子,混得一般的结交打工仔打工妹的圈子。小玉在这里也没有闲着,像她在学校一样,凭着讨喜的性格,认识了很多广西的男生。
那些男生都是在这里讨生活的打工仔,并不比小玉赚得多,但是男生在这样的生活里靠野性就能吃得开,于是很多人都选择了边打工边做社会上的混混,染着头发,露出纹身,在异乡深夜的街道上结伴而行。
小玉似乎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每天下班后,厂房楼下总有几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生在等着她,她看起来也很得意。

最忙的那段出货期过后,我又去管起了库房,每天运配件去工作台,运成品去物流公司,和她们的交流也就变得少了。
到了夏天,姐姐阿兰请了假,原因是老家的孩子病了,她要回去照顾。过了一周后,她回到厂里,结清了压的工资,正式辞职了。后来听老板说,阿兰的孩子得了重病,她也终于跟她老公闹翻了,两人已经分手。
我疑惑地问老板:“就这样离婚了?”
老板玩味地笑了笑,说:“他们结婚证都没有。”
而妹妹小玉依旧留在厂里。也许是因为没人管了,阿兰离开后,小玉和那帮男生走得越来越近,经常请假。有时出货太忙她也不来上班,人手不够,老板娘都要一起去帮着做拼装。老板娘也和我说,小玉太野了,迟早会出事。
老板娘猜得没错,小玉在姐姐阿兰离开的一个月后,突然消失了。
小玉没有给任何人说她去了哪里,也没有来上班。老板联系姐姐阿兰,阿兰也不知道小玉的去向。不过老板毕竟不是父母,他们关心的只是人手不够会影响生产。老板娘天天到厂里帮忙,经常做到发脾气。她说小玉没打招呼就走,回来以后,一分钱都不会给她。
过了半个月,老板又招了一个女生,也是广西的,替掉了小玉的位置。那个女生来厂里刚工作几天,小玉就回来了。
小玉回来不是想继续工作,而是找老板要她压了一个月的1800块工资。回来的小玉已经变得很不一样。那天她在办公室盛气凌人地看着老板,脸上化着很厚的妆,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劣质香水味。
老板没有给她工资,用老板的话说,“压一个月工资就是为了防你突然跑了”。小玉离开厂里前,表示她还会过来,当晚她就会把自己的东西搬离宿舍。小玉走后,老板娘故作神秘地对那几个女生说,小玉可能是被那些男的下了药,骗去做妓女了。
小玉的宿舍跟我和然哥的宿舍在同一栋楼。下班前,老板娘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让我拿给小玉。她叹了口气,说:“你让她快点回老家吧,她还小。”
听到这话我才突然想起,老板娘的女儿跟我一样大,才十四岁。正在中山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成绩很好,很漂亮,很听话,还会奶声奶气地向他们撒娇。
小玉的宿舍已经只有她一个人了,她给我开门时,正在收拾行李。我拿出五百块钱,转述了老板娘对我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
看到我递过去的钱,小玉没有接,她很生气地大声质问我:“凭什么就这么点?压的工资明明是1800。”
我说我只是个送钱传话的,顿了顿,我还是开口说:“你还是回去吧,总比没有强。”
小玉和我当时都是未成年,没有签合同。
小玉听到这话突然情绪崩溃,哭了起来。她疯了一样上来推我一把,我一下愣在原地。她哭着对我吼:“你他妈要我回哪儿去?我还回得去吗?”
这句话在我心里或许证实了老板娘的猜测,我什么也没说,把钱放在她的床上,转身关上门离开了。我没有能力帮她,也没有理由帮她。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小玉。

离开广东后,我没有主动想起过然哥,却好几次想起小玉哭泣的脸。那年她离开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她,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我始终记得。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想过帮助她,或许想过,也或许在那样的生活里,我是和老板一样的人。可是说到底,他们也没有错。
那年我十四岁,因为几次被学校开除、爷爷去世,决心告别学校,迈向新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很多农村少年选择的路。
那年夏天,我坐在回四川的长途大巴上。大巴途经湖南、贵州,窗外闪过的山野里已经没有了来时鲜艳美丽的油菜花,只有光秃秃的山坡和火辣的太阳。
我想起他们,想起然哥,想起阿兰,想起小玉,也想起我自己。那些广袤的土地上,还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们一样的少年。他们行走在夏天的烈日下,流着汗,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从一个个小村落走向一个个工业化的大城市。

从一个笼子,走向另一个笼子。变成螺丝钉,变成汗水,变成另一种人。可是没人看到他们,没人记得他们,年轻人们仿佛都活在正直、善良、光鲜的世界里,夜夜笙歌,娱乐至死。抑或是享受着阳光灿烂下的鲜花与汗水。
我没有野心。我只是觉得,应该看到他们,也应该记得他们。
题图 | 图片来自《少年巴比伦》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文/乌鸦,文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